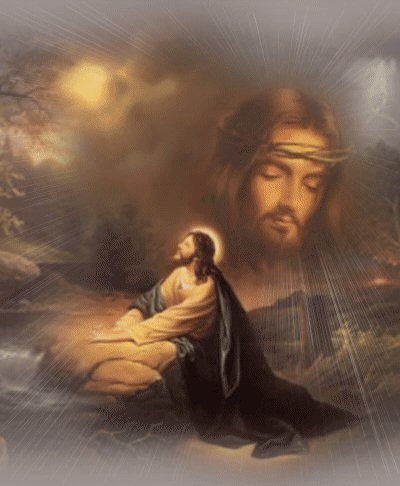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转一个弯,这么多,这么满
转一个弯,还是这么多,这么满
再转一个弯,更多,更满
多得就像没有一样
就像根本什麽都没有一样
多得什麽都找不到了
连呼吸都要找不到了
我想找到少
我想找到少之又少的少
(不,不是无,无和多一样,我要找到少)
可我要上哪里去找呢
告诉我,上哪里?
(2014年6月)
诗人,当你……
诗人,当你关注死亡
关注被遗忘的苦难
写下有力而感人的诗句
而你没有看到
一个诗人死了。又一个!又一个!
你的同类,
与你汲取着同一条河水的兄弟姐妹。
就在你的眼目前
在山里,在浅浅的山里
人家说是迷路,断食,断水
他说,死无葬身之地
人家说是失足,跌落到地下室
她说,花落,归期到了
……
“想写一首诗”
仅仅想写一首诗,挽留生命
他就不再有保留自己生命的余地
多么诡异的一个夏天
在同一个名字的下面
有人修路,扫墓,死去,朝下
有人领奖,数钱,绝不戴花,向上
白发苍苍的母亲,被人牵着手
坐在她儿子冰冷的坟头
滚瓜烂熟地背诵她儿子的诗集
脸上戴着暧昧难明的光
谁?这是谁的行为艺术?
难道是上帝本人驾临?
那纯粹而寒冷的高地
蓝色的火焰多么苍老
他年复一年陪伴在妻子身畔
去大雪纷纷的车站迎接自己
他再也没有地方去借一滴血了
在厚重的棉衣和头发下面
他像节约一粒米一样
劈着,剔着自己干瘦的骨头
可是柴仍是不够,仍是不够……
一位异国的某人情不自禁哭了那么久
而他妻子望眼欲穿地——不哭
孩子,平平安安的孩子
当你醒来,打开窗户,听到一声
清澈而真实的鸟鸣
却满屋子叫不应你的妈妈
不要哭泣,她在你能看到的某一朵花里
你要有足够足够的耐心慢慢长大
(2014年6月)
花落的时候,是归期……
在你的预感之中,在你的预料之外
在那么多桃花素笺猝不及防的
眼泪和祭奠不能止息的地方
落红,落红,落红成阵……
我没有和你说过话
我没有叫过你一声妹妹
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流下那无用的眼泪
我闭紧嘴巴不让自己说一句话
我背转身,背转身,背转身……
我知道我要遭报应
日子近了,近了,近了
漫长而持久地
被莫名其妙地堵回去不能流出来的泪水
已经满了一池又一池
它迟早要没过我的头顶
洗劫我,埋葬我,带走我
——然后——
——草长莺飞——
(2014年6月)
当你以基督之名
当你以基督之名
带领你的信众
举起雪亮的刀子
去围追堵截
去阉割撒旦
杀他,却不让他死的时候
你愤怒的理由是
他怎么可以连一块遮羞布都没有
你何其正义凛然
——紧追不舍
他何其仓惶不安
——无路可逃
那么,你是谁他是谁
上帝啊,他到底做了什麽
难道,仅仅因为他名叫撒旦?
可你总得让他到什麽地方去啊
(2014年6月)
腐烂的落叶
这一池水锈
无边无际,丝丝缕缕
蚀骨焚心,无休无止
等到切肤,已痛到麻木
却没有元凶
每一片叶子,都只是
浸在硫酸池中
自己给自己注射剂量越来越大的麻药、
在锈迹斑斓而色彩秾丽的尸体上
喷洒福尔马林和空气清新剂
唱歌,跳舞,画画,祈祷,写诗,催眠
成为斑驳中的一个斑点
(2014年6月)
……
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有人在整理海浪、波涛和地图
浪高千尺,亦不惊慌
心里暗含着必死、必败、必胜的勇气
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有人在整理石头、花朵和真理
有人在整理流言、瘟疫和神谕
有人在整理空气、血液和骨头
有人在整理桌椅、抽屉和机票
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一头狮子邀请一只麻雀在酒吧里聊天
一张课桌和一根电话线在交易所里握手
一头大象被一群蚂蚁挟持着赶夜路
一只火红的东星斑和一只银绿的苏眉
在深海里擦肩而过,分头上岸,在餐桌上为邻
一枚棕榈叶在丛林里孤单失群
一棵拒不结盟的野草
忍耐并感谢沙漠、雪原、冻土带和仍然活着的每一秒钟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