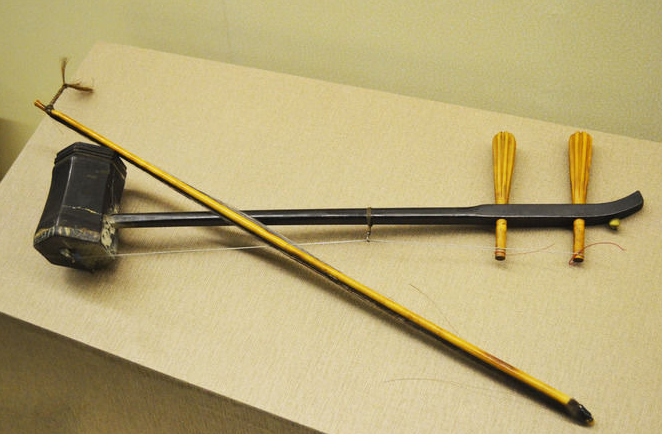不能怪别人,那就是一个人让人难忘的时期,而且上演了那么多的严酷和无法相信的事。我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面有一个临时工,由于我们是同姓,而且这个人喜欢开玩笑,那时候我干采购,很多零部件都要听他提出技术参数要求,感觉他对锅炉的构造烂熟于心中,曾经跟他一起去买过一次锅炉的耐高温的炉壁专用砖。
到了那里根本就无需我说话,他的专业术语让我听得口瞪目呆,第一次知道锅炉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学问,之后他被工作人员带着去看样品,在现场他拿着防火砖,掂量了一下说,应该还有更好质量的,这个砖头存放的时间有点长,那个工作人员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和经验,最终买了刚刚送来的新的耐火砖。
在回单位的路上,听他给我讲锅炉里面的构造,告诉我为什么要买好的,说锅炉炉壁垮塌是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发生爆炸,那可不是小的事情,他做了一个比喻,你们单身宿舍离锅炉房那么近,锅炉一但出事,你们那座小楼也就被炸塌了,就那么厉害,也就是那时候才知道每一个行业都要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规范,并非像我们想得那样跟家里面过冬的炉子那样简单。
就是这个人到后来才知道同样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当然也是那个年代的受害者,这个人在厂里可是一个风云人物,一度成为了护厂队的负责人,指挥工厂里面的上百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除去厂长就是我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文化,所以看不清很多事情,上面觉得我实诚就让我干了这样一个营生,自己觉得不错。后来自己太出名了就让一些人眼红,产生妒忌心理,特别是曾经对我有意见,看到我成了厂里的红人,成为了他们的领导,心里不服,但不敢当面说出来。有一天中午,我在屋子里跟另外的几个人擦枪,我擦完以后举起枪对了一下准星,就是这个动作让我倒了大霉。后来派出所来了人,听完汇报以后,二话不说就把人带走了,最后蹲了十年。由于大环境有所改变,提前四年出来,却丢了工作,媳妇也离我而去,只能干临时工过日子。"
听到这些,真的说不出什么话来,历史成就了一些人,也让一些人蒙受不白之冤,他就算做一个倒霉蛋吧。
在安徽路上结识的这位潘先生,感觉他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简单地跟我说过,因为自己的一些观点让他蒙受不白之冤,到现在不想再招惹那些是非,所以对谁都不相信,而且,跟谁也不神交,你买我的书,我们约定好时间地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之后分道扬镳,再有什么事情不该我的事情,我也不会承认你从我这里买的。
正因为他在那里摆着的一两本书都是当时禁卖的书籍,而且是最紧俏的书籍,自然卖价就让人咂舌,所以也算贩卖非法出版物,他的小心翼翼就可以理解了,他的戒备心非常强,他摆的地摊人少的时候摆上一两本,一旦人多了,就会拿回来一本,就摆出一本书,而且他的那辆破自行车放在很远的地方,他放书的黑色皮包也不放在眼前,放在隔壁摊的边上,让人误以为是别人的东西,这些都是防范措施,感觉做得很巧妙。
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在摊位上摆放着一本那时候很难买到的《梦的解析》,见到那本书就感觉拔不动腿,但我问了一下价格觉得高得离谱,后来知道好酒不怕巷子深,就在我觉得贵的时候,那本书被别人买走了,自己觉得挺后悔,就问他还有没有了,他也很警觉,说那要看一下,你真的想要下周再来。至于价格没得商量,那个人买的价格就是你买价格。
就这样,到下一个周六又去哪里,好容易找到了他,问他带来了没有,他说你真的想要,下周你给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打电话给你在约定时间和地点,一手交货一手付钱,就这样把单位电话给了他,不知道这也是他考察我的一种手段,而那天他摆在那里的是几本旧书,而不是我看到的港台书籍,足以见得他的警觉性有多高。
接到了他的电话,跟我说,你那天到某一个路口等我,把钱带好了,我问他万一书里面有质量问题咋办,他说不可能有那样的事,真的有问题,你还会在安徽路上找到我,我会为质量负责。放下电话感觉跟地下组织街头似的。
自己按照要求到了约定的地点,把车子停那里,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自己还在想估计又失约了,或许他没搞到那本书,过去了快半个小时,正准备走的时候,看到他推着车子来了,见到我说,我其实早就来了,就是在观察周围没有埋伏的人,最后发现你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请你理解我的这种做法,既是对你好,也是保护我自己,说着从包里拿出书来,让我快看有没有问题。
就这样开始跟他有交往,他跟我说,往后你还想要什么书就跟我说,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给你,自己对他的这种能力很佩服,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紧俏的书籍,除去城市大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可以进到,一般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搞到。
再到后来我从他那里买了一批书籍,价格不菲,但自己觉得物有所值,最起码在那个年代自己是先吃螃蟹的人,到后来这些书借给了自己的老师和文学圈的朋友,一度为有这样的书虚荣了一阵子,谁还知道现在这些书已经变得无人问津,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安徽路的自发文化小市场也早就没有了,成为了老舍公园,再后来那里也热闹了一阵子,老舍笔下的情景再现。那个姓潘的书贩子也不知怎样了,最后一次看他是他带我去了他的一个亲戚家,说他那里有一些好书,看我有没有兴趣,我跟着他去了那个地方,感觉就是他自己的家,屋里空空荡荡,家徒四壁。
一张破桌子上摆着一些书籍,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他跟我一起离开,但是到了门口,他跟我说,“我想去找一下我的这个亲戚,把钥匙还给他”,我说好,便走了,从那时候起就再没见到他,过去三十多年了,记忆深处还是他戴眼镜,镜片非常之厚,用土话形容,跟酒瓶底一样,感觉这个人应该曾经是一个学者。
管窥一见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