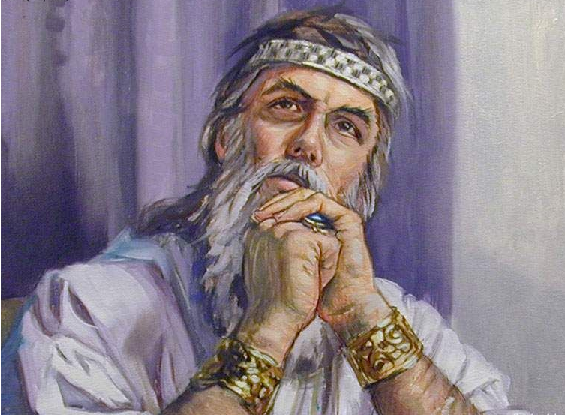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王国维《人间词话》
从王国维《人间词话》始,“境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术语。为之下定义、作解读者不可胜数。
我姑且也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此处的“境界”,是指诗人词人以现实世界为摹本,把实用性的、不美观的、丑陋的东西抛除,以充满审美性的事物为素材,在笔下构建一个不含杂质的纯审美空间。平凡世界就此成为理想世界。
所谓“纯审美空间”,是随着时令出现的天候和植物,以及与人的日常生活相一致的屋桥院塔所共同构建的。这些合适的素材,在诗学术语中被称为“意象”。
比如,一条被游人踏出的小路,路边是野花野草、湿润春泥,路的走向按照人的生活轨迹向下一个空间自然伸展。某天,因着某种机缘,路被铺上了碎石,路边多了一座茅屋。天长日久,铺路的碎石逐渐变成了石板、在一个又一个的雨季之后长出了青苔,路边的茅屋多了一座又多了一座,多年后变成了许多房屋。雨水从在路边浸润流淌,渐渐变成从屋檐流到路边小沟……一条悠长的雨巷就这样在时间的丰富展开中逐渐生成。
沈从文小说《边城》里的湘西小城,便是一处这样的世界: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①
然而,工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在于人们为实用而造物的能力显著提高。被建造的物事不再依靠着某种合理性、在时间流逝中自然生成,而是在短时间内被成批量地生产出来、布置妥当。建筑、植被,不能在自然秩序中错落有致地从容排列,只能在规划之下进入某个境域、填充某个空间。
在工业时代,获得“超能力”加持的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变成了利用和征服。曾经的深山老林不再是人们休憩、深思的天然场域,而成了工业原材料的聚集地,人们的眼光变成了计算、规划。
在这样的时代,道路和建筑是成批量规划、建造的,既缺乏生成的过程,又缺乏与整个情境的磨合——这便叫做“突兀”。此外,工业时代的产品重视实用性而忽视审美性,电线和立交桥对视野的切割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工业文明的世界里,处处都有突兀之物。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当代工业社会不会再创造出古典时代特有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例如诗歌、形而上学的理论和法贝热的复活节彩蛋。另一方面,它(工业社会)却制造大量的丑陋但很实用的东西,如机床、高速公路、轿车以及预制结构的房屋。”②
所以,在工业时代的现实中,很难找到一片完整的、现成的词境了。人们如果想在笔下制造词境和词句,只能通过心灵而不能仅仅通过眼睛去寻找素材。
古典时代的艺术家,重在高水准的艺术技能,素材则俯拾即是;工业时代的艺术家,重在一种特殊的审美能力和反思能力,能追忆田园牧歌时代人类的生存情态,能从遍地实用性中追忆、呼求审美性的建构,并将之描摹。
工业文明的世界里也不乏出色的设计师,能够在设计具有情境性的产品(如建筑、城区)时,除了努力兼顾审美性、秩序性和实用性之外,更努力为在时间中生成的种种元素留下空间——例如允许屋瓦或墙面在变旧后生成厚重感,允许爬墙虎或行道树在生长过程中参与对空间景观的塑造,允许建筑之间相互借景,允许建筑的位置、道路的走向,与山峰湖泊风向阳光等自然元素保持友好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产品中,本属于古典时代的词境依然有重新生发的可能性。只是辛苦了设计师。他如同电视剧剧组中负责搭建场景的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的一切场景都那么理所当然,然而想凭空制造一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场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如今的时代,技术比工业时代更加发达,日常生活中的工具、产品也更加抽象化了。古典和工业时代的人都无法想象,一个储物柜可以不经过任何接触性操作,仅仅使用手持仪器上的控制终端便能开启。控制储物柜大门开启的规则,则是现实中寻找不到对应物的一大批抽象的算法。
在一个如此抽象的世界上,构建诗境词境所需要的自然素材——意象,也将消失无踪。人不但缺乏构建境界的素材,更缺乏与素材互动、在素材中成长的机缘。对情境生动、意象丰满的中国古典词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代了。能够表达这个时代的诗词面貌,或许也应当像后现代的画作与音乐一样变得抽象。
①《边城》,沈从文 著,第395-396页。
②《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