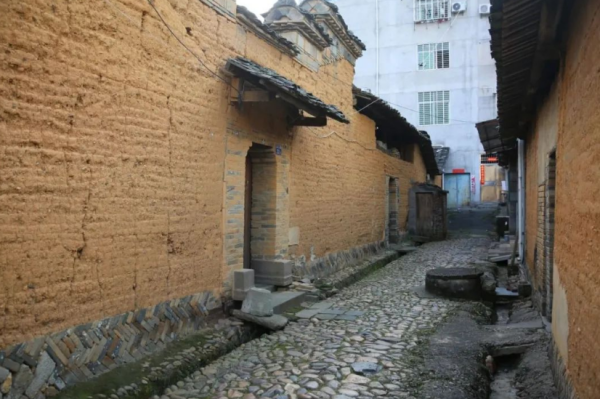我们知道,很多作家甚至大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均由诗歌开启。是诗歌带给他们良好的语感,把控叙述节奏和结构文本的能力,并持续影响他们的小说创作。而在另一些作家那里,始终坚持多文体并举,诗歌融会其他文体的现象也就更为鲜明。在此,我们择选刘全德、马召平和丁小龙三位中青年作家的小说样本进行简析,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为了扩大诗歌考察的范围,将观照对象由诗歌文本延伸至叙事文本;另一方面缘于三位作家都写诗,兼具诗人身份,他们小说的诗意成分或诗化程度相对较高,甚至通过对诗意、诗性的强化,增添叙事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
在这里,有必要先对诗意和诗性这两个概念简要说明。诗意,无疑是诗歌最直观的标识,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辨识尺度;而诗性,则是诗歌在本质意义上的提取。事实上,诗意、诗性作为一种说法,经常出离诗歌范畴,被用来广泛指称文学艺术作品呈现的诗化特征。
魔法师的药水
刘全德的《人马座纪事》是部奇书,在我的阅读经验外天马行空地展开。起初,我将它当普通的长篇小说来看,几页下来,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期待,完全被神秘、奇幻的另类叙事所填充。通读过后,才确信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面目奇异的创新性文本。多文体的跨界和联姻,童话与神话的交混,诗与史的融合,家族叙事、时空建构等等,为这本书赋予了新鲜而独特的魅力,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诗性语言的魔力让人沉迷。相对于熟悉的日常,奇幻、魔幻的场景和情节对人有新鲜刺激,却较难持久。好在本书的语言和段落非常简洁,叙述速度和场景转换也较为迅速。于是阅读慢下来,也得以梳理故事脉络、人物(动植物)关系和文本的深层寓意。
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对艺术童话极为推崇,认为童话本质上是一种解放自然的最高综合,是诗的法则,也认为童话具有预言的表现。本书的《神话卷》在我看来,就是一部暗黑风格的童话,或童话诗。乌鸦、蛇、仙鹤、魔鬼、巫师、国王、王子,各种角色纷纷登场,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交叠的时间,移位的空间,充满灵性或魔法的人和动植物之间的纠葛、幻变,令人瞠目结舌。其中涉及语言乃至万物的创生,圣经文本与中国远古神话的创造性改写,历史、文明、权力、家族、复仇等主题,隐约可见《百年孤独》的影子。《传说卷》是写实与魔幻的杂糅,空间也从上界的天马座转移到下界的地球,地理上的中原特征、佛文化元素和依稀的民国风貌,承载着故事的延续。在这卷中,诗性和童话特征有所减弱,但诡异之风又有新的表现。
《人马座纪事》无疑是一部幻想型的叙事文本,以诗化和魔化的方式构筑了一个深邃、多维的灵异时空。透过文本,作者逼人的才气、奇诡的想象及创造力都显露无遗。他就像一个配置神秘药水的魔法师,掌握着令事物变形、幻化,并发生奇妙关联的剂量和浓度。他并不刻意摹写、构造现实,然而在童话思维的推动下,一个真正的艺术世界建立起来,人的精神在其中自由穿行,历史与现实得到映现和折射。
生活滋味和诗意的调配
马召平最早写诗,以诗人身份为圈内朋友所熟知。他的诗朴素真诚,致力于乡土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诗意转化,其平民情怀和底层视角让人记忆犹新。就在诗歌蓬勃生长,有望更大提升的间隙,他却将写作的重心转移到散文上。他自觉的文体革新意识,将小说叙事中的“虚构”引入散文领域。当然,对于散文叙事的虚构化,会有不同的见解甚或意见,但毋庸讳言,是散文创作带给马召平更多的文学声誉。然而,正当众人对他的散文抱以持续高涨的热情和期待之际,他又不声不响地拿出一个个小说文本。作为诗人的马召平,他屡次实施的文体转换让人始料不及,但其中原委肯定来自他的内心。或者说,是表达欲求和不同文体之间对接、协调的结果。其实,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不同的文体在彰显不可替代性的同时,也会自行设定局限性。写作者往往根据自身喜好或表达对象的特点,进行适合自己的恰切的形式选择。
小说集《冷暖交织》,包含十个中短篇,呈现马召平写作的又一次华丽转身。文体样貌在改变,贯穿其中的却是不变的朴素和真诚。这显然是一种珍贵品质,有赖于创作者的身体在场和精神投入。如果说他的散文融入了部分小说元素,有虚构成分,那么他的小说则存在淡化情节、虚化人物、散化结构等特点,呈现出一定的散文化倾向。小说是叙事艺术,人物和故事是核心要素,戏剧性冲突强化了叙述的力度,凸显小说的文体特征。当然,这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现代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进行了全方位地革新,甚至颠覆,极大地拓展了叙事艺术的可能性。散文化的小说实践在中国也由来已久,文学史上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在弱化戏剧性之后,带来的是贴近生活原貌的真实感,以及融合主观意绪的诗意或诗性。
在小说中,马召平并不刻意进行诗意的嫁接或移植,他尊重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状态,以及人物内心的真切感受。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他说出自己的认知:“热和冷是一种生命的感受……热是生命虚无奔放的气息,而狂热之后的冷是麻木的。”缘于触觉的热和冷,产生于味觉的苦辣酸甜,这些作用于身体的各种感触,以躯体化修辞的方式,传递出强烈的内心体验。同时,马召平在营造生存、爱情、理想、婚姻的冷热境遇和百般滋味的同时,作为诗人的他,诗意、诗性的带入显得自然而然。文本中具有诗意的部分,更多体现在比喻修辞和环境描写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可以说贯穿他所有的篇章和段落。比如,《喜欢冬天的贾三》:“他们整个晚上都在亲密地私语,口含着花瓣和雨水”,“窗外那些落了叶子的树苗赤溜溜地摇摆着,像蚯蚓一样扭扭捏捏升上寂寥的天空”;《大风天》:“他们像两条挣扎着回到水里的鱼儿一样,尽情地折腾着身体”;《想起老韩》:“老韩的琴声像一块乌云,在细雨中左右缭绕起起伏伏”,等等。像以下这样的话语方式也传递着特别的诗意:
亲爱的贾三,睡在一场大雪中的贾三,他能听到的只有雪花的声音。整条街道的黑暗和寂静都被雪花吞没了。
——《喜欢冬天的贾三》
夏小辉的父母说完就走了,那是一个落叶缤纷的日子。夏小辉的父母帮着他买了灶具,清洗和整理了他所有的衣服。夏小辉的父母走了。那是一个落叶缤纷的日子。
——《艺术青年夏小辉》
这样的诗意来自特别的语感,语气和语调,以及循环往复的诗歌调式。关切的话语犹如温存的雪花,轻轻覆盖因醉酒死在夜晚街道上的贾三;夏小辉、夏小辉的父母、落叶缤纷,这些词句的重复,带来绵延的惆怅情绪。尤为特别的是,《明亮的夏天》中:“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有点像深冬时节的形状,模糊浑圆。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太阳不是大家想象的红彤彤的太阳”,这段话在稍作调整后(将天上改为殡仪馆上空),重复了三次,每次都处于人物命运转折的不同情境。这种对自然物象的描写,很好地衬托或暗示出主人公的心境。大段、长篇幅文字传递诗意的情况也有不少,像《明亮的夏天》和《冷暖交织》这两篇开头的数段文字。《艺术青年夏小辉》和《想起老韩》写作时间较早,算是马召平最初的小说实践。正是得益于诗歌、散文提供的艺术滋养,他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小说中富有韵味的叙述节奏、人物命运的跌宕、淡淡的抒情气息,整体上呈现了散文化叙事的诗性特征。总体来说,在诗意、诗情的渲染上,马召平是节制的,有很好的控制力。作为服务于叙事的辅助手段,不宜发生喧宾夺主的现象。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