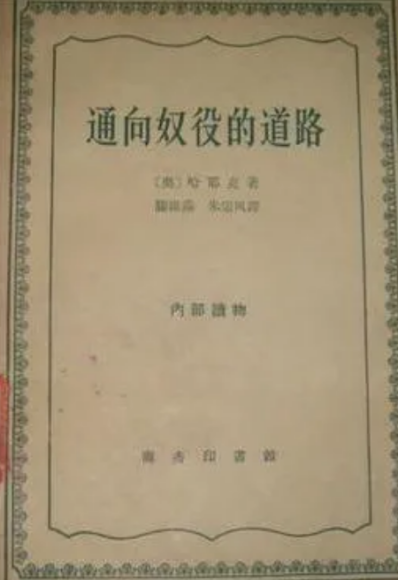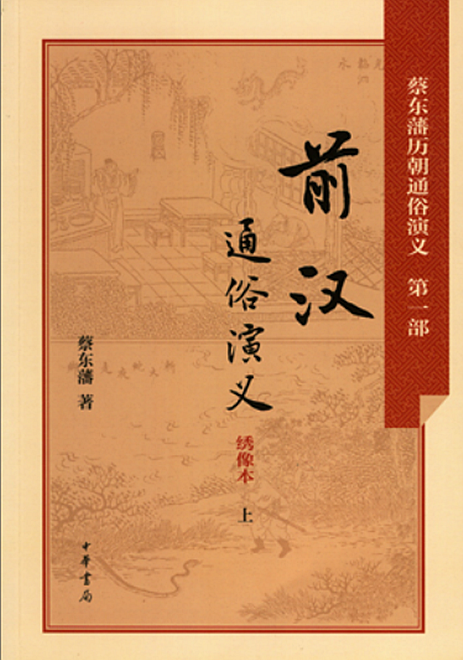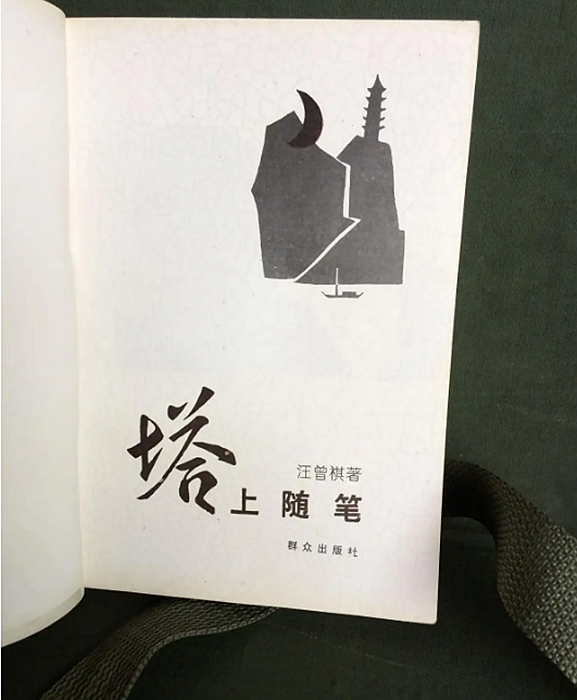对于诗歌而言,语言并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作为心与物、精神与世界沟通对话的中介或整合之物,它总是携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生命的呼吸,有效参与到诗歌情趣和内蕴的营建中。李晓恒是操持着这种带有棱角、略显拗口的语言进行他自己的诗歌表达的,或许这种语言风格正是他个人的性格气质在不经意中的流露。
《是谁耷拉了我的耳朵》那本诗集,我很早就读到了。存留我脑海的,是一种不同于当下流行的、大众化的写作态势,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是根植于自我生存的独特性体验以及个人化的传达策略。仅仅书名,就传递出一种现实生存的无奈与质询之惑。我想,那本诗集与名利无关,甚至也与他的文学理想无关,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理念,就是将诗意融合贯通于现实生存,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诗意的存在,一种通达圆融的人生境界。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再执着于文本建设,或者说疏于文本建设,而选择从根本上寻找艺术同人的现实存在、精神归依相融合的终极问题。就像海子所表明的: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当然,对于大部分的写作者而言,这不太现实,他们期待着在文本上有所建树,因而无暇顾及。然而,李晓恒的写作,提出了一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却往往被忽略。
诗歌写作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一种精神的放血,一种现实的煎熬。对于自我的苦苦追问,对于现实骨肉相触的摩擦,对于永恒遥不可及却又永不停歇的渴求,注定诗人在现世摆脱不了痛苦的纠缠。诗歌的本性决定了它与李晓恒的人生理念并不相投的一面,这或许就是他此后选择以书画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的原因。他也说过,写字画画对他而言就是彻底的放松和自由,彻底的享受。
就在我遥遥注目着作为诗人的李晓恒变换了身份,投入书法绘画的怀抱而遗憾的时候,他在并不轻松的生存间隙、工作和应酬结余下来的时间,或许就在等待回望的翘首中,用手机按键零敲碎打地写下了百余首情诗,这无论如何都要让我侧目和惊叹。因为对于他闲散、多变的个性,能持续专注于随写随扔的诗歌,实属不易。因为我知道,在写作诗歌之前,他所持有的是小说家身份,发表过多篇很有分量的具有现代派风格和意趣的小说,得到过圈内前辈的认可和表彰。
但我始终确信这样一个事实:诗歌犹如一颗光明的种子,当被不经意地点播进生命当中,就会促使诗性人格的不断成长,胎记一般再也无法抹去。而诗的,或者说诗性的,也是对所有艺术的最高抽象。甚至哲学,也散发诗性的光辉。
我在此所要说的就是眼下这本《铁的城》。一百首情诗,完满的数字,诗集名称却充满冰冷、禁锢的压抑感。在《是谁耷拉了我的耳朵》中就有很多首情诗,有着桃花的娇艳、浪漫和对世俗的反抗与超然,这本最新的爱情诗集又想阐述怎样的理念呢?通过细读,我看到李晓恒展示的情感世界的万千姿态,渴望、失落、期盼、幻想的种种情境,更感觉到人类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在现实生存的重压下,表现出的那种执着和热烈。他不是完全具象地、单一地书写爱情,或爱情的对象,而是把爱情,人类精神世界最高贵、最纯粹的情感放置到人的整体生存的框架中去考察和思索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这本诗集对他一贯追求的自在圆融的人生理念的延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通过这本诗集唤醒人们爱的意识,抛却生活中的虚伪、狡诈和功利,在铁一般冰冷、强硬的生之围城里,种花种草,温暖、软化我们的心灵和规囿我们的外在环境。
“铁的城”,无疑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给予的一个绝妙隐喻。而人的情感或者爱情,就像在冰冷囚禁下涌动、奔突的烈火,未能逾越界限,却始终燃烧不息。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带给人们的精神上的痛苦抑或麻木,让我们更多地关注外在的东西,社会强加给我们层层叠加的面具或缀饰,从而忽略了内心深处最原始、最纯粹的情感冲动,生命最真挚的欲念和渴求。这或许就是《铁的城》这本诗集并不执著于诗歌本身,却又超出诗歌文本意义的价值所在。
作为庞大社会机器中的一个细小部件,我们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奔走在自我生存和生命实现的狭小空间,无奈之举就是被动地接受了被赋予的多重身份,变换着无数的脸谱,层层叠掩的表象之下,却都存在一个真实的竭力彰显却难以自明的真我。如果深究艺术创作中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内心诉求,我们就能同样地推延并确认,李晓恒和他的小说、诗歌、书画创作,各类艺术的实践,乃至种种努力,都是对这个真我的不断的剥离和敞明。
2015.10.21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