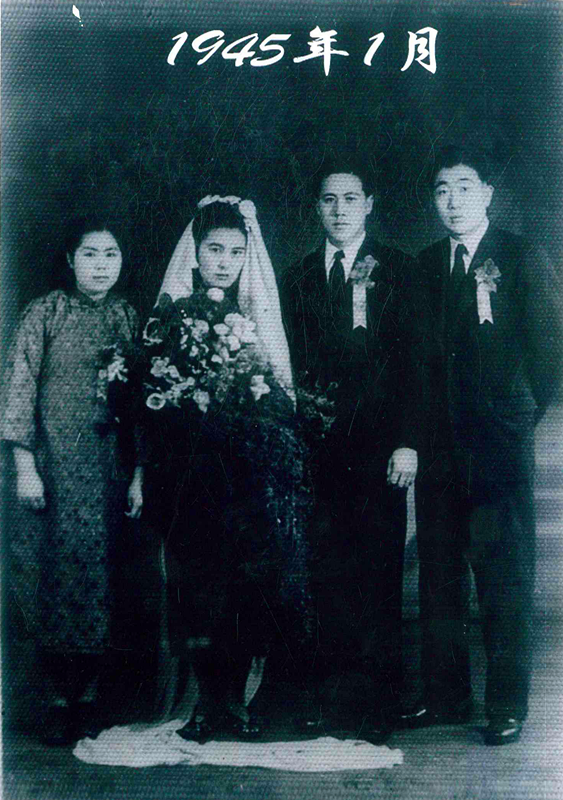我偷过!
很刺激……
在共和国最热闹的那十年,也是我一生最热闹的十年,我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就用“热闹”吧……
某天晚上,天挺热,大家都睡着了。突然,传来一阵锣鼓声,还伴随着嘈杂的口号。我一向睡不沉,溜下床趴窗上一看,只见市立医院门前人头攒动,锣鼓声就来自那里。我蹑手蹑脚穿衣出门,一路小跑赶去看热闹。
医院门口已聚集了一堆人,大部分都是被锣鼓声吸引来的。我到跟前时,看见几个年轻人把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推推搡搡弄到桌子上,有三个人也上去了,两个一左一右抓着花白头发的胳膊,向上一撅……我就看不见了,我太小,大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三个。中间那个穿一身绿军装,用戴着红色“胳膊箍”(在未来的若干年,这个“胳膊箍”一直缠绕着我,又引出多少故事……)的手,抖抖的把张纸凑到眼前,大声地念着什么,我听不懂。另一只手直直地伸向花白头发,不是掐着脖子就是揪着头发。不一会旁边又是一阵骚动,看热闹的人们呼啦啦往那边涌。一帮青年人拖着一个什么人过来了,人们拥挤着互相推搡着,我被裹挟着一会这边一会那边,直到我小哥一把揪住我的胳膊:“走,回家!”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昨晚是青岛医学院的造反派,打倒了一个叫“走资派”,还一个叫“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当然,很快我就知道的更多。我知道凡是单位的领导都叫走资派,还知道凡是上点年纪的搞技术的都叫反动学术权威,还知道了那个红色胳膊箍叫红袖章,戴上它身份就不一样了。
破四旧开始了,对门王先生家被抄,戴着红袖章的人一趟趟地往楼下搬,有些东西搬出去扔在门口,有些却被人直接拐过弯顺着旁边胡同拿走了。
一个偶然,纯粹是偶然,我发现抄出来的书都被烧了。在大学路,我把衣服扔到抄家抄出书堆上,若无其事地看热闹,然后趁人不备,假装拿衣服,包起几本书就跑……这算是第一次偷。但比起后来的事这根本不算什么,之后的偷才是真正的偷。
市立医院对面有个大碉堡,正面被一个大宣传牌子挡住,侧面是围墙,院子里是一家橡胶厂,堆满了旧轮胎。一次玩抓特务游戏时,我偶然发现了一条缝,可以钻到碉堡门口,而那个铁门能打开,于是这里就成了我的藏书房。现在听到有人说谁谁是什么藏书家我就想笑,你那叫什么藏书,当年我那地儿才是真正的“藏”。
打扫是个大工程,里面除了碎砖瓦石块,还有几根胳膊粗的竹子。竹子派上大用场了,劈开后用铁丝绑起来做成书架,挑选些比较成型的砖垒成夹墙,把那些垃圾通天填进去,空间还真不小。整个施工过程是借了邻居的手电筒完成的,那时候手电筒是家用电器,不可能经常借。要想在里面看书,几乎不可能。白天还勉强可以,因为碉堡的射击孔是用砖头堵住的,我抠开了一小块,凑到近前还行,但下午光就很弱了,晚上更是一团漆黑。最先想到的是手电筒,得想办法弄到钱,因为一个手电筒要两块多。
住在观象山周围的人应该记得,在后来的青岛六中那里,最早是市北烟斗社,装烟丝的小碗是用铅做成的。工人随手把铅渣子泼在山坡上,液体的铅比重大,浸透到石头缝里或土层深处。不知谁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漫山遍野都是挖铅大军,我也混迹其中。
除了挖铅,帮人包粽子,糊火柴盒,还跟着我小哥下海捞冻菜,但很快我就不去了,因为小哥剥削我,他把卖冻菜的钱拿去装他的半导体了。我又跟着挪庄的刘大哥去捞过几回,但刘大哥给了我五毛钱后告诉我,以后别跟着他了,十二中对面的“大岛子”水深流急,他怕出危险,毕竟我才十岁……包粽子最实惠,尤其是有一回给交际处包,一分钱一个,我一天就挣了六毛多。
我很快就有了手电筒,那一刻真是爽,头一天晚上一直看书到老母亲喊我。那时候晚上睡觉都很早,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开着灯还费电,母亲到九点多就开始挨个叫,她嗓门大,我在碉堡里就能听见。时间不久问题来了,电池没电了……做蜡烛,这主意不错。拿着家里蜡烛研究半天,觉得不难,可是蜡从哪找弄,只有一个办法……“偷”。
现在知道那个术语叫“踩点”,踩点还真是费工夫,没几天就瞄准了几个点,都是土产杂品店。一个在市场三路,一个在莘县路,另一个记不清哪条路了,大约在火车站附近。因为这三个店,都是用一个分成若干格子的大木头盒子盛着不同的货物,摆在店门口。淡紫色蜡的做成扁方长条状,中间还凹进去半圆形的槽,在格子里明晃晃地躺着。第一次偷东西,比第一次偷情还紧张,感觉就要死了。我站在火车站附近的那个店门口,身体靠在木盒子边,假装随手把衣服放在木盒子上,正好盖住那些蜡。正当我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头上挨一鸡毛掸子。我眼睛只顾盯着老头售货员了,旁边还站着一个阿姨竟没看见。不记得我是怎么脱身的了,总之好几年都不敢往那个方向走。市场三路和莘县路都得手了,而且不止一次。
棉纱在那个院子里的橡胶厂就有,用马口铁卷成筒,图钉把棉纱固定在木板上,棉纱穿过圆筒保持在中心位置,把融化的蜡浇进去,等待蜡变成固态,成了。当我把所有的蜡变成蜡烛,那份成就感直接爆棚。
但我还是失败了……蜡烛根本就点不着。我把蜡烛头朝下点着棉纱,着到蜡时火就灭了。
后来我大哥从单位拿回一桶煤油,我成功地做成了一盏油灯……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重操旧业又干了一票,这回我有了俩同伙,那是开始学画以后了。莱芜二路有个做石膏像的小作坊,里面都是些让我们垂涎三尺的石膏教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从后墙爬进去,把石膏像递给同伙,再由同伙拿到门口交给接应的……那晚偷了一个哭娃一个亚历山大,原本还有个海盗,可惜石膏像还没干,往外递时碎了。
那俩同伙,一个后来当了某法院的法官,另一个是某艺术学院的院长……
20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