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桃花,容颜逼真,开得端艳。
路边、桥上、岸畔、水中画舫,
与桃花的距离恒定。
所有与它们亲近的事都已叫停,
包括仰首驻足的文墨骚客,
只可远观而不能近前。
四月在花瓣里抱成一簇,
五月未获许可,不得通过。
画家的律法简明扼要:
凡桃花者,不凋零,不结果,
自然也不犯桃花劫。
终获郊游的小姐,穿红衫绿裤,
她不骑马,不坐轿,挎个竹编的提篮,
学垂地的柳枝,扭一扭,摇三摇。
早已日过三竿,
却怎么也踏不上眼前的万年桥,
眼睁睁一竹篮栀子花,
被三百年风雨,吹着开,散着落。
那个买折扇的,
已经来过,还是走了?
柜台后三个穿长衫的老板,
也许是伙计?向一个方向伸长脖子,
像一把展开的折扇,
巴巴地等不曾出现的生意。
我说买折扇,最好两面都画着江南;
他们看也不看我一眼,
手指一段巧妙的距离。
抓药的先生一大早出的门,
郎中昨夜开的药方,揣入袖口。
我看他挤在戏台第一排,听得入迷,
如果有机会,或许上台唱几句?
他脑袋摇晃,不曾停止;
夫人的病,他说不打紧,
天黑之前不会再生新的毛病,
郎中既承诺药到病除,便不是要命的大病。
可是日落之际,匆忙返城的人流,
没人见他的行迹。
于是,看不见的一切,
值得推敲和尊重。
比如太阳的照耀,
一定从四个甚至更多方向,
因为,在固定时刻的固定时空,
所有的山、房屋、树木、船帆以及人群,
都失去了影子。如影随形在这里是个谬误。
或者正好反过来,我们眼见的事实骗过我们,
那些直直站立我们面前的正是阴影本身。
金银店铺的抽屉没有金和玉。
侧向我们的房子里没有生命,不能居住。
鱼篓没有鱼。端着的酒杯没有酒。
唱戏的张大嘴巴,却无戏词。
跪在地上竖着耳朵听圣谕的什么也没听到。
马从姑苏台一口气跑到金门不气喘。
精致的小人物挑两只大大的空桶,
却累得弯下了腰,
因为无论过去多少岁月,他不得移动半步。
其实我们冤枉了画家,
鱼就在背篓里,还活着,
背鱼篓的伙计跑在回饭庄的路上,
不用担心错过吃鱼的时刻。
酒是有的,一艘靠岸的船载满陈酿,
我们只需明白那只是一小截距离,
可喝一口酒却要消耗漫长时光。
有把折扇画过我要的江南,
三个出神的伙计同时沉思默想:
折扇终究躺在第几层抽屉?
费思量的是那顶四人抬的花轿,
里面是否坐着迷人的新娘?
至少,山塘街的几千号人想看看她,
食肆茶寮的闲杂人等探出身子,
像遇见多年未见的辰光。
可是轿帘垂着,密不透风,
只有鸣锣的催促赶路,
春光撩人啊,无人让道,
轿子挤一挤,晃一晃,停一停,
不知多少日子才走得出七里长街。
也许此时花轿本是空的,从一开始,
叛逆的新娘便骑了马,选择另一条小路,
早早会了等候的新郎。
什么是永恒?画家给了我们明示:
看看那些望东望西的人就知道,
我们千百年伸头缩脑什么都没改变。
可是一万两千人最终去了何处?
他们甚至无法留下姓名。河把大地分成两岸,
我们看不到水,也寻不见光,
自古及今,一成不变地流淌。
山站在远处,长高或下陷了几寸?
没有关系,它始终用高度回应海面。
四百条船去了北方还是南方?
两千间房屋和五十座桥梁还剩多少?
才两百五十年,它们被推倒过多少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万物之灵?
虎丘塔前仰后合,笑歪身子。
灵岩山麓,峰岩和鸣,
松涛竹韵,辰光匝地。
一盘围棋,眼看局面就要分明,
鹤发童颜的老者举起终局的黑子,
停滞半空,三百余年都未落定。
忽听得身旁的松柏,一枚坚果坠地,
起起落落滚去了汉唐。
写于2012年
整理于2020年1月
参见作者更多作品
参见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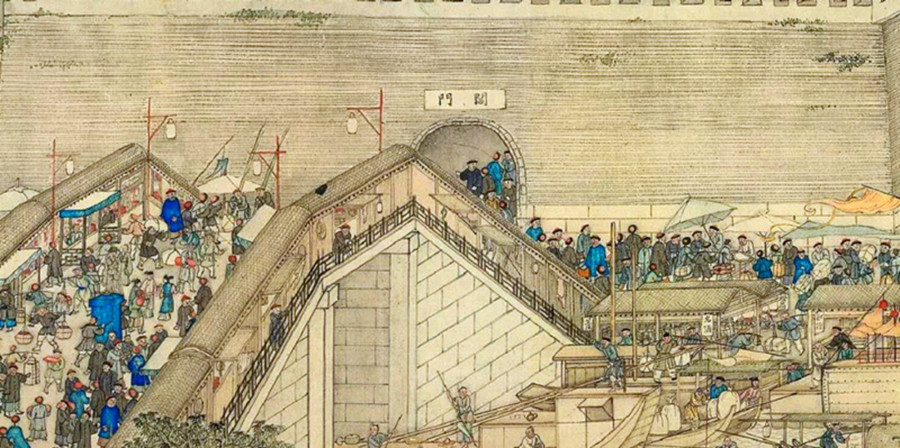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