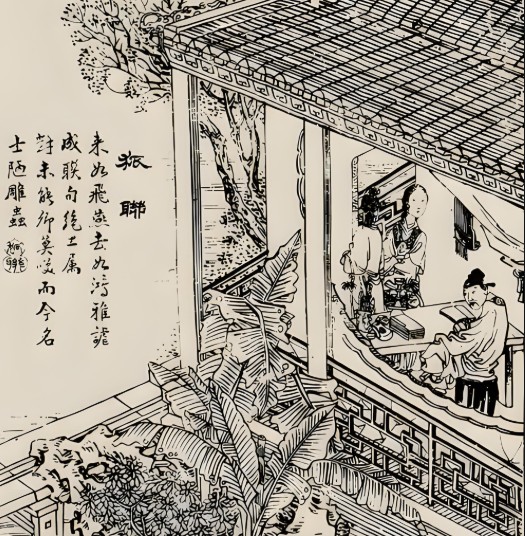其实应当与我共同记住这个日子的人,就青岛市而言至少不下二百多人。1959年9月11日,岛城200多名青少年应召支援山区建设(实为稻粱谋),到待开发的临沂地区去当乡村教师,我时年17岁。
当年9月10日晩,200多人在青岛火车站集合,乘慢车抵达中转站益都时天已拂晓。稍作休整后,编组改乘卡车沿崎岖山路南下,一路颠簸,约中午时分在沂水停车打尖。大约下午5时左右,车队从沂河桥头的大槐树边缓缓驶过,终于结束了我平生首次离家的长途旅行。灰头土脸的同学们一个个从车上爬下,活动着早已胀麻的腿脚。
临沂市教育局是这次行动的主办者,它坐落在离政府不远的南北大街上,坐东向西,灰瓦平房,门前有一米多宽的排水明沟。路的北端正对着政府的大门楼,两扇木质大门已黑漆斑驳,像旧式的衙门。南端不远处即是郊区,那里有著名的烈士陵园,罗炳辉将军就长眠于此。再往南去,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
集中培训也是实习待分配的二十天,吃住都在当时的临沂师范学校内,据说当地乡村教师完小毕业就算是高学历,我们自然被视为“高知”,实习并无障碍。闲暇时还可以打打乒乓球,与临沂一中的学生们一起踢踢足球。岂不知组织上除了看档案之外,还利用这段时间遴选有用之材,我曾经两年代表青岛四中足球队参加过全市中学生足球联赛,所以很自然地结识了临沂市体委的徐老师和省足球队下来选材的领导,于不知不觉中埋下了改变一生命运的伏笔。
我在青驼乡山北夹村小学任教三个月,便奉调进城,在朝阳小学当体育教员,成为我们这批人中1%的幸运者(只有两人进了城),但那段阅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青驼乡距市区90华里,是当时临沂市最北端的一个公社(后划归沂南县管辖)。北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孟良崗。山北头村在青驼乡南18华里,一百多户人家,依山傍河。小学只有一、二年级各一个班,每班二十多名学生都是本村人。一年级由本村民办教师郑玉发任教,他15岁,高小毕业,已任教一年。二年级归我教。语文、算术、唱歌、体育都按市统编教材上课。我的学生小的十一二岁,大的十四五岁,男女各半。班长王廷宪15岁,小名叫傻子,陪我在一铺土炕上做伴过夜。校址原本是一地主的宅院,北屋六间,土坯草顶,打通后改为二间教室,东厢二间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院子长约等于两间教室,宽约五米,杂石垒起半人多高的围墙内就是操场,可转圈跑步或做游戏。门楼过道放些干草秫秸杂物,三块砖支起便是炉灶,用于烧水,燃料是学生们奉献的玉米秸、棒、秫秸和杂干草。
当地百姓的草屋均不设烟道,袅袅炊烟都从门窗散出,“烟暖房,屁暖炕”的口头语妇孺皆知。村内有郑、王两大姓氏,书记郑立四十多岁,辈份很高,大队长郑玉礼三十多岁,是村中最高长官,我一日三餐在郑老师家搭伙,每月交8元伙食费,配给粮每月一次到六里路之外的中心粮店去买。郑老师父母约四十多岁,一姐十八岁待字闺中,一弟郑玉财13岁,是我的学生。那年头正是三年灾害的前夕,人民公社尚在,但公共食堂已散伙,各家自起炉灶。主食是地瓜、高粱煎饼,煎饼上带着一层磨不碎的地瓜蔓梗。少许黄豆上碾轧扁,伴以地瓜萝卜煮成粥便是改善生活,油、肉、蛋已极罕见。食物数量尚可裹腹,但总感觉肌肠辘辘。百姓用水从井中提取,还可从村外河边沙滩上挖坑渗得。村里人平时只喝生水,放在瓦壶中烧热叫做喝茶,有客人来时,就地采些茶树叶子放在壶中烧开,叫做喝大叶子茶。
学生们除了上课之外还必须劳动,拾草、担水,挣工分等。到田间劳动称为“下湖干活儿”,估计可能此地祖辈多湖,称谓沿袭下来,我习惯说“下地干活儿”受到嘲笑,他们说“下地”是指死后入土。
贫穷的主要表征是物资极端匮乏,学生们穿一件空心棉袄过冬已是不错的家境。教具除粉笔和一只哨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计时靠鸡鸣和日影,但人们自身的生物钟却十分准确。唯一的乐器是我从青岛随身携带的一只口琴,每周两节唱歌课,学生们的发音总带有浓厚的梆子味,不同于我们听惯了的外国民歌200首。识字、写字、算术难不住我的学生,为此我的教学进度大大超过了大纲规定的要求,曾因此受到过中心小学领导的批评。
记得初冬的一个中午,风和日暖,班长提议全班同学到村外打栗子,抓野兔。我第一次认识了栗蓬是带刺的,核桃挂在树上外型像梨。正当大伙兴高采烈地返回学校时,不料中心小学校长带五六个老师来观摩我的教学。偏巧当天没备新课,一时间慌了手脚。学生们也没见过这个阵仗,纷纷交头接耳。情急了灵感也来了,急中生智,我把昨天上的一堂课重演了一遍,生字领读默写带提问,同学们配合得天衣无缝,课后校长从怀中掏出马蹄表一看,整整35分钟。现场点评,全面表扬。但我追野兔时的大汗,仍不停地沿腮而下,个中的奥秘只有天晓得。
那时村中没有电话,与外界联系全凭不定期骑自行车来的邮递员。距山北头一华里多的石门村小学是乡中心小学与我保持联系的中转站。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凡有会议通知,必是石门小学老师步行来通知我,然后再结伴去青驼乡,十八华里山路大约需步行两个小时,我一生走路的“行如风”大约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卧如弓”的习惯可能也与那夜晚睡在凉枕上“当团长”不无关系。
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全市公办老师大集中,去市里参加三干会反右倾。因为两年前我曾目睹了青岛四中我所敬爱的校长和老师沦为右派分子的下场,更何况我的家中有三人被打成右派,自己一宿之间由“革干家属”变成“右派子弟”,断了生计而不得继续升学,所以打定主意只听不讲,免得引火烧身。开始动员学习倒也平和,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急转直下,人人自危。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是祸躲不过。进入小组讨论发言阶段,人人必须表态发言,提意见,找不足,为的是三面红旗更加伟大。不想同组来自青岛十中的同仁发言,无意中把我牵连进去。他姓陈,名字记不得了,左眼永远蒙着纱布,两行白线挂在耳朵上,有人称他为“独具慧眼老师”。他说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举例说明,他引证了曾经发生在青岛四中操场上的一件事:为炼焦炉守夜的一名高二级学生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时年19岁,外号叫黄毛,因我是四中毕业,他便让我当证明。我明知确有其事,但又怕祸从口出,于是便含糊其辞地说好像听说过这件事,但未见官方正式公布的死因。这下子不得了,全组火力一下子集中到独目老师身上,我也脱不了干系。大会斗小会批,逼着写检查,最后只能承认污蔑三面红旗,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而我是协从,作了深刻检查才算蒙混过关。但也早已惊得三魂出窍七魄无踪。自那以后,再未听到过独目老师的下落,不知他是否熬过那场灾难。
我因会踢足球,早已被市体委领导相中,年底之前即奉调进市区城关朝阳小学任教,同时担任临沂市少年足球队教练兼队长,参加了地区足球选拔赛,继而代表临沂专区足球队参加了在烟台举行的全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在14支球队中获得第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前三名是青岛、济南、烟台)。我以独进13球的表现,成为临沂地区足球史上的功臣,次年3月即奉调进入山东足球二队,开始了我的足球生涯。1961年夏我随队调入青岛体委运动科,曾见过同去临沂教书的黄玉琴同学,她已是青岛冶金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了。后来,听说同去临沂的二百多人,有人当兵、升学或另谋职业,也有留在当地成家立业的,但始终不知独目陈老师的下落。每当追思往事,我心中便惴惴不安。
一晃35年过去了,1994年我因公务赴临沂,又踏上了那片土地。朋友们特意安排我去山北头村寻旧。到蒙阴的公路还是那山条,但路面拓宽了三倍以上,自徐公店往东,公路直通山北头村,小学已迁到村边,红瓦砖房,玻璃门窗,初具规模。旧校址尚在,但已荒芜。当年的傻子班长,是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早已子孙满堂,当年为我操持一日三餐的郑大娘已经病至不起,但还记得当年的吴老师。郑玉发老师在沂南县城工作,郑玉财和妻子芦苇花当年都是我的学生。留在村里的学生大都五十上下年纪,纷纷聚拢,嘘长问短,他们都还记得我,但都异口同声说老师讲话太快,他们大都听不太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站在村头,寒风袭来,往事历历在目,耳际回响起李叔同的《送别》“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觥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我的独目同学,你还好吗,我的二百多位同路人是否还记得那年的“9·11”?
2005年元月5日
吴胜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