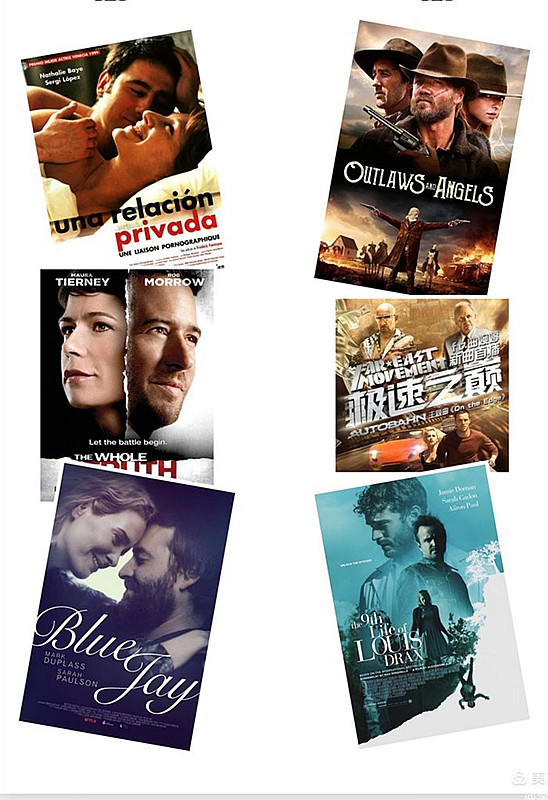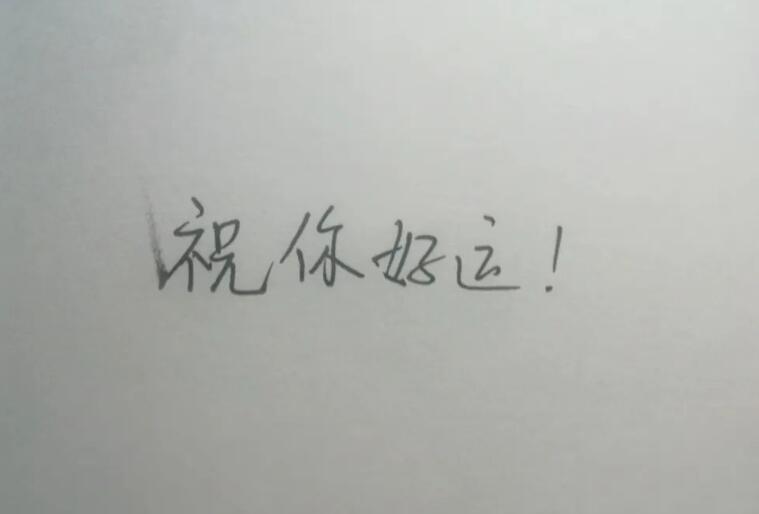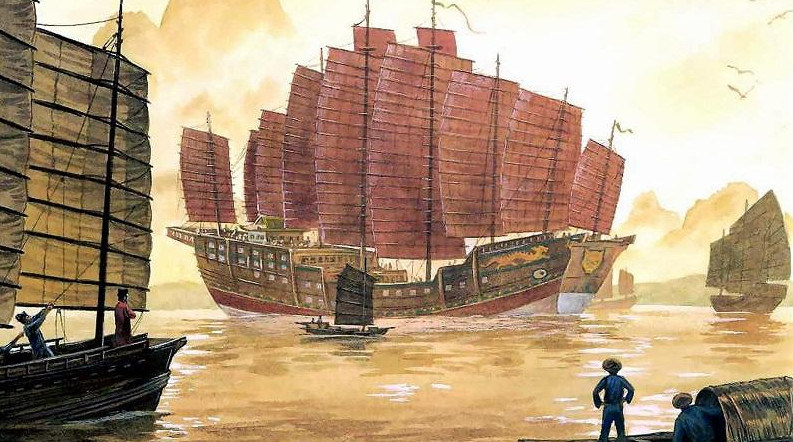我的摇篮在召唤我
凡喜欢离群索居的人,都像单独迁徙的鸟一样,是孤单的,危弱的,乃至凶险的,但这么做终究是有无法抗拒的理由的。
米什莱在《夜莺的迁徙》里借着夜莺之口回答说,“我要动身远行。别的鸟儿可以留下,它们不需要东方,而我,我的摇篮在召唤我……”
是啊,我的摇篮在召唤我。一切向着旷野的,向着大自然怀抱的,向着遥远的原始记忆几近盲目地不断靠近的,不可遏止的内驱力,无不是响应摇篮的召唤。这种内在驱动力在有些人来说是太强烈了,以至不避失群孤单和弱小无力的危险。
在这向着摇篮迁徙的凶险途中,有多少一只一只孤单的夜莺遇险遇难了,并不都能平安到达迁徙或栖居地,但却前仆后继,世世代代都有鸟这么做,也有人这么做。
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人类有集体的童年。无法免于记忆。只要活着,总有一些记忆留下来。死后是否还有记忆,我不知。
小时候,我的天堂极小;五十岁以后,我的天堂同样极小。小小的天堂就是小小的摇篮。祖母的菜园子——童年的百草园;一条名叫黄崖谷的小山谷——历经半世沧桑終相遇的伊甸园;一个名叫苇河的荒萋萋的小村庄,我的圆梦园——耕读梦的栖落处,无数破碎镜像的缝合与衔接处。
我不否认我生来喜欢孤独乃至孤寂的生活。康德说,“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的帝王。”在我独自享有的小小的天堂里,的确如此。
个人的童年记忆,尤其是持续一生的精神性,乃至潜意识或无意识性记忆里,应该存留或折射着部分人类整体性的早期记忆,这一条线索我至今并不十分清晰,只是或然性的探讨,未必会有什么结论。(2018.11.18)
黄崖谷
我住的小山谷,本属瞪羚谷的一个小褶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
一天,红婶来我院里串门,我问她这个小山谷叫什么名字,我房背后的小山岗叫什么名字,对面的山又叫什么名字?
红婶被我问得愣怔了一下,随后就口给我回了一串名号出来,说:黄崖(nai)渠,黄崖卡,黄崖根,黄崖窝子……
之后我就喜欢上了黄崖这个名字,管这个小山谷叫黄崖谷,管房背后长满橡树和松树的小山岗叫黄崖岗,管大石崖小瀑布那里叫黄崖岭。(是的,我不愿意用秦岭、终南山这么大这么大的名号,我喜欢小地名,哪怕是杜撰的。)
极小的山谷,日常在这里往来活动的就我一个人,很少有人来。离村子和水泥村道那边并不远,但是,因为有树木竹林的遮挡和掩映,我看不见那边的人迹和屋舍,那边也看不见我的小院和小屋。
村子那边平常也很安静。村民都搬到山外新村里去了,只有三几位舍不得离开老屋的老人留在村里,还有几位租住的修行师父和居士,还有一家农家乐。村子那边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嘈杂的人声车声传过来,是进山游玩的游客们。偶尔,也会有好奇或寻幽访隐的人绕过来,问东问西,东拍西拍。
我极少到村子那边去,也绝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那里去串门、造访与参拜,一月四十去集镇上采买一次生活日用品。
我像掩耳盗铃一般,假装这条小山谷就是远离喧嚣尘世的荒山旷野之地。但它确实也像,尤其是在雨雪雾霭天气里,那种茫茫苍苍、杳无人迹的感觉,仿佛我曾经熟悉的城市、村镇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一般。我的世界就只是这条与世隔绝般的小山谷。
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好时光。因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报刊杂志,没有各种聊天与聚会,我不再被动接收那些铺天盖地而价值观极其混乱的各路信息,多年来满脑袋碎玻璃碴一般难以整合的尖锐刺痛的破碎感与自相冲突感得以修复,内心日渐单纯明亮起来,目光柔和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那时,我真切地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寂然之美,人的内在与外在也没有矛盾冲突,无是无非,没有过度劳碌和忧惧,没有过多的物质需求,一切日用都可以因陋就简,整个人的身、心、灵是一体的,浑然的,自在的,愉悦的,欢畅的,灵醒的,通透的,简洁的,纯真的,烂漫的,和方圆百来十步日常活动范围内的水光山色、动植两界所有生灵之间的相处,都是亲切的,熟稔的,信任与怜惜的。
当我每天,无论清晨或月夜,和我的猫狗们在房后那道小山坡上奔跑,追逐,嬉戏的时候;无论阴晴雨雪,带着它们,沿着那条常年铺满落叶的小径去汲水的时候;跟我的竹林、喜鹊、松鼠、野猪、花草、树木、蝴蝶、萤火虫、纺织娘、人面蜘蛛们随意说话的时候;捡拾落叶,制作标本的时候;看到野猪邻居毫不嫌弃,毫不客气地吃光我种的一小片土豆的时候;看到我的喜鹊夫妇每天理直气壮地来跟我要早餐的时候……我像回到童年一般,虽满头华发,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天真烂漫,既无以言表,也无需言表。
不独终南山如此,大自然对人的精神慰藉和灵魂荡涤,哪里都是一样的。我的黄崖谷就是我的波林根、提契诺,就是我从此带在心里的小天堂和伊甸园。(2018.11.25)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