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沟示意图
上次说到外祖父家是沂水县朱家沟村,那个村里刘姓居多,但不都是“关顶刘”一支,还有别的支系,至于是什么支系不太清楚,也从未打听过。当时村子处于所谓“根据地”,村里主事的领导好像叫刘成顺,就是另一支系的。还有一位姓牛(叫牛月亮,当地话,牛读作you)的支书。
当时城里的汉奸经常到村里来派公粮,日本兵也经常下来扫荡。每次来,村里便鸡飞狗跳。日本兵抓住鸡,用开水烫烫,屠撸屠撸毛就吃,看得乡亲们直呼恶心:这就不是些人种!那里虽说是山区,却多是丘陵,没有什么像样的山,每次遇到扫荡,大姑娘小媳妇,脸上抹上锅灰,吓得浑身发抖,躲在河沟土坑里。
因姥爷做生意,家境比邻居族人要好,所以母亲得以读私塾,又上了几年小学。说起童年在私塾学过的内容,年已九旬的母亲开口就能背诵一大串,百家姓、三字经,还有现已不熟悉的《庄农日用歌》:“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
不过家境殷实,也为在日后的土改埋下了麻烦的祸根。划成分时,外祖父是下中农,按说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一类,但工作队不管这些,对村里的地主不管不问,却冲着外祖父下手。可能是地主家只有土地,而不像外祖父做生意那样露富吧。工作队把姥爷家里的老古董洗劫一空,把姥爷和二姥爷弟兄俩五花大绑,开始绑在当街的碾棍上示众,乡亲们抗议,说这样还怎么碾粮食?所以又被解送到区里。家里人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上有大姐,但已远嫁到沂山深处,即便是回来也不能做啥,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妇,没见啥世面;弟弟妹妹还小,于是她壮着胆子去给父亲和二大伯送饭。后来,又拉着已过继给二大伯家的五姐到区上去讨说法。姐妹俩,一个十五六,一个十三四,一路打听着,饿了就到人家讨口饭吃,几经周折,多次去区里讨说法。区长也姓刘,很和蔼,得知情况后,答应放人。后来,历次运动的内查外调,相关外调人员都少不了到村里和县里来折腾一番。一九七零年疏散人口时,我正在姥姥家,就看到父亲单位一位熟悉的蒋西林叔叔来村里搞外调。
母亲这一辈的人很多,一九四五年前后,有几十位兄弟姐妹先后出来参军(究竟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或是解放军,当时的称呼比较乱,年代久远,母亲记不太清)及其相关机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母亲读了三年私塾,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所以部队文工团招她入伍,但她年龄超龄,于是哭鼻子。部队一个大姐过来安慰她,给她出主意,改小年龄,于是以12岁的年龄入了伍。入伍后,发现不适应,又调整,先后在军工厂、随军书店、部队医院等单位,最后在三野九兵团廿一医院做护士。
当时村里的姐妹参军后,大都嫁给了部队上的干部。母亲一位堂姐参军后,嫁给一位年纪很大的干部,这人参军前本人就是地主,两人差了十多岁还是二十岁。我在太平路37号团市委工作时,某年夏季某日,正在办公室,忽接一电话,来电话的就是这位姨妈,当时是泰安某学院政治部负责人,她带车来青岛旅游,车子没油了,停在栈桥街头,要我去找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刘维理。我一听吓一跳,刘正是分管团口的书记,是我们单位的顶头上司,这么点小事哪能去找他呢。姨妈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我说,你就说我来了,说我的名字就行。我将信将疑,惴惴不安地走进当时海边的灰大楼(后拆掉)市委办公楼。记得当时是台风过后,靠近海边的办公楼内还有水渍,通过秘书找到正在开会的刘,刘从会议室出来,一听到我姨妈的名字,赶紧问姨妈在哪里,接着跟我走出大楼,见到姨妈后,恭恭敬敬地说了句什么。后来才知道,刘书记当年是我姨夫的警卫员。当时刘跟机关很多人一样,就近到栈桥西边的海水浴场游泳,气温适宜时,游泳的人多,他不怎么显眼,但秋后,尤其是初冬时节,他还坚持游泳,就很显眼了。我当时也坚持了很久,直到初冬外出出差才中断。从姨妈来青那次之后,又见过刘几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并没有说什么。直到他后来患病离世。五姨也是嫁给一位军官,后来文革期间,所在城市连云港武斗很厉害,动用了重型武器。夫妻二人均是市里的当权派,是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一家人不得已逃到青岛避难,住在我家狭窄的空间里好长时间。
母亲所在部队驻扎滕县官桥期间,外祖父曾前去探亲。外祖父对接待的干部说,要来看儿子——重男轻女的心理吧,大概觉得说来看女儿有点难为情。接待干部问你儿子叫什么,外祖父说了母亲的名字,那干部很好笑,于是故意大声吆喝,喂,×的父亲来看他儿子咯!大家哈哈一笑。
在认识父亲之前,母亲部队里有位同乡,叫陈什么,后改名益三。当时追求母亲,但被拒绝。理由是,母亲说那人口音太重,说话不好听。后来这位战友找到意中人,某日,带着女友向母亲炫耀。母亲却不以为然。很多年之后,这位战友随部队南下,在上海某单位工作。
部队有一位炊事班长,姓汪,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体弱多病,对母亲很关照,母亲认他做干爹,汪班长退伍时,要带母亲一起走,母亲征求指导员(姓顾)意见,顾指导员不同意,说,他那样穷,孤身一人,自己生活都难保证,你能跟他走吗,最终那人自己退伍回乡了,据说后来饿死了。
还有一位财务股长,带着很大一捆钞票叛逃,但没追回来,不知所踪。
跟母亲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位老战友,也是同县的同乡,相距不远,肖丽阿姨,到老年一直与母亲有来往,住在云霄路。
父母在青岛安家后的几十年里,沂蒙老家的亲戚经常来,不像那些做了大官的亲戚,对亲戚拒之门外——似乎是回避什么——而母亲无官一身轻,来者不拒。来的都是客,来,多数是为要东西,虽父母不富,但比乡下还是好很多,那时物质匮乏,乡下尤甚,所以走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咸鱼干(鳞刀鱼)、小海米总是标配。也有来看病的,父母从医,多少便利一些,但也有达不到满意的,他们以为,只要得了病,到了青岛他二姨/二姑/二姐这里,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实不要说那个年月的医疗条件,就是搁今天,医院、医生也做不到有病必治,有治必愈的。某年,我上高中,老家一位表兄带着重病的孩子来青求医,虽经父母多方联系名医,终因病入膏肓而不治。表兄大为不满。也无奈。但他坚持要送孩子回去落葬,不想在青岛火化。只好借一辆地排车拉回去,我记得是山大医院位于平原路的太平间,从那里出发,我带路,其实我认识的路也仅仅是胜利桥以南,而且主要是五路电车线,别的路记不太清。就这样,我陪着表兄,从平原路出发,我凭着不深的印象,沿五路电车线一路向北。逝者遗体上覆盖着厚厚的棉被,严严实实的,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所以沿路看到的人无不指指点点。那时,我身体很弱,很瘦,走这样远的路也是吃不消。好不容易走到胜利桥,与表兄告别。我看着他,拉着地排车,慢慢向北走去,消失在视线里。(待续)
周晓方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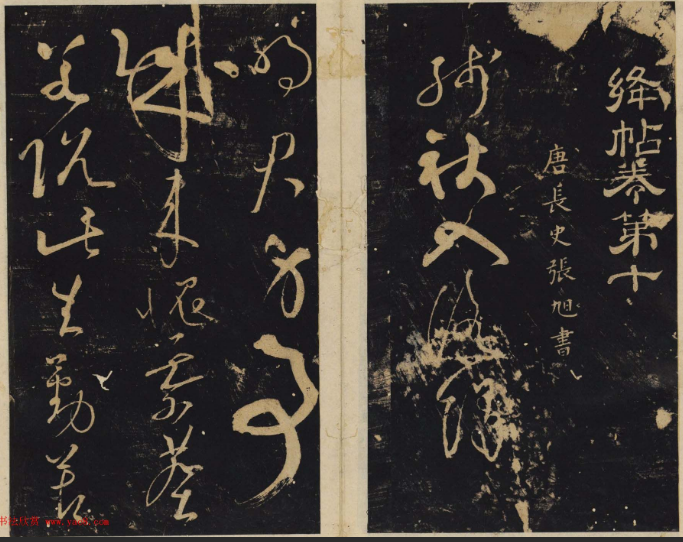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