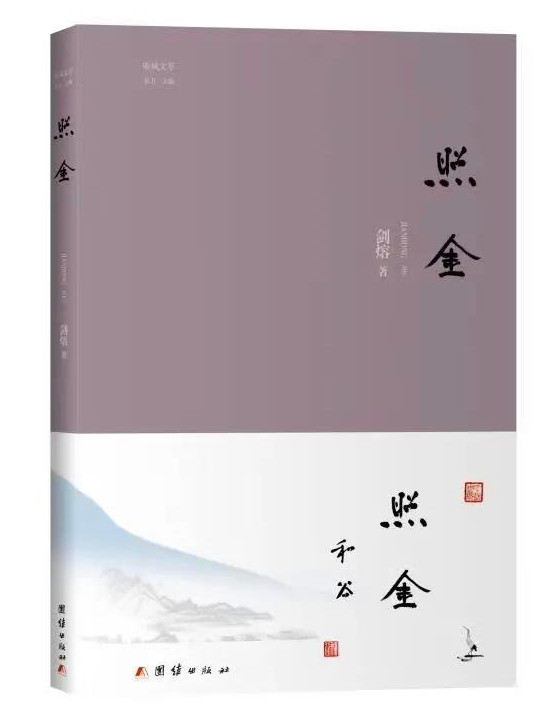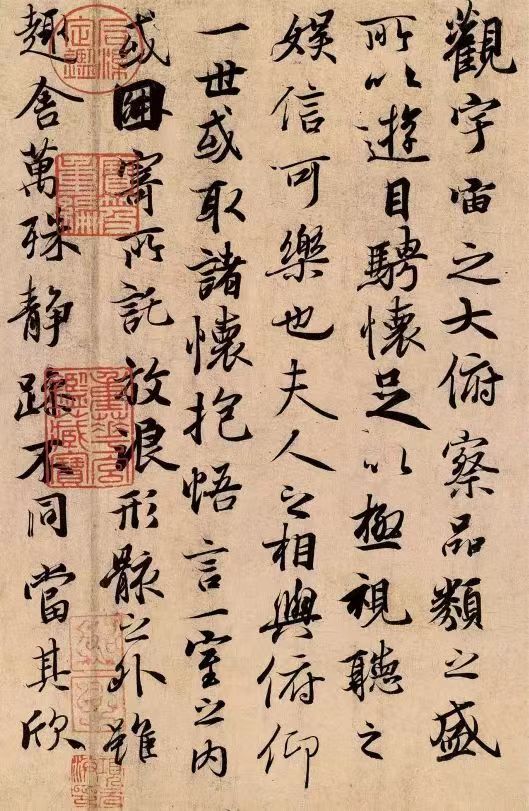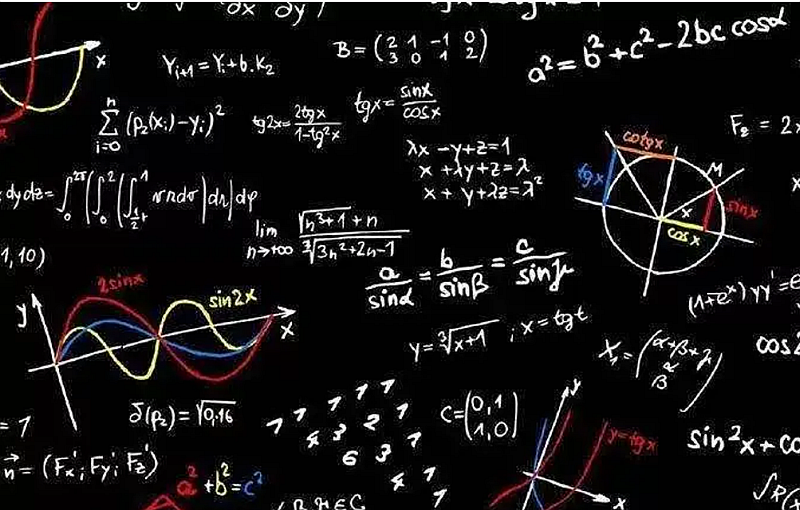读剑熔散文诗集《照金》
这本集子由《照金》《陈炉》《秦直道》《山川风光》《矿山散章》五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是片断的连缀,一种松散的组章式结构。就内容而言,《照金》《陈炉》是本地名胜,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地方;《秦直道》与铜川有地缘上的牵连,更多是在渭北高原广阔的区域伸展;《山川风光》有铜川土地上的风物,也有作者游踪所至的其他风景名胜;而《矿山散章》取材于矿山生活,是作者生活积淀的诗意描绘。这些散文诗的题材、内容紧密围绕铜川这片热土,不难看出作者投注的热情。
对写作者而言,司空见惯的本地风物,难有新鲜感带来的刺激和创作上的冲动。不过,这种情况却有利于创作者全面掌握书写对象的特征、性状,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多内容信息,为深挖深掘打下基础。从这些散文诗的书写状态来看,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显然是作者熟悉把握写作对象、更多占有写作材料的体现。《照金》《陈炉》和《秦直道》三篇,其呈现几乎是全景式的,内容足够丰富,从地形地貌、历史文化遗存、风土人情,乃至季节的变迁、饮食等,都有详尽的描述。具体的生活细节随处可见,给人真实不虚、自然素朴之感。当然,对一个地域的诗意呈现,不一定非要这种方方面面、全景式的描绘,精心的剪裁、提炼和深入表达,或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在《照金》中,作者写道:“我要为一棵树竖碑,记载它朴素的壮举”。这里,“朴素”和“壮举”产生修辞上的悖谬,诗意的效果自然也就出来了。《陈炉》中有这样的句子:“历史在燃烧。/陈炉在燃烧。/诗文在燃烧。”联想到那熊熊的炉火,我们真的会感觉到历史、陈炉、诗文都笼罩在一团火光中。再比如,对于夜晚的来临,诗人说“矿山的夜在启航”;对于从幽深巷道走出来的矿工,他用“火神”“盗火者”比拟。这些都是散文诗诗化特征的表现。当然,如能通篇进行这样的处理,艺术效果会更好。“矿灯姑娘”,对于并不熟悉煤矿工作的人来说,会有陌生感、新鲜感,这个人物形象有进一步挖掘、塑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说到散文诗,很多人会想到,一种诗和散文“混血”的产物,综合了两种文体的特征甚至优长的独立文体。事实并非如此。散文诗在本质上依然是诗,与散文的关系仅在于语言的散化和形体的自由等方面。正如散文诗的首创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的题词:总之,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辛辣。观察当下众多的散文诗作品,我们会发现,这种文体已经成为诗意的勾兑或情感过剩的产物。他们缺乏对散文诗源流的梳理,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领会,书写方式和文本表现等方面自然也难尽人意。就散文诗而言,诗意或诗性决定着文体向度,诗化与散文化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面对诗人剑熔的《照金风云》,这样一部倾情走心之作,我们难免有所期待或要求:让诗更集中、更强劲地在散文中生长。
老烟斗和他的诗
一个抽烟的人,手执木质烟斗吞云吐雾的人,想必是一个沉思者,冥想者——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如果他恰巧也是一个饮者,嗜酒的人,那就有意思了——烟雾缭绕,醉意深沉……烟和酒,过量了对身体有害,但于诗或许不无助益。
一个为自己取名“老烟斗”的人,不仅嗜烟,也嗜酒。烟和酒对他似乎并无伤害,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总是生龙活虎,令人艳羡。但这些都是因为他写诗,才让人觉得有趣或好奇,甚至有了某种意义。
老烟斗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半山腰走了下来,高不成、低不就/大胆妄为,梦见李白、杜甫/许是,伤风感冒,在发高烧?”显然,他说这话,有自况和谦逊的成分,更多则是自我调侃。从中,我们能够感知一个“老小孩”的智慧和可爱;也能想象,一个人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才得以真正地拥抱缪斯,那种心绪应该是五味杂陈的。生活的阅历,处世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说已经足够丰富、圆熟,如何将这些有益的资源导入诗歌,转化为诗歌表达中的微妙情境和深厚底蕴,老烟斗在用他的作品做直观地呈示。他的语言,言说方式,及切入主题的角度,都具有个人性,是独特的,甚至是出人预料的。我不相信他临时抱佛脚——在花甲之年,才投入诗歌的怀抱。他对诗歌的热爱和自觉的语言练习,应该更早。
于是,我们看到老烟斗诗歌中那些点亮眼睛的修辞,当然也不限于修辞。比如,《野性非洲》中的“太阳”,能“任性地剥去焦灼的鳞甲”,“踩在脚下的干谷”,竟然“血口大开,啃食羚羊和鳄鱼的骨头”。比如,他这样抒写《一生》:“两枚雨滴落下,一个小坑便成了家/搂在一起,就不孤单了”,形象化的描述让人心动。再比如,他写“钻石”,认为那“也是石头,只不过多吃了些风/多饮了些水,多耗了些时日,多走了些/弯路,多受了些折磨”。这分明也是自况,或者说是从事物的客观存在中寻得人生的寓意。此外,他还要“把灵魂托付给小的事物”,“做自己的仇人”,这种态度令人赞赏,从中也可想象他对自我生命的认知和期许。
老烟斗诗歌的取材是广泛的,他勤于观察,敏于思考,悉心收集心灵的颤动。能够在别人司空见惯,甚至感到索然无味的生活材料中,发现独特的诗意细节。当然,老烟斗目前的写作也是艰辛的,他在努力寻找词与物的有效链接,挖掘生活现象埋藏的深意,历练打磨,以便向诗歌的核心区域突进。
诗歌,不仅体现为诗人同生活及时代的融洽,一种“合谋”关系,更多时候,会表现为紧张、冲突乃至抵牾的状态。因为,诗表现现实,更表现理想。老烟斗在他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和安逸生活之际,却突然迷恋上写诗,那就有得苦让他受了。这是写作之苦,既如中国古人说的:“吟安两个字,捻断数根须”,“文章憎命达”之类,也如西方大师所言:“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在各个角落里寻觅韵的偶然/绊在字眼上,就像绊着了石头。”但事实上,寻觅不一定就能寻到,投入和产出也很可能不成比例。
不过,在揣摩或体悟某种心境,寻找恰切的词语之际,烦恼往往被兑换为喜悦。那是一种发现的乐趣,一种表达上的适意和满足。与这样的愉悦相比,写作上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目前,老烟斗写诗的状态极佳,可以认定他正迷恋这种苦与乐的辩证游戏。艺术无止境,但愿老烟斗在写诗的路途上,不断精进,收获更多惊喜。
作者简介:王可田,1972年生,陕西铜川人,陕西作协第三届签约作家。出版诗集《麦芒上的舞者》《存在者》,评论集《诗访谈》《诗观察》。曾获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