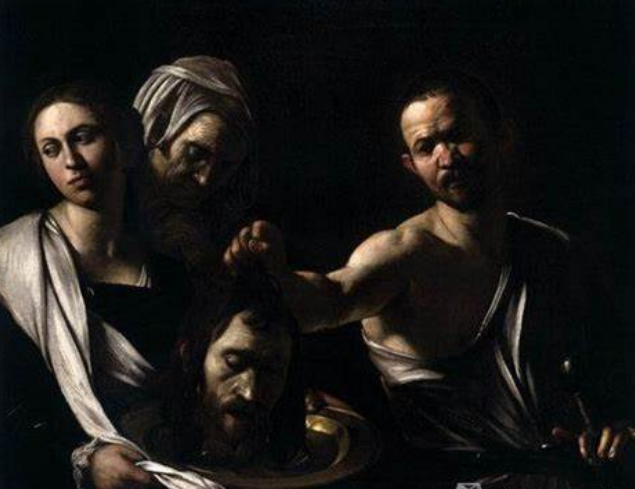经典的魅力
在155年前的10月和12月,英国出版界相继推出了三部留存世界经典文库的重要小说。那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尼丝·格雷》。三姐妹当时的年龄分别是31岁、29岁和27岁。
一百多年来,人们反复解读和研究这三朵姊妹花的作品,不懈地探究她们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感情。而这种解读与研究,将伴随人类文学史,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关于三姐妹的这三部代表作,众所周知的是:最早获得社会承认、并且评价最高的是《简爱》;而最初被忽视、后来却越来越引起评论界重视、并且争议最多的是《呼啸山庄》;直至今天,长期被忽视和遭受冷遇的是《艾格尼丝·格雷》。
相比较而言,小妹安妮的《艾》,从各个角度和层面上看,都比两位姐姐要显得单薄和稚嫩一些,却也不乏独特和动人之处。
在国内,人们对三姐妹的认识是从《简》开始的,至今,中译本已有许多种,翻译和引进的研究与传记类作品也很多。正如华东师大教授黄源深先生1993年在为译林出版社重新翻译《简爱》时所说,“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极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次开掘……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①黄源深译本从1994年6月初版到2000年5月,中间已经再版10次之多,而在读者之间还有别的译本在广泛流传。
而我们对《呼》和《艾》的认识与了解相对要晚得多。
关于《呼啸山庄》,普遍见到最早的中译本,应该是1980年出版的朱炯强译本,显然比《简爱》要晚很多,但是,在国内和在国外一样,人们对这部奇特的著作一经认识,便很快着迷起来。短短20年间,已有多种译本,而且不断再版,比如,近年流传最广的1988年上海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方平译本,到1997年就已经再版7次之多,之外,还有杨苡译本、梁根顺译本等多种版本。翻开20年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呼啸山庄》的研究文章不仅与日俱增,而且莫衷一是,几乎每一个阅读者和评论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不同理解,同时提出不同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三姐妹研究的不断突破,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几乎高过了一直占据三姐妹作品最高位置的《简爱》。
至于《艾格尼丝·格雷》,直到2000年12月才有了裘因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加之国外对安妮的研究性文献也远不如两位姐姐那么多,国内更少有介绍和引进,所以难怪我们了解不多了。
关于这三部作品,可以有无数的比较与评说,但在这篇有限的文字中,我只想通过对各自不同叙述方式的比较,粗浅地谈一点自己的阅读体验和认识,尤其是在《呼啸山庄》中,作为叙述主体的两个边缘性人物,想简约地探讨一下他们在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
“我”,从中心到边缘,意欲何为?
从叙述角度上讲,这三部作品都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也就是说,叙述主体始终是“我”。
在《简》和《艾》中,“我”就是作品主人公,笔触可以直达人物内心最深入最隐秘最细敏的部位,尽管故事情节多有虚构,但人物的许多内心体验、感受和观点、立场则直接出自作者本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人为痕迹,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感觉到作者借助人物、甚至越过人物直接站出来说话,很武断地要将个人观点强加给读者。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就好像我们正在很投入地看一出舞台剧,演员唱着唱着就要停下来,换一副超然剧情之外的表情,跟台下的观众解释些什么、提示些什么,比如:“趁他看画的时候,读者,我要告诉你,那是些什么画。”(黄源深译《简爱》P140)、“你没有完全忘记小阿黛勒吧,是不是呀,读者?我并没有忘记。”(同上P521)……“一切真实的故事都包含着有益的教诲……我不惜抛开顾虑,把不肯告诉最亲密朋友的内心隐秘真诚地披露给我的读者。”(裘因译《艾格尼丝·格雷》P1),等等。在这两部小说中,充满了这种在我们阅读的眼睛中提示我们到场的句子。
然而,《呼啸山庄》跟前两部完全不同,尽管也是第一人称,却最大限度地打破和超越了第一人称的局限和制约:从结构上讲,是一种层层逼进的包容性结构,而不是像前两部那样惯常的线性结构;从视角上讲,几乎达到了全视角的客观与冷静,作者意志隐藏得深之又深,尽可能地避免了主观叙述带来的种种偏狭和对人物的误解……
在《呼啸山庄》中,大家公认的男女主人公是希刺克历夫和凯瑟琳。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方平就认为真正的主人公是哈利顿。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很大程度上跟这部作品独特的叙述方式有一定关系。
在这里,叙述主体“我”,不是故事中心人物中的任何一位,而是跟故事本身毫无关系、完全置身于矛盾漩涡之外的两个“无关”的冷眼旁观者——房客洛克乌德和女佣丁耐莉。
第一个“我”——洛克乌德,是一位有厌世情绪的知识青年、租住在画眉田庄的房客。对于喧嚣繁杂的尘世而言,他是一个遁世者和逃离者;对于作品所展示的故事发生地而言,他是一个闯入者,一个不速之客。他从海边度假中一场没有结果甚至没有展开的爱情中逃了出来,来到英国北部约克郡一个叫“呼啸山庄”的庄园,这里与世隔绝一般的静谧荒凉和美丽绝尘的乡间景色,使他错以为找到一个远离尘世纷争的世外桃源,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一个厌世者的理想天堂”。
然而,在这里,他却遭遇了另一场更为酷烈的“争斗”——人性善恶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只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一个倾听者和记录者,也就是说,只是一双耳朵、一双眼睛和一支笔,故事本身跟他不仅毫无关系,而且隔着一个真正的讲述者——耐莉。
第二个“我”——丁耐莉,是从小随母亲进了呼啸山庄的女仆。用方平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14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谁是〈呼啸山庄〉的主人公?》②中的话说:“小说中出现的第二个叙述者‘我’(耐莉)是故事的边缘人物,她是呼啸山庄那一个小天地里三十年爱憎恩仇、人事沧桑的目击者,在很多场合又是大小事情的参与者,而且还时常对眼前的事态议论一番,给她的叙述添上了一重感情色彩;但故事发展的进程并不因为她的喜欢或是不喜欢而受到影响。……可是,有关她个人的私事(什么时候嫁的人?有没有孩子等等),书中一句都没有交待。她没有个人的历史,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只是小说中的半个人物,为了便于故事情节的运转而存在。”
不错,在《呼》中,一个讲述者、一个转述者,两个“我”都是远离中心的边缘人物,如果说耐莉只是“半个人物”,那么,洛克乌德甚至连半个人物都算不上。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人物的存在,似乎真的仅仅只是结构需要,是那种被我们称为“结构性人物”的角色。在缩写本或别的体裁(比如影视剧)的改编中,这样的角色完全可以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记。
然而,在对原作的阅读和理解中则完全不同。我以为他们不仅仅是为“结构”和“情节运转”而存在的。他们有更加重要和隐秘的使命。否则,如果仅仅为了讲故事,艾米莉大可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费这么大的周折,给一个原本已经够复杂的故事增加这样两个“不是人物的人物”。
那么这两个人物对于整部作品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叙述主体边缘化的深层含义是什么?或者,就作者创作意图而言,有没有那样一个被隐藏的秘密使命和意图?
为什么选中洛克乌德,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当然,方平先生的认为也许是对的。但是,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爱和恨,都是生命在燃烧》③中引“牛津版”杰克教授的序言所说“《呼啸山庄》是最让人猜不透的英国小说之一”、是“我们现代文学中的斯芬克斯”,这部小说令人着迷之处,正在于对它几乎从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去阅读和理解,都可以有无数想象、无数注解,就像一只百拼不厌的魔方。就连这样两个远离作品中心的最边缘和最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工具性人物”,也有无尽可探究的内涵与意义。当然,这里或许有“猜”的成分。
先说洛克乌德。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研究勃朗特姐妹的各类专著已经有很多种,问题与结论也五花八门,但无论是考证还是阐释,研究中难度最大和歧义最多、同时让研究者最感兴趣也最具挑战性的人物是艾米莉。“1929年,K·A·R·萨格登在《勃朗特一家生活简史》中,曾列举了勃氏传记文学中的五大悬案”,有两大悬案涉及艾米莉,其中第五条就是“艾米莉的性格之谜”,而且作者断言,“这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④
在短短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艾米莉留给后世的印象是一个神秘、阴郁、寡言、孤傲的避世者形象,在临终前,她销毁了自己除这部小说和部分诗作之外的所有私人文字,包括书信、日记等。就像《呼啸山庄》中的故事主人公们一样,将自己惊涛骇浪、跌宕起伏、丰富无限、深远辽阔的内心世界,紧紧地封存在不断被人误解的外表和行为后面,任人评说,决计不对自己做一句注释与倾诉。
因此,对艾米莉的了解,不在于她告诉大家一个怎样的自己,而在于你在她的作品中探索、认识和发现到一个怎样的艾米莉。正如“E·F·本森在《夏洛蒂·勃朗特》中说,夏洛蒂写作是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艾米莉从不写外部经验,她的灵感纯系发自内心。”⑤尽管人们对《呼啸山庄》的写作,考证了种种素材来源和现实参照,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这是一部心灵之作,而且用了一种及其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犹如一次真正的历险一般,这里对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一场超限探索。
那么,对于“呼啸山庄”、对于整部作品来说,洛克乌德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他所随身携带的,除了眼睛、耳朵和一支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倾听和勇于探究的心灵。
在许多文章中,人们习惯称他为一个“好打听奇闻轶事的游客”。但首先,他跟“呼啸山庄”的相遇,缘于他对尘世的逃离,在他到来之前,山庄一直存在着,故事也在发生着,对于滚滚红尘的外部世界而言,那里所有的一切,不为人知,也几乎没有人关心和过问,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每一条狗,都对陌生的外部世界保持着最敏感的警觉和戒备,那种戒备几乎达到不通情理和难以理解的地步,就像一个人用一个坚硬孤寂却敏感异常的壳包裹着的内心世界一样,一个真正无关和无缘的人,怎么可能进入这个世界?
然而,洛克乌德进入了,他的偶然发现和不懈探寻为我们开启了一道进入之门,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深处,张着一双惊讶的眼睛,审慎地屏息看着不断展开在眼前的一场对抗与战争。
几十年来,呼啸山庄怎能没有过客?但所有的过客都只是过客,就像芸芸众生之间,到处都有陌路擦肩,只有在心灵上能够互相感应的人,才能走进彼此的精神世界。所以,洛克乌德是个例外,他既是这部作品结构中最外面的一件衣裳,也是引领我们进入作品之中的一枚探照灯。
隐藏在耐莉公开任务背后的秘密使命
再说耐莉——这个被方平先生称之为“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半个人物”。
我们跟着洛克乌德来到“呼啸山庄”的面前,首先揭开的是美丽和谐的乡间田园一般的外衣,很快便发现了被隐藏在下面的紧张而不和谐的痕迹,在隐隐感觉到一种深埋其中的“骚动”、不安和神秘的、随时有可能爆发的风暴时,还没有打算深究那些被感觉到的究竟是什么,就立刻被当成一个“闯入者”和“探秘者”,而接到了最不友好的警告:“‘你最好别理这只狗,’希刺客利夫先生以同样的音调咆着,”……而“这对狗同那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提防着,监视着。”⑥
狗且如此,何况人呢。在如此壁垒森严的提防中,我们跟着洛克乌德,被一些在呼啸山庄是一种习以为常、而在我们却是一种从未经见的神秘和怪异的发现搞得神经紧张,不断想知道真实的答案,却又在处处碰壁和一片茫然中迷失而不得要领,以至于将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直至第四章时,终于找到丁耐莉,事情才发生转机。
耐莉,是这里唯一态度温和而热情的、不加提防与戒备的、愿意接受访客和回答提问并积极讲述的人。相对于被讲述中的每一个人的被动和封闭状态,耐莉是唯一主动和开放的,是我们通往那个神秘世界的一条途径,不管是不是最好,但在这里是唯一。
那么,她果真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吗?她果真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吗?她果真只是为了“情节运转而存在”的吗?她仅仅只是一个“目击者”和“讲述者”吗?……如果是,那她的讲述应该始终不带过于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意志,但事实不是这样。比如:在第三十二章的最后,当耐莉说着“我所有的愿望中最高的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合。在他们结婚那天,我将不羡慕任何人了;在英国将没有一个比我更快乐的女人了。”时,她凭什么?当她在第三十三章中说着“你知道,他们俩多少有几分都像是我的孩子”时,又凭什么?当她在最后一章,摇摇头,说着“我相信死者是太平了,可没有权利来轻贱他们。”,而制止洛克乌德对死者的调侃时,更凭什么?要知道,她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女佣,身份和地位比这里面除约瑟夫和齐拉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都低下,在整个故事里面,“最高的愿望”和“最终的快乐”怎么会在她哪里呢?跟她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物的出现是多余和真正苍白无物的,尽管人们不断指证这个是情节性人物、那个是结构性人物,但是读者和读者的感觉不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莎剧一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物、包括道具的出现,都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和安排的,整个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以及“精神探险”的完成,无一不在作者冷静又饱含激情与悲悯情怀的关照之中,那个深深隐藏幕后的作者,就像艾米莉在现实中一样缄默无言,从没有对作品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行为横加干涉与评说,也从不曾站到我们面前来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一样微小的注释也没有,然而,作者的意志却贯穿始终,故事在经过了那样一场惊涛骇浪的搏击与对抗之后,朝向耐莉的“最高愿望”发展着,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愿望?
在对《呼啸山庄》的评价中,人们引述最多的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giniaWoolf,1882—1941)在1916年发表的《〈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一段话:“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⑦
“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从哪里感觉?怎样拼凑与整合?如果我们在阅读中只注意了故事情节,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邪恶的复仇故事和一个疯狂的爱情故事,就像英国评论界最初面对这部小说时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据不予以承认一样,人们几乎在主人公希刺克利夫和凯瑟琳身上只看到疯狂与邪恶,而看不到希望与理想,正如金琼在《绝对时空中的永恒沉思》中引述乔治·桑普森在《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中所言:“《呼啸山庄》中的邪恶‘令人吃惊’,因为‘它是纯粹的邪恶,绝对没有任何肉欲的痕迹。激情是无拘无束的,但它不是肉体的。’”⑧对此,当时的人们和社会道德难以理解和接受,人们甚至一直不解和怀疑从没有恋爱经历、极少跟人接触的艾米莉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艾米莉研究中,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艾米莉是一个具有通灵术的神秘主义者。
但是,弗吉尼亚对艾米莉的了解与理解是深透的。在作品中,耐莉几乎不动声色地充当了作者意志的代言人,她冷静地目睹了这场人性善恶与精神世界酷烈、盲目、绝望的搏击与挣扎,并且以自己低微却特殊的身份、冷静却悲悯的心肠、不被重视却坚定自信的意志尽可能地介入了“情节”的发展中。
她对第一代之间互相吸引、互相排斥、互相厮杀的任何一方其实都给予了最彻底的揭露,因此,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为攻击方口实的缺陷,所以许多评论者曾指责这部小说的一个理由是“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她在许多关键时刻,探到了人性深处最阴暗邪恶的角落,却决意不替他们掩盖和隐藏。比如,在凯瑟琳决定跟林顿结婚又无法割舍希刺克利夫时,她将自己再也无法压制的最真实最隐秘的内心矛盾倾诉给耐莉听,当时,耐莉知道希刺克利夫就在那间屋子里面,但她没有阻止、提醒、甚至暗示凯瑟琳,而让她将自己在完全不知道希刺克利夫在场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真实态度暴露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希刺克利夫的失踪三年?在以后的许多次类似的关键性情节里,她都充当了一个这样“铁石心肠”的揭示和暴露真实的角色,不管后果多么严重; 但同时她又对每一个人物都寄予了最大的同情,包括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十足“恶棍”的希刺克利夫,她其实一直在尝试和努力想要帮助他和引导他走出迷途。比如,在少年希刺克利夫严肃地回答耐莉的提问时说:“我在打算怎样报复辛德雷。我不在乎要等多久,只要最后能报仇就行,希望他不要在我报复之前就死掉。”这时,她说:“羞啊,惩罚恶人是上帝的事,我们应该学着饶恕。”但是,她眼看着希刺克利夫在仇恨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疯狂和孤寂,直至自己打败和毁灭了自己,才回到了自己的灵魂和爱那里,她没能看到仇恨从活着的希刺克利夫心中被驱逐出去,但是,这种愿望在哈里顿的心灵中得以实现。
而哈里顿和小凯瑟琳,他们从父母辈心灵的痛苦挣扎和精神的分裂撕扯中诞生出来,却几乎是在耐莉的一手关怀和爱抚中成长起来,他们的血液与生命中,一半承袭着父母辈天性中一切纯朴美好的部分,一半寄托着耐莉的“最大愿望”。他们最终让耐莉的愿望得以实现,将一场战争升华到一个静穆、和谐、高尚的境界。而小林顿,被赋予的是另一种命运,他几乎承袭了父母辈天性中所有邪恶和坏的部分:舅舅林顿的孱弱无力、凯瑟琳舅妈的自私自我、父亲希刺克利夫的冷酷狭隘、母亲伊莎贝拉的盲目浅薄……他的死,跟上一辈中任何一位的死都不同,差不多是一种抛弃,耐莉对他也没有表示任何同情。
如此,还能说耐莉对于情节的推进是没有“影响”的吗?还能说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结构性人物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正是耐莉暴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传达了作者的主观意志。因此她的叙述,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人为色彩。
耐莉是第一主人公
就像我们在许多时候、许多作品中发现的那样,形式跟内容,难解难分。大多时候,我们谈论一部作品的结构、修辞或者叙述方式时,无疑是在探讨表现形式的问题,然而,对于一些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作品,比如《呼啸山庄》,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
如果我们从叙述角度并且以解构的目光来看《呼啸山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丁耐莉是整部作品的第一主人公,而其他人物多少都带有施指符号性质和象征意味。就好像对于一盘棋来说,厮杀的是棋子,但棋子是被动的,只有棋手和看不见的棋手意志是主动的。
那么,在《呼啸山庄》这盘棋里,丁耐莉是唯一看得见的棋手。我们可以不知道她的私人历史以及她个人的爱情、生活故事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但凡她在场,她的主观意志以及她对事态发展的影响,就会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前面我们说过,《呼啸山庄》是一部充满诗意和象征的心灵之作。从社会的角度上讲,当时的英国,正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变革时期,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中,“呼啸山庄”象征和代表的是原始的农业文明,“画眉田庄”代表的是现代的工业文明。
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希刺克利夫代表的是原始而质朴的生命本原,所谓“本我”,几乎无根无底,只是老恩萧先生偶然捡回来、并且已经具有生命意识的一个黑小孩,作品从头到尾没有交待他的出身,没有人能回答关于他的最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但是,这个孩子却始终有着强健的体魄、旺盛以至野性和无法驾驭的生命力、强烈的爱恨情感和具有毁灭性的内在激情,因为始终遭受的歧视、践踏和不公正待遇,而深深埋下仇恨的种子,他一生受尽折磨以至疯狂而无法战胜、无法超越的只是内心的仇恨与复仇愿望。
与希刺克利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顿,作为田庄少主,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和驯化,具有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无可挑剔的修养,成年后,自然而且义不容辞地担任着社会职务,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敬……等等,他所代表的是社会教化的产物——“文明人”,所谓“超我”,但是,另一面,他却像始终被养在温室中的植物一样,孱弱和毫无生机,无可挑剔,却毫无激情与活力,但是,临到终了,他身上因为修为和教化所深深化在生命中几乎成为一种本能的温文宽厚、自我克制、忍受痛苦与折磨、宽恕别人的品性,闪耀着人性中柔和而持久的光芒,让他获得了人们(包括丁耐莉)最终的永远的尊敬。
在这两个人中间,被共同爱着、争夺着、珍惜着却无可避免地置之于死地的是凯瑟琳。凯瑟琳是一个极端的矛盾体,自从认识林顿(人性中的更高境界)后,无时无刻不在一种痛苦的挣扎和抉择中,所谓“自我”。一方面从情感上、从潜意识里、从生命深处、从本能上,她都更接近于希刺克利夫,然而,从理智上,却向往着林顿,希望通过她能将自己不同程度深爱着的两个男人“结合”在一起,能化解双方的“矛盾”,包括她的婚姻,都有一定的象征性,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她代表着人对自身本能超越的一种向往,从社会的角度上讲,她代表着“山庄”对“田庄”、也就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好奇和向往,希望通过“联姻”来达到和实施超越与结合的目的。但是,这种愿望在她身上显然难以实现,那种固有的偏见和难以化解的矛盾,并非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和平地消除和解决,必须有所牺牲,那么,凯瑟琳的心灵、情感以及像花蕾一样美丽的19岁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个残酷而悲壮凄美的“战场”,只有从她的死亡中诞生的新生命——小凯蒂,才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像初升的朝阳一样,是人性的完美与和谐。
那么,在第一代的故事纠葛中,最中心最关键的三个人物,其实就是“人”的三位一体,也就是人性中的三个层面。
到了第二代,作为第一代生命的延续,哈利顿和小凯蒂的结合,代表了所有痛苦挣扎的结果——凤凰涅磐一般的新生,代价是从生命中剥离和摒弃了小林顿。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痛苦演变过程中,除了自身的痛苦挣扎与争斗之外,唯一关注始终、参与始终的“外力”就是丁耐莉。对于第一代,她的参与带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更多的是一种关注、了解、同情和近似于冷酷的揭露与批判。对于第二代,她的参与是主动的:作为哈利顿的生身父母,辛德雷夫妇因为一个的早逝和另一个的堕落,几乎未尽一天养育之责;作为哈利顿的教父,希刺克利夫始终拿他作为复仇的工具,一心要将社会对他的所有不公回报在哈利顿身上,然而,就在希刺克利夫以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几乎将哈利顿完全塑造成自己的一个翻版、甚至在蒙昧与卑贱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却因为有过堪称养母与教母的耐莉的早期启蒙,哈利顿唯一没有继承希刺克利夫的是“仇恨”,以及连带的偏见,而且并不排斥异己的东西,对于“文明”有一种纯朴的向往,更宝贵的是有一颗宽厚的仁爱之心。哈利顿宣告了希刺克利夫的失败,对希刺克利夫毕其一生的复仇计划,是一个彻底的讽刺,却正好实现了耐莉从一开始就对希刺克利夫提出的警告与愿望:“羞啊,惩罚恶人是上帝的事,我们应该学着饶恕。”
那么,小凯蒂也一样,凯瑟琳给了她生命,却在她一诞生就离她而去,是耐莉将她一手带大。因此,唯有耐莉有资格说这两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讲是她的孩子,也只有她有资格说,这两个孩子的结合是她最大的愿望与欣慰。
如果说《呼啸山庄》是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的“拼凑”与“整合”,那么,丁耐莉这个“读过许多书”、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和一颗宽厚的悲悯心肠却身份低微的仆人,就是那只实施之手。
注释:
① 1994年6月译林版《简爱》“译后记”。
②《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一期方平《谁是〈呼啸山庄〉的主人公?》(P3)
③《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二期(P3)
④《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一期杨静远《关于勃朗特姐妹的传记文学》
胡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