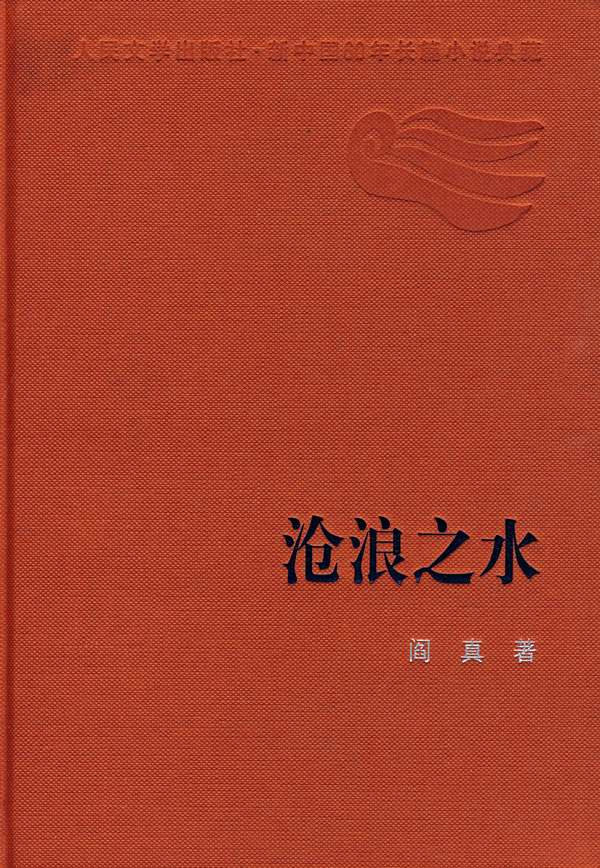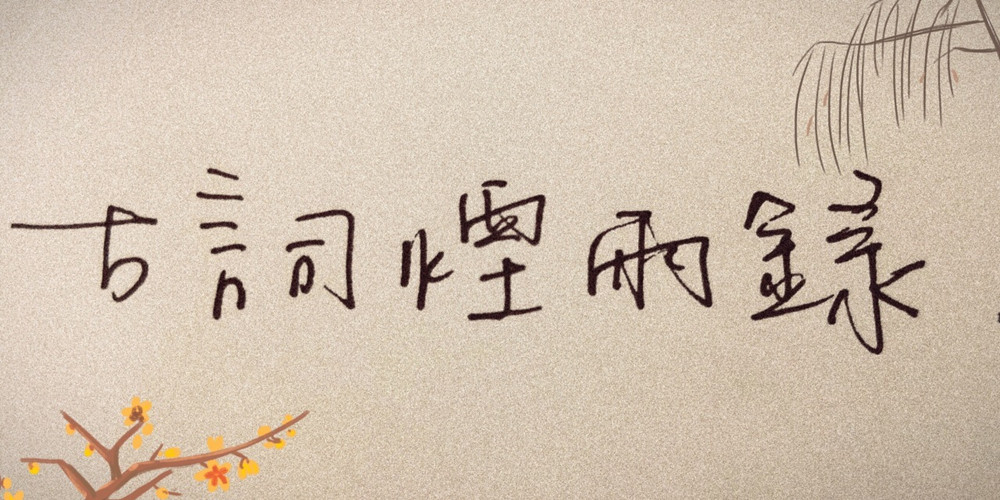51.事迫離幽墅,貧牽犯畏途。
二句謂為事所迫、為貧所累,離開所隱幽居,走上兇險仕途。
第48韻以下至此聯,多飢貧之音愁蹙之情。由“事迫”推斷是發生家庭變故,經濟拮据,讀書難以為繼,故被迫踏上仕途。這又恰對應于前引《上裴相公啓》“橫經稷下”所接言“俄屬羈孤牽軫”等困境。至于是何家庭變故,有待深考。
52.爱憎防杜摯,悲嘆似楊朱。
杜摯,是溫《上裴相公啟》在緊接上文“安事晨炊”之後,敘述“既而羈齒侯門,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而提到的迫害自己的人物。《上裴啟》本身表明,“杜摯相傾,臧倉見嫉”之事明顯發生在“羈齒侯門”之後的“旅遊淮上”之時。而此處所言“愛憎防杜摯”則是在家庭變故後、被迫踏上兇險仕途之初。“杜摯相傾,臧倉見嫉”為互文,故杜、臧屬同類的傾陷加害溫庭筠的人物。據《孟子‧梁惠王》載,“嬖人有臧倉者沮”孟子。而所謂“嬖人”者,據《左傳‧隱三年》:“公子州吁, 嬖人之子也”之釋文:“嬖,親幸也。賤而得幸曰嬖”;考慮晚唐形勢,當曲指宮中嬖幸,即得皇帝寵信而專權的宦官。 由此推理,所謂“杜摯”者,應亦是宦官。參前第28韻“揚觶”之解,“杜摯”當作“杜蕢”。“楊朱”句,典出《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二句謂踏上仕途之始,自己就受到宦官的迫害,而仿徨岐路,不知所之(可見溫與宦官的仇恨起自上一代,而溫的出仕甚晚而長期隱居,有避地避仇之意)。
顧嗣立《詩集》援引《三國志‧魏志‧劉劭傳》附“郎中令河東杜摯”事而謂之曰“事未詳。”其人不相干,固不得其詳也。劉學鍇《全集》則引(《史記·秦本紀》(亦見《商君本紀)之反對商鞅變法的杜摯,亦與溫詩文之上下文無關。為了識別這個杜摯,我們不得不考慮兩個可能:一是歷史上尚另有關於“杜摯”的記載,今亦不得見也;二是別有一人,其名在多少世紀的版刻印刷中發生訛誤,被寫成今日的形態,今本“杜摯”或應是稍不同的另一個名字。 由本詩第二十八韻“揚觶辱彎弧” 之注可証“杜摯”應作“杜蕢”,“蕢”字因版本朽爛、 字跡模糊而被誤認作“摯”,“杜蕢”本是膳宰(亦宦官之一種)之名,而即指宦官。溫受宦官迫害的證明,見前第二韻“頑童逃廣柳”句注引《上裴舍人啟》。受迫害而猶努力進取,在江淮受辱、從遊莊恪、改名“岐”以應試,等第而罷舉的系列事件中有豐富生動的表現。所以本詩第52韻“爱憎防杜摯“及《上裴相公啟》“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中的“杜摯”均應作“杜蕢”。
53.旅食常過衛,羈遊欲渡瀘。
過衛(衛地在今河南淇、滑縣),語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過曹”;言奔波道路,而屢經衛地。羈遊,長期客遊他鄉。渡瀘,語借諸葛亮《前出師表》“五月渡瀘”,瀘即今金沙江;“欲渡瀘”,謂遊蜀深入腹地,幾乎渡瀘而西。
54.塞歌傷督護,邊角思單于。
“督護”,即《丁督護歌》,晉宋間曲,“其聲哀切”,詳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二‧吳聲歌曲》宋武帝《丁督護歌五首》解題;多寫戎馬艱辛和戰爭造成的思婦哀怨。單于,唐角曲;《樂府詩集· 横吹曲辭四‧梅花落》解題云:“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角曲,軍中之樂也。杜佑《通典··樂典》載“蚩尤師魑魅與黄帝戰,帝始命吹角,作龍鳴以御之。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二句謂出入邊塞,聞塞上督護之歌而傷懷,聽邊庭大角之曲而興感;概括自己的軍營感受。
第48至52韻,既而自傷老大,又由地位的下降而為生事逼迫,不得不棄隱求仕。但仕途伊始,就要謹防宦官迫害。 第53至54韻,寫羈旅四方(包括出塞入蜀)到處依人的經歷。這一段經歷與溫《上裴相公啟》所謂“羈齒侯門”漫游四方的敘述相應;只是詳略不同而已。
55.堡戍摽槍槊,關河鎖舳艫。
堡戍,駐軍營壘;摽:通標;誇示、高舉。關河,函谷關與黃河,或泛指一般關口與河道。二句寫戍樓槍槊林立,關河舳艫禁鎖;分明是緊張的非常形勢。
56.威容尊大樹,刑法避秋荼。
“威容“句,典出《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秋荼”,語本漢桓寬《鹽鐵論》卷十《刑德》“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後遂習以秋荼代指繁刑密法。二句自謂本欲尊大樹將軍之威容(而謀求職位),(不期變生突然),自己只得逃避繁如秋荼的刑法(而遠赴京師)。 此“大樹”不言自明,必已倒下,詩人諱直言之耳。 按此處溫所尊之“大樹”當指王涯,詳見拙作《溫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一輯)。
第55至56韻,當時(甘露之變)特殊形勢下,溫所依“大樹(將軍)”既倒,禍及自身,他只能選擇逃之夭夭。 這兩聯實際上隱括了甘露變後他在揚州受宦官侮辱,而回長安的原因。這段經歷與《上裴相公啓》“羈齒侯門”後面緊跟的“旅遊淮上”(即江淮受辱)等語相應。溫“旅遊淮上”之事件在唐宋間筆記小說中乃至正史中都有片段或者歪曲的反映, 溫本人詩文中也有隱晦的點睛式的透露。把這兩方面的文字表述剪輯整合在一起,方可得其全貌。
“旅遊淮上”以下,《上裴啓》原文是:“投書自達,懷刺求知。 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 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 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射( 應作涉,讀若喋)血有冤,叫天無路。 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嗟,靡能昭雪”。尤其“通人見愍”數句, 正說明迫害温庭筠者舍宦官無他人。
如上,本詩與《上裴相公啓》的敘事梗概完全一致。“自頃爰田錫寵,鏤鼎傳芳”對應5—8韻;“占數遼西”對應30—46韻;“橫經稷下; 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思欲紐儒門之絕帷,恢常典之休烈。俄屬羈孤牽軫,藜藿難虞。處默無衾,徒然夜歎。 修齡絕米,安事晨炊”對應第47—52韻;“既而羈齒侯門”對應第53—54韻;“旅遊淮上”云云對應第55—56韻。其自敘生平甚為清楚:都是說自從祖宗建功立業,後因“直道”而衰微,自己則不得不避地隱居,曾讀書太學;但因家庭變故,難以維持生計;乃“羈齒侯門”、其後則“旅遊淮上”。雖詳略互異,甚至有互補之處,寫的都是溫到江淮受辱為止的全部經歷。 那麼,溫在江淮受辱之後,有什麽遭際呢?下文57至74 韵可以看出溫回到長安經過很多周折乃有從遊莊恪太子的特別機遇。
57.遠目窮千里,歸心寄九衢。
九衢,義同九逵、九陌,指長安。二句可解作“窮千里之遠目,寄九衢之歸心”,有戀闕思君之意。
此時回京師,其事即《舊傳》所謂“受辱”之後“庭筠自至長安”;其時不是《舊傳》所云咸通中,而是在大和開成之際。溫在揚州有《上吏部韓郎中啓》,求“分鐵官之瑣吏,厠鹽醬之常僚”以求解決買妓為妻費用,結果受到宦官勢力毫不留情的人身攻擊和造謠誣蔑,是之謂“江淮受辱”。我們本來粗定江淮事件發生時間,也就是上本啓的時間在大和開成之交。啓中語“弦弧未審,可異前朝”,自謂連“弦弧”(指弓箭)都不能審視一下,比喻連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都沒有;這和“前朝”之“劉蕡下第”事件難道不同嗎?今得此一言而確定該啓上于開成元年;經歷受辱最後赴長安,當在開成元年下半年或更晚。
58.寢甘誠繫滯,漿饋貴睢盱。
寢甘,睡眠酣足也。《莊子‧徐無鬼》“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繫滯,牽繫而滯留,謂宦途久不通達。漿饋,語出《莊子‧列御寇》“列御寇…遇伯昏瞀人。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謂曾要就食的十家賣漿店中,五家把漿先送來,喻被各家款待。 睢盱,張目仰視貌。二句可解作:若圖“寢甘”誠當“繫滯”,欲得“漿饋”,貴在“睢盱”;謂圖舒適而不勉力,當然仕途久無所就,要想在京城有所得,貴在會瞪大眼睛,窺伺求索。
59.懷刺名先遠,干時道自孤。
懷刺,身上帶着名片;語出《後漢書》本傳禰衡“陰懷一剌,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名先遠,謂自己的狼籍名聲早已使人避之唯恐不遠。干時,干求當時當道者而求有所用;溫“干時”之“道”,當與削滅宦官有關,其事至難,而同道者寡,故謂之“孤”。按“甘露之變”以後,“中官用事,衣冠道喪”(《舊唐書》卷一百七十《裴度傳》),當時的士人對本難以解決的宦官專權問題已無計可施。
60.齒牙頻激發,簦笈尚崎嶇。
齒牙,猶言口舌;《南史》卷十九《謝眺傳》“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激發,激而發之;謂有人貶抑而更有人推舉自己。簦笈,簦為有長柄的笠而笈即書箱,簦笈謂未仕文人全副裝備,而代指其人或其宦途。 二句謂經有關人物多次或貶或褒,或抑或揚,自己仕途仍然不順。意思與《上裴舍人啟》所謂“王尊一身,困于賢佞”(“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見《漢書·王尊傳》,即“三期賢佞”)相似。
61.蓮府侯門貴,霜臺帝命俞。
蓮府,亦作蓮池、蓮幕,美稱幕府,此謂宰相府。《南史》卷二十二《王儉傳》“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所謂“蓮府侯門貴”,指李程、裴度等看重并推薦自己。霜臺,本御史臺之別稱;此處實指“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第60韻說自己被人貶褒抑揚,尚無進身之階, 已經伏下了受推薦而飛昇的可能。 故本聯之得貴人重視皇帝俞可自然承上說自己。二句謂蓮府侯門貴我,因而帝命俞我效命所謂“霜臺”,即經宰相李程等的推薦,皇帝俞可,而任職于“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見下),成為太子李永的侍從文人。詳見《溫庭筠從遊莊恪太子重考》( 待刊), 今僅列其主要論證如下:
劉學鍇《全集》謂本句以下說的是題中諸位御史的活動, 完全脫離了詩本身的連續性。事實上, 本詩一百韻,無一句不關溫自己者,無一句非親受親歷親見親聞者。即使僅從局部看, 第57至第60韻也是每一句都說自己, 豈能毫無過接就一下子轉到別人身上?如果全是說別人,以下至第74韻以侍御史爲主的朝見儀式更不是未列朝班的溫庭筠所能想象的;若自己未經其事,卻又以想象之筆寫給經歷其事的諸位侍御史看,也完全不合理。那樣讀下去,詩人的詩思、敘事的邏輯,也完全失去着落, 不知所云了。
溫《詩集》卷六《洞戶二十二韻》專寫溫從遊莊恪太子事。 其事始自開成二年夏秋間而終于開成三年十月莊恪死之前,前後僅一年略多時間。該詩第四韻就交代了自己初見莊恪太子的特定時間和地點:“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砧”--當初秋霜清玉女搗砧之時,在宮省粉署諸曹仙郎之地。經過以比爲賦的諸多描述而又值蕭瑟搖落之時,至第二十韻“綠囊逢趙后,青瑣見王沈”,謂狠毒的寵妃和猖獗宮掖的宦官合謀害死了年幼的太子,實指楊賢妃與宦官仇士良等合謀害死了莊恪太子李永之事。《新唐書》卷一二五《文宗二子傳》王起《莊恪太子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所以說,飛卿開始從遊莊恪太子的時間(應比初見太子早)應略早于開成二年秋。
我們從這個判斷繼續推理(並且也考慮溫在開成元年“江淮受辱”的經歷),所謂“襄州李尚書”應符合開成元年二年間任職尚書、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的條件。符合這個條件者非李程莫屬。由《新傳》知李程“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可見,李是從右僕射兼判吏部尚書之職務,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的,稱之爲襄州李尚書,固有由。蓋為尚書時,當已經推薦溫,以待委命,而鎮襄之後,溫乃至長安赴任,然後謝官也。其時間當在李程開成二年三月在長安受命赴襄州,並且到任安頓之後。考慮李程調動官職準備旅行而由長安遷至襄陽所需時間,以及溫庭筠就任新官所需手續過程,估計此啓大致寫于開成二年五六月間。
《謝紇干相啓》(簡稱《謝紇》)與《謝襄州李尚書啓》(簡稱《謝李》)皆載列于《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三《謝官》條目下。溫終生仕途偃蹇,我們本就懷疑他究竟有幾次機會,能使他象《謝李》 那樣“托羊角之高風”,或象《謝紇》這樣“冥升而欲近烟霄”―說得如此隆重,都是直捷擢升至高位;以溫之措辭的準確,即使語帶誇張,若不是真接近了天家,斷不至用此等文字。而溫平生得以接近帝王的際遇,只有一次而已,就是從遊莊恪太子。故二啟所謝之官都應指從遊莊恪太子時所任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屬官。只是在《謝李》中,用“豈知畫舸方遊,俄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芝泥”之語婉言,而在《謝紇》中,用“楚國命官”與“棲于宥密”曲指而已。更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是,無論是《謝紇》所言“揚芳甄藻,發跡門牆”,還是《謝李》所言“寵自升堂,榮因著錄”皆清楚表明,溫是經由其業師的推舉薦引,才得此寵榮而有此“發跡”,才“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而“榮非始圖,事過初願”的。不能設想,經一個業師,溫有兩次如此扶搖直上的際遇;同樣很難設想,溫有兩位業師都曾薦引他平步青云。一言以蔽之,《謝紇》、《謝李》二啟,實為同一事件而寫, 所“謝”是同一個官職。
由趙璘《因話錄》“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瑴,先於雁門公為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封雁門公。”知所謂“紇干公”乃紇干臮;而他就是《謝紇》的啓主。紇干臮未曾任宰相, 不可稱爲“相公”;但觀趙璘稱之爲“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 我們受到啓發,溫也可同樣稱之, 也許本啓原來的題目是《謝紇干公啓》,至《文苑英華》成書, 被妄加了“相”字而已。紇干臮開成三年,以刑部員外郎任考官,且是“書判考官”(王讜《唐語林》卷四引《因話錄》);這個職務, 應該看作他開成二年“揚芳甄藻”(選拔文官)的繼續。 換言之, 他應是在開成二年已經任職吏部, 負責銓選官員的。
李程乃當時名儒名師、又是宗室丞相,以頂頭上司吏部尚書兼師輩身份指使他的下屬紇干臮這個書判考官選取溫庭筠,應是名正言順的。這也可從溫文中看出:《謝李》乃謝其大力推薦,謝紇則謝其順水推舟也。不管怎麼說,溫庭筠在此說的清楚,是老師器重自己的文才而向紇干推薦自己,才獲此高就的:“此皆揚芳甄藻,發跡門牆”是也。其中負責“揚芳甄藻”者是紇干臮, 而溫所從發跡之“門牆”, 指李程宅第。再補充說一句,紇干臮乃元和十年(815)進士, 李程則爲貞元十二年(796)狀元及第, 資望才德不可同日而語,溫絕不會拜李爲師,又拜紇干爲師的。所以溫的謝啓中也就是對紇干說幾句如“未由陳謝,伏用兢惶”的客套話而已。
紇干是“揚芳甄藻”或“秉甄藻之權”的官, 是選拔文官的官,也就是在吏部銓選中負責“書”和“判”的考官。據《新唐書· 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 溫庭筠當時並無功名,並無職務,他如何能有資格參加吏部這樣的銓選呢?愚以為,除了李程的舉薦(所以有文宗認可,即“帝命俞”也),紇干的推轂,溫恐怕只能是通過“用蔭”的途徑入仕的。根據《新唐書選舉志》“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從這個表看來, 溫庭筠的父輩至少爲正五品。
62.驥蹄初躡景,鵬翅欲摶扶。
驥蹄、鵬翅,指代駿馬、大鵬,自喻良才。躡景(讀如影),追趕光影,即飛騰意;《文選》卷三十四曹植《七啟》“忽躡景而輕騖。”李善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摶扶,盤旋而上,喻被擢拔而迅速高升;《莊子‧逍遙遊》“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二句自言因此 扶搖而上,幾可一展鹏程;即〈謝李〉“托羊角之高風”與《謝紇》“冥升而欲近烟霄”。
57-62 韻, 敘述回到長安後,孤道干時,多費周折,終經宰相推薦,皇帝認可而開始從游莊恪太子,飛騰有望。自此以下, 全是在左春坊司經局從遊太子時所見所歷,其中關于侍御史的描寫, 是對“比侍御史”的司直的描寫而已。
63.寓直回驄馬,分曹對暝烏。
寓直: 謂郎官以下官員寄宿直廬值夜; 驄馬,青白雜色的馬,本指侍御史坐騎,此指太子司直。《後漢書》卷三十七《桓典傳》:是時宦官秉權,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分曹,分別部曹,或分司意。暝烏,即朝夕烏,亦御史之典。《漢書》卷八十三《朱博傳》:“是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此聯自敘在所謂“霜臺”任職,與其同僚(應包括題中侍御史諸公),值夜、輪班,目睹而且身歷司經局屬下諸曹日常活動。必須強調指出, 溫絕不會把一些他自己沒有見過的想象的描寫, 寫給經歷其事的題中諸公看。
64.百神歆髣髴,孤竹韵含胡。
“百神”句,用王延壽《鲁靈光殿賦》(《文選》卷十一)“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髣髴”句意(“魯”字暗射莊恪太子李永初封“魯”王)。歆,嗅聞也,髣髴,隱約、依稀之意。句謂百神隱隱約約聞到殿中的馨香(歆享而保佑太子)。 孤竹,以孤竹所製之笛。《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鄭玄注:“孤竹,竹特生者。”賈公彦疏:“謂若嶧陽孤桐。”按“嶧陽孤桐”,語出《書·禹貢》“孔傳:“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韻含胡,謂其聲不清晰而若有若無,亦有暗示太子前程黯淡的作用。 二句描寫“皇太子朝宮臣”時殿陛間飄渺的馨香和肅穆的音樂;同時也暗示雖望太子有神明護持,畢竟前景可憂。
65.鳳闕分班立,鴛行竦劍趨。
鳳闕,漢宮殿名,後世常用以代指皇宮或朝廷。分班立,本指百官按品級和官署朝謁皇帝時依序分組而立,此指皇太子小朝廷內之班序,同時照應諸位侍御友人,言與之同侍東宮也。《新唐書百官志四下》:“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皇太子朝,則分知東西班。”《唐會要》卷二十四亦云:“太子司直二人,…凡皇太子朝宫臣,則分知東西班。”故溫與諸侍御史友人中當有二位為“分知東西班”的司直或扮演司直角色的人(是否包含溫—待考)。鴛行,鴛一作鵷,字通,猶言鷺序, 因鴛鴦、鷺鷥或飛或行,皆井然有序,舊習之以喻百官上朝的行列。竦劍趨,劍身直挺而趨身進殿;參見第8韻注引周遷《輿服雜事》。
此聯“鳳闕”“鴛行”說得隆重,其實是寫“皇太子朝宮臣”的氣象,溫自然也在所謂“宮臣”之列。考皇太子所朝之宮臣中,能持劍上朝者可謂特別。頗疑此人即開成三年拜太子太師的宰相鄭覃。《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開成三年)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舊唐書》卷一七二《馮定傳》“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新唐書》卷九十五《文宗二子傳》“開成三年,詔宫臣詣崇明門謁朔望”。《唐會要》卷二十六《皇太子見三師禮》,“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少陽院東有南北街,街北出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敕“宣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門下,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並權停。其年八月,敕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敕處分。九月敕:太子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溫本人在開成二年夏秋閒得以臨危受命,從遊而輔佐莊恪太子。太子開成三年十月被害後,溫避難于故人之家,于開成四年得以改名溫岐應京兆府試而得等第,其後經痛苦的努力和觀望,開成五年終不得不“罷舉”而“行役議秦吳”,也就是從此開始了“濫竄于白衣”(《唐摭言》卷二)的過程(直到大中十二年才如《唐摭言》卷二所言“為等第久方及第”,而勉強以一個特殊的案例得第,如《溫集》卷十一《投憲丞啟》所言“遂竊科名,才沾祿賜”。
66.觸邪承密勿,持法奉訏謨。
觸邪,本古代傳說的一種神羊。王充《論衡》(卷十七)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皋繇洽獄,有罪者令羊觸之。”後因以其辨觸姦邪之能而指御史之職,此處亦以形容“比侍御史”的司直抵制奸邪(尤指宦官)的實際行為。密勿,意為機密;《三國志》卷十六(《魏書》卷十六)《杜恕傳》:“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訏謨:大計,宏謀;《詩•大雅•抑》“訏謨定命。”毛傳:“訏,大;謨,謀。”鄭玄箋:“大謀定命”。此聯謂“比侍御史”的司直,承皇帝的密旨抵觸奸邪,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支撐皇朝的大業。
按以上63、 64、 65、 66四韻的順序似應依次為63、 66、 65、 64。 這樣第63韻“寓直”、“分曹”寫“侍御史”的日常活動便和第66韻寫御史的職能使命密切連貫了。而第65韻“鳳闕”“鴛行”寫“皇太子朝宮臣”的氣象,接以64韻“百神”、“孤竹”宮中焚香的肅穆和奏樂的莊嚴也密切連貫。 而照目前的順序,第63韻“寓直”之後接言64韻“百神”、 65韻“鳳闕”兩聯而描寫宮中氣象,然後再回到描寫御史功能的第66韻,順序似嫌混亂。這種錯誤應是排版時“串行”(是“串列”)造成;舊式豎排版,每列兩韻,把前一列的上半,接上後一列的下半;而把後一列的上半,補上前一韻的下半;是《百韻》這樣的長律排版時容易發生的失誤。
67.鳴玉鏘登降,衡牙響曳婁。
鳴玉,參第10韻解。 又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章表》:“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登降,猶進退,指登階下階進退揖讓之禮。衡牙,《禮記‧玉藻》,“佩玉有衡牙,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孔穎達《正義》:“凡佩玉必上繫衡,下垂三道,穿以賓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于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触璜而為聲”。曳婁,此謂餘音搖曳不絕。語本《詩‧唐風‧山有樞》“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毛傳:“婁亦曳也。” 二句寫東宮群臣進退有節、正大堂皇,謹事儲君。
63—67韻, 寫左(右)春坊“司直”的日常活動及眾宮臣“詣崇明門謁見”太子的氣象,尤其此中關于“司直”的描寫, 自有溫庭筠身影。
68.祀親和氏璧,香近博山爐 。
觀此二聯所用動詞, 相親相近,其中似有人在,故求諸比喻。拙作《溫庭筠從游莊恪太子考論》(以下簡作《考論》)已有論述;“祀”諧音“嗣”,謂嗣君,即指莊恪太子。和氏璧,即卞和獻璞鑿得之玉。 又《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東方朔二十篇”,其中有《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等,惜已佚失。《詩集》卷一有《生禖屏風歌》當系借其題為莊恪太子事作。《責和氏璧》原文雖佚,其題目所謂“和氏璧”既是“責”的對象,必喻某人,其修辭為溫所借鑒。又“和氏璧”亦第10韻所謂楚玉也,當喻賢人。如此,“祀親和氏璧”乃暗寓“太子親近賢人”之意。由此推下句,其意當為:賢人近太子。 香,稱美之詞,與“祀”相對偶,所諧本字當作“相”,有輔臣之意, 正可指太子“宮臣”。溫〈達摩支曲〉“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很平常地用“香”和“絲”諧音“相”和“思”;這里乃不平常地用“香”和“祀”諧“相”和“嗣”,而暗指莊恪太子與其從臣(包括溫本人)。 博山爐, 拙文《考論》本猜測此語必涉太子而為太子之隱喻,并且從先唐雜說、詩賦、諸史《輿服志》有關太子部分以及溫本人的詩中共找到五條旁證;也提到《樂府詩集》卷四十九《楊叛兒》“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壚”之以“香”和“博山爐”抒男女之情;到溫的手中,稍加點化,便是寫君臣之事了。今搜雜書而得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鐘鼎彝器辨》有關記述:“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 唯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者,香爐之制始於此”,乃大喜,太子和博山爐的聯係是有歷史淵源的。“博山爐”之喻太子,可以無疑問也。以本聯為中心,63—67韻是總環境,以下69—73韻則轉寫詩人特殊的角色和感受。這種結構也顯示當時東宮之臣對太子的眾星捧月式的擁戴和溫庭筠對太子極端的忠誠。
69.瑞景森瓊樹,輕冰瑩玉壺。
瓊樹,喻擁護太子的賢人。《世說新語•賞譽》:“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輕冰”句, 鮑照《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王昌齡詩“一片冰心在玉壺”。此聯承上,寫宮中景、物而兼含喻:先言東宮之臣:以瑤林瓊樹喻太子周圍賢人眾多;再說東宮之主:以玉壺冰喻指太子方年幼而天真無邪 。
70.豸冠簪鐵柱,螭首對金铺。
豸冠,見第66韻解, 關于獬豸的類似說法很多。又如:《後漢書志·輿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後,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獸,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秦滅楚,以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 …。”螭首,指殿上陛下之頂端呈龍頭形的短柱。《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後因以“螭頭載筆”表示史官侍值。按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屬于門下省, 對應的東宮官應該是左春坊司議郎。《新唐書》卷四十九《百官志四上》“司議郎二人,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啟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錄為記注;…歲終則錄送史館。掌侍從規諫”。二句表明詩人職責所在似兼與司直、司議郎有關。
71.内史書千卷,將軍畫一厨。
内史,指王羲之,曾任右將軍、會稽內史,故稱右軍、內史。書千卷,指唐代宮廷尚保留的相當數量的王羲之書法真跡。唐張彥遠輯《法書要錄》十卷(范祥雍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有《二王書錄》。又《太平御覽》卷二百九“蘭亭真跡”條引《尚書故實》,太宗酷愛學大王真跡,以至《蘭亭》帖被藏于昭陵;唐胡璩《譚賓錄》記載唐高宗曾向王羲之後代王方慶索帖。將軍,用指晉代畫家顧愷之,《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引《世說新語•排調》“顧愷之為虎頭將軍”。畫一廚,指唐時宮廷珍藏的顧愷之畫;《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引《歷代名畫記》,顧曾以一廚畫暫寄桓玄,有所謂“妙畫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的故事。
今按:在晚唐時,王羲之書帖和顧愷之畫很可能藏于左春坊司經局所領崇文館,溫《洞戶二十二韻》中“書帖得來禽”句可為旁証。此聯透露溫從遊太子期間在崇文館看到皇家珍藏。當時溫似爲太子司直兼文學侍從,或只如“監察侍御里行”一樣,只是見習而已。但毫無疑問的是,溫確在“皇太子”所“朝”的“宮臣” 之列。
72.眼明驚氣象,心死伏規模。
眼明, 猶言大開眼界;心死,謂心中極為傾服。氣象,即規模,當謂書畫珍寶的精美絕倫以及皇家制度儀仗的豪華尊嚴。
73.豈意觀文物,何勞琢碔砆。
文物,指皇家獨有的典藏記錄和文化精品;《左傳·桓公二年》:“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碔砆,一種似玉之石頭,此謙而自比。《文選·子虛賦》(卷七)“礝石碔砆”句張揖注曰:“碔砆,赤地白彩,蔥蘢白黑不分”。二句謂本未料有此近接天家、開闊眼界的機會,今退身也不必勞官家雕琢這塊不成玉的材料了。下句帶反諷語氣。
74.草肥牧騕褭,苔澀淬昆吾。
騕褭,《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瑞應圖》曰:“神馬也。 與飛兔同。 以明君有德則至也。”昆吾,傳說是用昆吾石冶煉成鐵所制、削鐵如泥之劍;《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龍魚河圖》曰:“冶治其石(昆吾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苔澀,應喻條件艱澀不順;“澀”字用法, 參見《五十韻》“澀劍猶堪淬”。二句言說肥草才能養出騕褭神駒,澀苔亦可淬厲昆吾寶劍,寄托太子既死之後自己不得其時的傷感,和得到了政治歷練的自負。
69—74韻,用隱晦華麗的語言,盛飾自己從游莊恪太子所歷所見; 寄托自己銘心刻骨的政治感觸。尤其其中關於“司直”的第二次描寫, 令人不得不強烈懷疑是詩人自道。
75.鄉思巢枝鳥,年華過隙駒。
巢枝鳥,思江南故鄉之自喻;《古詩. 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過隙駒,時間過得很快的比喻;《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76.銜恩空抱影,酬德未捐軀。
抱影,謂孤獨自處、形影相弔;《楚辭. 哀時命》“廓抱景而獨倚兮。”捐軀,效忠獻身之謂;曹植《白馬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二句自謂感念皇恩,而當道無知音者;欲思報答,卻無效命機會。
77.時輩推良友,家聲繼令圖。
此二句自言當時人士視己為良師益友,自己也無愧溫氏美譽,應是真實寫照,非飛卿自飾也。 可與李商隱、段成式、紀唐夫、皮日休等多人評論與有關史料相證。 唐宋間筆記雜說于庭筠之誣蔑不實之詞及其後代的翻版,亟須澄清。
78.致身傷短翮,驤首顧疲駑。
致身,盡忠事君報國之謂;《論語.学而第一》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短翮,短的鳥翎,比喻個人能力和奧援皆不足飛騰。驤首:(蛟龍或駿馬),抬頭,常狀人意氣軒昂,指題中諸公。疲駑,即第2韻所謂“羸馬”,自喻疲憊無能,憤懣語。二句自傷無緣報國,愧對諸友人。
79.班馬方齊騖,陈雷亦并驅。
班、馬:班固、司馬遷;《隋書經籍志》“遠覽馬《史》、班《書》。” 陳、雷: 陳重, 雷義。《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列傳》:“太守張雲舉(陳)重孝廉,重以讓義,…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舉茂才,讓于陳重…鄉里為之語曰:“胶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句謂諸位友人文名、宦途皆進。
80.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
言爾志:孔子使弟子“盍各言爾志”, 見第18韻注。 吾徒, 本孔子指其門徒,此借用;《論語·先進》:“非吾徒也”。又《論語·子罕》:子曰“後生可畏”。二句謂昔日與諸公有同門之誼,今後生可畏,升沉異路也。
81.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
氣干牛斗,用《晉書. 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後得豐城寶劍故事。“轆轤劍”,古代一種寶劍名,其劍柄為玉制.由兩塊玉相套合而成,“環口中間似轆轤旋轉”(陶宗儀《輟耕錄.玉轆轤》),故名。二句以寶劍劍氣沖天而無人識自喻懷才不遇。
82.客來斟綠蟻,妻試踏青蚨。
綠蟻,酒面上浮起的綠色泡沫;《文選》卷二六謝眺《在郡臥病呈沈尚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張銑注“綠蟻,酒也。”青蚨,一種蟲,據說以其血塗錢上,可招同類而還。見《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引《淮南萬畢術》,干寶《搜神記》記等類似故事,後用“青蚨”代指錢。 此二句其實是說下一韻自己遭致“積毀銷骨”的根本事因, 即在江淮買妓為妻的事端。“客來斟綠蟻”者,說自己為青樓之客而飲酒;“妻試踏青蚨”者,其實是“試妻踏青蚨”的倒裝;解作娶(妓為)妻而奮力不惜錢財。
温《五十韻》于其事亦言“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說自己遊宦則没有毛義那樣的傳檄任命, 辦婚事則没有阮修那樣“眾人為之斂錢”的機遇---其實也是向李僕射訴說自己不得不謀職揚子院的苦衷;正因他在宦官勢力麇集的揚子院謀職,並且得到錢財資助而買妓為妻,才碰上仇家的残酷迫害。此聯是從詩人角度寫出了下聯積毀銷骨的原因。詳見拙作《温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
83.積毁方銷骨,微瑕懼掩瑜。
積毀銷骨,謂(由以上的行為導致的)層出不窮的毀謗會使人難以生存,語出《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文選》卷三十九鄒陽《于獄中上書自明》“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李善注:“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消滅”。微瑕掩瑜,謂以小過掩蓋大德;《禮記‧聘義》:“瑕不掩瑜”。鄭玄注:“瑕,玉之病也。 瑜,其中間美者。”溫庭筠無奈而自認“買妓為妻”是其“微瑕”。二句謂“微瑕”導致的無窮毀謗簡直要把温吞噬而否定其全人。理由如下:
其一,《玉泉子》曰:“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子留後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狭邪所費。”“多為狹邪所費”與“妻試踏青蚨”,只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而已,前者含嘲諷而失真,後者嫌刻琢而近晦耳。正因第82韻所言買妓為妻;才有本韻說的受盡誣謗,“微瑕掩瑜”的結果。
其二,溫《上鹽鐵侍郎啓》“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 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諑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折之路斷”—說的雖然含蓄委婉,其事就是第82、83韻這段為妓女贖身、買妓為妻,而橫遭誣蔑的情事:自己硬把那眠花宿柳的麋鹿狹邪之情,來效法雙飛雙宿的夫妻之愛,這不是以所遇青樓女子為妻又是什麽呢?麋鹿之情,一般解為狂放不羈,特殊解為淫放多情。《禮記月令》:“麋角解”句下孔穎達疏“麋為陰獸,情淫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而麋鹿亦是一夫多妻制的象征。鴛鴦之性:指追求夫妻恩愛、男女佳配的情性。 至于“幽蘭”句,語本《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及“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自謂像屈原好修那樣遭到群小的攻擊,被誣為“善淫”。 丹桂句,自言竟然因此不能中第而落魄窮途。
其三,溫《上吏部韓郎中啓》“諸葛之娶妻怕早”句,也說到自己老大娶妻,不得不求韓助己在揚州鹽鐵院謀職,這和《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婚乏阮修錢”之描述自己結婚沒有阮修那樣有名流為之斂錢為婚的排場又不謀而合。
其四,溫《偶遊》詩“與君便是鴛鴦侶,休向人間覓往還”及《懊惱曲》“玉白蘭芳不相顧,青樓一笑值千金。”也說明溫確實對此妓女有“鴛鴦之性”,並且爲了這位青樓女子的“一笑”,不惜千金即為之贖身,傾其所有“盡為狹邪所費”。這些證據能若合符契地證明溫破費錢財買妓為妻事,應該不是偶然的。
其五,劉學鍇《全集》卷十一《上鹽鐵侍郎啟》之校注認為《全唐文》卷七八六“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應從《文苑英華》卷六六二作“鴛鸞”,“同鵷鸞,喻朝官。朝官班行整肅有序,備受拘束,與‘麋鹿之情’正相反”。這種解釋與本句後半句直接矛盾。試問:雖個性狂放不羈,學習和效法鵷行鷺列的班序,怎麼就蒙受“善淫”的“謠諑”而斷了考取進士的路呢?
以上第82、83韻其實是在說完從遊莊恪太子之事後,回顧前塵,說到自己在江淮買妓為妻、被宦官勢力當做把柄,而受辱、受毀謗事。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和背景,則在前文第55、56韻已有說明。 江淮受辱之本末如此簡略地前後出現在本詩中,也是很多論者不能發現此事的原因。
第75—83韻:如今自傷老大而懷鄉,欲報皇恩而無緣。朋輩青雲,獨我蹭瞪,追究起來,自己在江淮買妓為妻之“微瑕”乃是受盡毀謗的根本原因。
84.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
蛇矛, 此處喻唐政府的軍隊。《樂府詩集·雜歌謠辭.隴上歌》:“隴上壯士有陳安,…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舊唐書》卷一七八《鄭畋傳》:“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魚服,《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為比喻帝王變服而被困之典。又劉向《說苑·正諫》(卷九),伍子胥諫吳王勿從民飲酒曰:“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今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此處喻“受制于家奴”的皇帝。二句謂國家政局未穩,而皇帝又受制于宦官。
85.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
“欲就”二句,謂想在其中做手腳,欺騙社會輿論(就算是當世人不知道),安能逃得過冥冥中鬼神懲罰。《莊子.庚桑楚》:“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按“就”字當介詞用,其賓語(如帝位繼承)省略;二句的主語(宦官勢力)亦然。
86.是非迷覺夢,行役議秦吴。
是非已夢幻一樣地迷失,詩人乃計劃自長安遠適吳地舊居(而淡出物議)。
87.凛冽風埃慘,蕭條草木枯。
風埃:猶言風塵、風物。二句想像冬日東歸途中所見。
88.低徊傷志氣,蒙犯變肌膚。
低徊: 流連回顧; 蒙犯:蒙受、面對(風日雨雪寒暑等)。
89.旅雁唯聞叫,飢鷹不待呼。
二句因途次所見為喻, 詠羈旅失意情懷。飢鷹,杜甫《贈韋左丞丈》“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
90.夢梭抛促織,心繭學蜘蛛。
兩句頗見雕繪刻琢。上句謂自己 “織夢”之“梭”為促織所催而頻抛,言夜間碾轉苦思而不能成眠也;下句則謂自己心緒之結效法蜘蛛之繭,紛亂封于心中而難與人言。促織,蟋蟀別名;《詩集》引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鱼疏》云:“蟋蟀,…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91.寧復機難料,庸非信未孚。
機難料,可參《三國誌‧魏志‧高貴鄉公髦傳》“高貴鄉公卒”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提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信未孚, 語出《左傳.莊公十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上句言(宦官)廢立之謀其實世人可知;而下句謂:難道不是信用尚不足以服眾嗎?好像非常隱晦地暗諷武宗,而明似批評宦官。
92.激揚銜箭虎,疑懼聽冰狐。
二句是溫庭筠的自畫像;說自己受盡傷害,激憤難已如中箭之虎, 而處境險惡,心懷疑懼如聽冰之狐。《水經注·河水一》引晋郭缘生《述征記》:“ 狐…善聽,冰下無水乃過。”
93.處己將營窟,論心若合符。
營窟, 謂經營避禍逃生之方;《戰國策‧齊策四》“狡兔有三窟, 僅得免其死耳;…請為君復鑿二窟。”合符,比喻兩件事物完全相同或一致;《孟子‧離婁下》:“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符,符節,中国古代朝廷傳令、調兵遣將等事務的憑證,以金屬或竹木等為之,作鳥獸等形;雙方各執半,合之以驗而信;參見第21韻“繻”之解釋。二句自言將避禍引退,正合諸友人之勸告,聽從明哲保身的古訓。
94.浪言輝棣萼,何所托葭莩。
棣萼,棠棣的花和萼,亦作“棣鄂”, 喻兄弟或兄弟友爱。《詩經‧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葭莩,蘆葦中的薄膜,喻疏遠的親戚。《漢書‧中山靖王劉勝傳》“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上句謂休想兄弟會榮耀自己,下句謂沾一點遠親也托不上任何方便。 案上句所謂兄弟或指溫造之子溫璋;下句則指溫與唐皇室的遠親關係。
95.喬木能求友,危巢莫嚇雛。
喬木、求友,語出《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危巢,應喻岌岌可危的名位。嚇雛,語出《莊子・外篇・秋水》:“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云云。上句自謂能求同道舊友而遷喬出谷;下句自比鵷雛,言己雖以改名事招致種種誹謗,但名位---危巢之于己,不過鵷鶵所視鴟梟之腐鼠而已。按:或以“嚇雛”為飛卿此時已經有子之證,即使與溫實際得子的時間粗合,亦恐不足為訓;蓋解“雛”爲其子,則以危巢嚇其雛,離開上下文以“己”爲中心的主線,無意義。
96.風華飄領袖,詩禮拜裙襦。
領袖,《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裙襦“之“裙” 各本皆作“衾”,誤; 蓋“裙”之古字君上衣下,而訛為“衾”也。裙襦,出《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 大儒臚傳曰: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二句言有些人看似士林領袖,道貌岸然,實不過“以詩禮發塚”的偽君子而已。又,上句或可解為詩人自詡領袖後進。
97.欹枕情何苦,同舟道豈殊?
“同舟”句,顧本校,豈一作固;此變用“同舟共濟”意。《孫子・九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二句自謂所以倚枕不眠者:本來是同舟共濟之人,“道”怎麼會不同呢?考慮“豈”字的異文“固”,此句似在譴責某人。按溫改名舉場參加京兆府試,得“等第”而罷舉,當然因為改名事泄;雖遲早要泄露,但其過程中畢竟有爭名者出賣。“同舟道豈殊”的反問,或“同舟道固殊”的反話,都似包含詩人對告密者的譴責。
98.放懷親蕙芷,收迹異桑榆。
蕙、芷,皆香花香草,以喻賢人或代指隱者家園。 《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 收迹,謂隱退;桑榆,日落時餘光所照之處,常用以比晚年;《淮南子.天文訓》“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二句言自己只好縱情林下生涯,不過隱退尚非老年(日後或猶有可為)。
99.贈遠聊攀柳,裁書欲截蒲。
攀柳,即折柳。《三輔黃圖·橋》云“灞橋在長安東,跨水做橋,漢人送客至此,折柳送別。”《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梁武帝《折楊柳》解題引《唐書·樂志》曰“梁樂府有‘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此歌辭元出北國,即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枝》是也。”截蒲,據《漢書》本傳,路溫舒父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今案:當時正當嚴冬, 不唯“折柳“為想象之語;“截蒲”亦湊韻之詞耳。
100.瞻風無限淚,回首更踟蹰。
84-100韻,詩人縱觀所處形勢:宦官罪惡,總是難逃天譴;自己遐適保身,也是無奈;親戚無所託,摯友尚可依;“以詩禮發塚”的偽君子及“道殊”的“同舟”者不必提;表現了無限遺憾而並不絕望的心情。
綜上注釋及分析:按其敘事和抒情的總體順序,全詩可分為七段。第一段為第1至第10韻,感歎自己應試失敗,經歷厄難,報國無門。第二段為第11至第29韻,婉曲道出改名(溫岐)應試的苦衷、得“等第”而“罷舉”的原委。第三段為第30至第47 韻,因而只好退居林下,故轉而描述當年隱居讀書生涯,其末有“橫經稷下”的經歷。第四段為第48至第56韻,言己仕途之初已受宦官迫害,“羈齒侯門”之後,“大樹”無依,乃“避秋荼”而赴京;其事即隱括詩人之“江淮受辱”也。第五段為第57至第74 韻, 言自至長安,多費周折,得皇帝(文宗)特許任職“霜臺”。通過描寫“詣崇明門謁見”太子等氣象,盛飾自己從遊莊恪太子所歷所見所感。第六段為第75至第83韻:如今自傷蹭瞪,亦自知江淮買妓為妻之“微瑕”,實為“積毀銷骨”之肇因。第七段為第84至第100韻,詩人鞭撻宦官,反省自身,珍重友誼,批評偽善,終能自勵而不為人生之災難擊倒也。
其中江淮受辱事,以《玉泉子》所記,與溫《上裴相公啓》、《上吏部韓郎中啓》、《上鹽鐵侍郎啓》、兩《唐書》本傳, 以及《懊惱曲》、《偶遊》等,尤其本詩比勘對照而得。從遊莊恪太子事,則賴溫詩文中《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洞戶二十二韻》、《謝李尚書啓》、《謝紇干(相)公啓》、《上封尚書啓》等多項內證繹出。“等第罷舉”及改名詳情則由本詩提供真實細節。溫平生祕事,多在此也。尚有大中期間所作《菩薩蠻》評價聚訟紛紜,攪擾場屋而貶尉隨縣一案衆說喧騰,值得深深考究;其實也與以上三事因果相及。 可見研究透徹此三事的重要性。 謹獻拙見,希望得到學界批評指正。
作者牟懷川 加拿大碧溪省立大學亞洲研究系代課教師 馬茂元教授末座弟子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