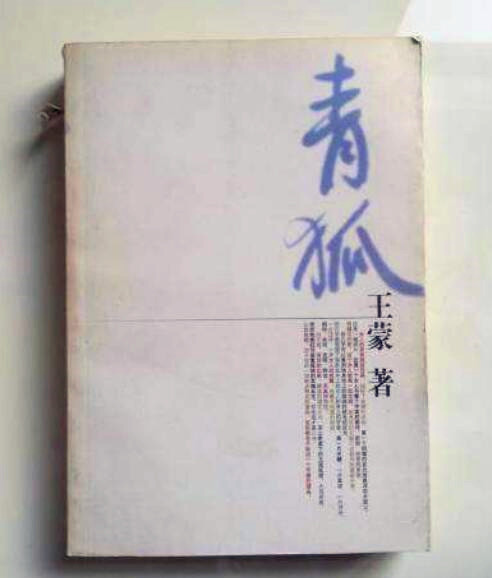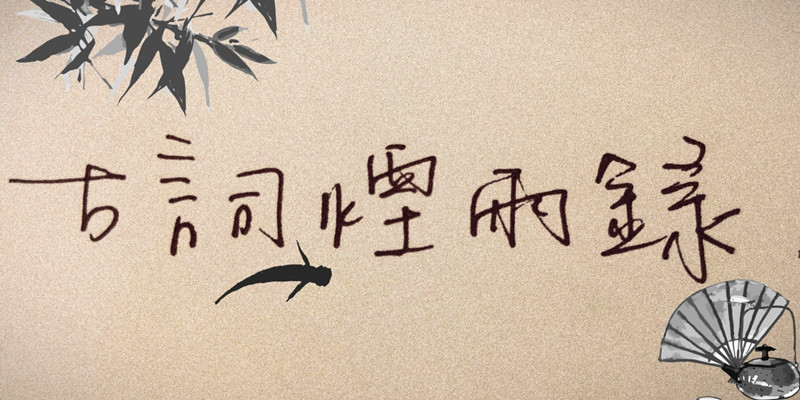《虞美人·春花秋月》:
春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由于是名篇,凡是讲古典诗词者,几乎没有不讲这首词的。所以千百年来,讲《虞美人·春花秋月》的文章车载斗量,不计其数。但能讲明白、能讲出词中深意的文章十分罕见。
至于这首词好在哪里,为什么都说好,李煜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词?——围绕这首词的这些重要问题,诗话家大都语焉不详,或者有意回避了。
即便有所涉及这个问题者,也未能给出让人满意的解释。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讲《虞美人·春花秋月》的文章,都对词的首句“春华秋月何时了”理解有误。
“春华秋月何时了”,是这首词的基调,是其中心意义的起点,是其思想情感的主脉,是其情调的主旋律。
所以,对词的首句理解有误,后边的所有议论,必定“言不及义”,或流于肤浅。
至于前边围绕这首词提出的那几个问题,更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答。
那些诗话家对这首词首句所以理解有误,毛病出在:都望文生义地把“春华秋月”解释为“良辰美景(帝王生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理解,首句“春华秋月何时了”就成了这样的意思:
“良辰美景(帝王生活)什么时候结束啊”!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作者写这首词的时候,沦为亡国之君已经将近四年了,此时的李煜怎么可能提出“良辰美景(帝王生活)什么时候结束”?一个阶下囚,难道会提出“什么时候成了阶下囚”这种没有用、却是切肤之痛的问话?
这样的理解与解释,与全词的意义很不协调;与词的基调也不合拍;更无法说明白这首词“为什么都说好”?
实际上,“春华秋月”在这里,是指春天秋天的意思。
众所周知,春天秋天是一年四季中两个最好的季节:
春光明媚,万紫千红……
秋高气爽,金秋十月……
实际上,作者是用春华与秋月这两个含有诗意的概念,寓意春天与秋天。说白了就是通常所说的“春去秋来”。
所以首句“春华秋月何时了”,应是这样的意思:
“春去秋来什么时候结束啊”!
春去秋来是有规律的自然现象。
规律意味着什么?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规律是人类不可安排、不可左右、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
于是进一步分析首句“春华秋月何时了”,就成了这样的意思:
“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春去秋来什么时候结束啊”!
首句分析到这里,便离“豁然开朗”很近了。
通读全词的文字意义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仅仅悲叹眼前阶下囚的遭遇;而是咏叹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不能看到这一点,是那些诗话家“理解有误”的主要原因。
大部分诗话家都局限在“亡国哀音”的判断上,未能看出:作者在悲叹目前的遭遇中,同时感叹了自己的一生:是“命中注定”,是命该如此,是命运的安排!
而命运在李煜眼中是不可安排、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所以作者用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春去秋来”,寓意自己的人生命运。
这种层层深入分析的结果,首句便顺理成章为:
“这样的命运什么时候结束啊”!
——至此,首句的意义便豁然开朗了。首句后边的文字,是对“命运”的回顾与咏叹。
回顾往昔的结果,使作者的情绪又起来了,情感的波澜又在心底涌起,于是词句出现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这种震撼人心的天问!如此极端的天问,在“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恰”字中达到极端痛苦、极端绝望、极端悲愤的情感巅峰!
接下来的回答,便水到渠成为意味深长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这里的“恰”字是神来之笔!增强了末句撕心裂肺的震撼力!把全词的精神力量提升到“江奔三峡,河出潼关”之际蓄势待发的高度。末句意义在这个高度上,一泻千里,汇成汪洋大海,使读者陷于无穷无尽的思绪中,不能自拔。
但是,当代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非议末句的“恰”字用得不好。他认为“恰”字生硬、刺耳,有损全篇词的整体美感。
顾随先生有所不知:词至末句,作者的情感达到极端的巅峰!恰恰是这个“恰”字的生硬、刺耳涵有的力度,增加了末句的分量,增强了末句的精神震撼力!
如果末句的“恰”字换成任何一个其它的字,例如“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原来的精神震撼力量便骤减许多,原本光彩的末句,会变得平淡无奇而索然了。
说“恰”字是“神来之笔”,是因为“恰”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收拢全部的思想情感立于高山之巅!于是才有了一泻千里的气势力量。
词中的“恰”字,充分体现出李煜是写词的高手,措辞用句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首句解释为:“这样的命运什么时候结束啊”,对全词有着一通百通的效果,使全词上下一脉相承。接下来的词意,都是首句意义的深化与延伸。
于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与评价:
《虞美人·春花秋月》其实是李煜的命运咏叹调。
但是《虞美人·春花秋月》涵有丰富而又深邃的思想情感,并未“到此为止”。让我们继续分析下去——
有一点可以肯定:《虞美人·春花秋月》广受读者喜欢,不仅上流社会喜欢;不仅学者教授喜欢;就是普通大众、一般读者也喜欢。如果《虞美人·春花秋月》仅仅是悲叹了作者个人的命运。这首词不可能有既光彩夺目、又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那么,这首词永不褪色的艺术魅力暗含着什么呢?
暗含着这样既深邃又普遍的意义:
《虞美人春花秋月》不仅是李煜个人命运咏叹调,也是人类命运咏叹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将《虞美人春花秋月》与宋徽宗赵佶的《燕山亭》相比较,便会有新的发现。
宋徽宗赵佶与李煜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都是亡国之君。都是艺术天才。都是擅长写诗填词的人。都有亡国后的作品传世。
赵佶的《燕山亭》与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属于同背景、同性质的作品。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燕山亭》用冰清玉洁、美丽动人的花被风雨摧残后、出现的凋零凄惨景象,寓意自己目前的悲惨遭遇。从而发出了悲苦无助、归国无望的哀音!
《燕山亭》写得不错,语言平易流畅,情真意切,亡国哀音悲痛凄楚,很感动人。会在读者中引起普遍的理解、同情与怜悯。但仅此而已。
而广为流传的《虞美人·春花秋月》在读者中,不仅引起普遍的理解、同情与怜悯;还必然地会引发读者思想情感的强烈共鸣!
——这就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与《燕山亭》的根本差异所在。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艺术效果呢?
显而易见,《燕山亭》是作者对眼下遭遇的悲叹,表达了对阶下囚的痛切感受,抒发出了亡国之君的哀情。
《虞美人·春花秋月》并非仅仅是对遭遇本身的悲叹;而是作者从目前遭遇出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抒发了对整个命运的感慨万千,成为一首命运咏叹调。
两首词这种不同出发点、不同着眼点的不同感受,体现出不同的思想水平、不同的精神境界、不同的情感档次、不同的审美情操。
《虞美人·春花秋月》在咏叹作者命运的同时,实质上也咏叹了人类的命运!这是引发读者强烈共鸣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
《虞美人·春花秋月》用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春华秋月”,寓意个人命运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实际上也是人类命运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
李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观?
这与李煜接受的教育有关。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教育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论语》是经典,是必读,是必修课。孔子在《论语》里谈过命运: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悟道:
自己的经历不是自己安排的,都是偶然遇到的,都是“走到哪里算那里”。他把这种人生经历谓之曰命运。他认为命运是上天安排的,所以谓之曰天命。
既然是天命,那么命运便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
这便是李煜命运观的由来。这个命运观用人类现代语言概括:
命运实际上是由无数偶然因素连缀而成的一个过程——即人生的全部经历都是偶然因素的连缀现象。这个连缀现象是普遍的、绝对的。
所以说《虞美人·春花秋月》中蕴含的命运观,也体现了人类的命运。
《虞美人春花秋月》用“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愁”字,涵盖了命运的全部意义。这也是人类命运的真实内容。
于是不难看出,李煜在词中咏叹的个人命运,契合了人类的命运。
如果说,李煜的命运观来源于《论语》;那么,李煜在词中咏叹命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达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高度——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与李煜的苦难意识有关。李煜具有深厚的苦难意识,这从李煜传世的三十多首词中可以看出来。苦难意识是什么呢?
苦难意识含有四个方面:
(1)生活之苦。
出大力、流大汗,仅能维持温饱,是一种苦。上班族,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仅能维持生活的开支!他们离富裕很远,这也是一种苦……
(2)生存环境之苦。在那些专制主义社会里,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并且只能说假话,不能说真话。这样的生存环境太苦。
(3)无奈之苦。
人世间有太多的无奈,人人都有无奈的时候。无奈会使人备受煎熬之苦。
(4)痛苦之苦。
人世间,除了傻子谁没有痛苦?
所以说,苦难意识是对人生、对人类命运既深刻、又精辟的哲学概括,成为“人生哲学”的核心意义。
都说“文学是人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那些最优秀的文学艺术,都是苦难意识的结晶。
试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到意大利但丁的《神曲》;从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德国歌德的《浮士德》;从灿烂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到辉煌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再到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个文学大厦上的皇冠,这朵永不凋谢的文学奇葩——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名著的长廊。
在这座长廊里,不断回响着以苦难为主旋律的音乐。那是人类永恒的声音!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