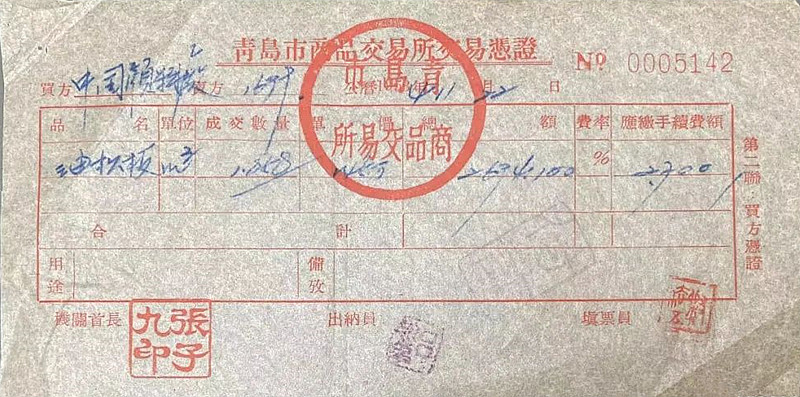首次见到朱飞,是在我们刚升入高中时的开学典礼上。一个很有些干瘦的小老头,像先前在哪本卡通书里见过的人物。看上去快近六十了,其实那时他不过才五十出头。朱飞时任年级组长,典礼上的开篇致辞就是由他演说的。我发觉他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扬眉,当他扬起双眉的时候,额上的皱纹就清晰而深邃地显露出来,等到他把双眉舒展下去,那额便似被熨烫了一回一样平整了许多。这表情丰富滑稽又显得可爱。
朱飞是班上唯一坐着授课的老师。原以为只是他的习惯,后来才知他一直身体欠佳,稍站立久些就会觉得累。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的交往是甚少的,我对朱飞性情的揣摩也只通过课堂。大概他是那种性情耿直古奥又有些愤世嫉俗之人,每每在讲解课文的中途,朱飞老师似乎总喜欢“节外生枝”地将自己对世事的一些牢骚不平之语穿插其中,语言里充满着幽默与机智。同学们许多是常常会在课上开小差的,朱飞老师这些充满个性的牢骚话却每每能给人提神,并引起同学们的会心一笑。
不曾想年过半百的朱飞老师居然还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我们的校歌就是由朱飞作词并亲自教我们演唱的。犹记得当年他坐在讲台前,声情并茂地演唱着,并时不时地辅以手势的样子。同学们的情绪委实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群情振奋地跟着他把这首夹杂着通俗和民族唱法的校歌学唱起来:“西山山麓鄱湖之滨,升起一颗璀璨的新星。我们来自希望的田野,我们来自水乡山村……”这个干瘦的小老头不止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的,且还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这个经常念叨着“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语文老师后来却有次在课堂上因我大动过肝火。那次他让全班同学默写王勃的《滕王阁序》,且居然首次下得讲台来从第一组开始挨个检查。他检查得非常认真,几乎一个没漏过,可我那次却不知犯了什么浑只字没写。朱飞老师走到我这边问时,我只是摇了摇头。我眼瞅着却才还微笑着询问我的朱飞老师即刻动了怒,剩下的同学也不再查看了,疾步就走回讲台边,然后将一本书重重地摔在了讲桌上。我头也不敢抬,听他用了愤懑的口吻说——“我原先还比较看好这个女孩,认为她文章写得还可以,没想到她这样自暴自弃……”
朱飞老师一口气说了好些话,他接下去的“是我帮你调入到文科班来的”“我还只看过你一篇像样的文章呢”“不把《滕王阁序》默写出来不要再来上我的课”等等话语字字叩在了我心上。一直以为他有些古板的,现在想来,朱飞老师真正是个性情中人。我记得我一边眼角挂着泪花,一边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那篇古文默写了出来。课后我跑去找他,还未告诉他我已默写完时,朱飞已换了和颜悦色的面孔对我了。
后来的语文课我一直都认真听着,另还将一本写有几十篇文章的日记簿给过朱飞过目。因为他在里面有留言,我一直小心珍藏着。此后朱飞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与成长。只是到我读高三时,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不得不提前退了休。这之间我买了点东西去朱飞老师家看望他,恰巧他不在,他一名与我相仿佛年纪的女儿接待了我。之后朱飞老师对我的去看望竟很是感动。有次黄昏我和两名男同学走在校园里与他不期而遇,短暂的闲聊后,朱飞老师只向我一人说让我有空去他家坐坐。这令那两名成绩优秀且也是朱飞老师学生的男同学颇感诧异。朱飞老师当即就解释说,因为只有我记挂着已退休的他。不久朱飞便叫得我到他家去,送给我一本有关议论文资料的书,他知道我在论文写作方面欠缺。他嘱咐我说送给我的书就不许再借给别人看了。我莞尔而笑,这几回的接触让我竟觉得朱飞老师像个率真的孩子。
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有半年时间蛰伏在家。朱飞老师托人带了封信给我,别致的信纸,非常精美的竖体字书写格式。我想不保存都不可能了。他对我的落榜表示难过,希望我能再返校复读。朱飞的话很是给我鼓舞,仿佛蒙昧的灵魂里打开了一个缺口闪进了一道亮光。然而,当我重回到学校,再见朱飞老师时,未曾想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最后一次见着朱飞老师是96年九月。那时我还在为着择高校而奔波,朱飞老师像往常一样把我送到他家门外。我和他约好等一切稳定下来再跟他联系。但后来进入高校我却一直未能抽出空去亲自看他。再不久我便去了外地实习,这一去就近一年。实习一回来后我便打算去看看朱飞老师,但得到同学告诉给我的消息说,朱飞老师已去世了,严重脑血栓,抢救未及时,猝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得知这个消息的刹那,我感到非常地震惊与沉痛,仿佛被打开缺口的灵魂又被重新被晦暗堵住。回味与朱飞老师最后的相见,竟没有一丝预兆。于是懊悔之心油然而生,恨为什么没有去看他,更恨当初在他执教之时为什么没有做个好学生。
同学告诉我朱飞老师具体的去世日期,我推算起来,就在距那个时间的头一星期,我曾从外地给他寄过一张贺卡和一封短信。我记得那张贺卡上是一幅平安夜的画面。我祝福他拥有三百六十五个平安的日日夜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离世之前已收到我的祝福。如果没有,我愿望他在九泉之下能感知到,他有一名学生,将永生把他来怀念。
2008年
本文载于《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
2022.6.15 A8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