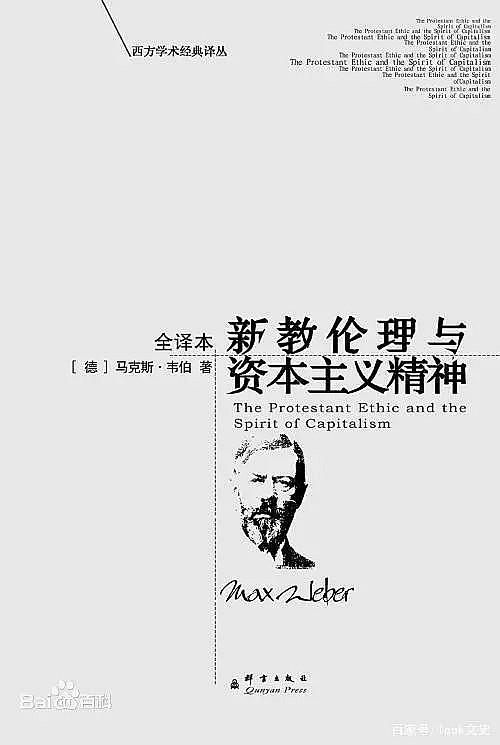实际上不同意批评民国大师的人们,没有经历民国时期,对那代大师的了解大都是道听途说。所谓的反对,都是一种良好愿望的情绪表达。并非是对人、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学术研究后的思想判断。但是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与对科学问题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必须持有不可或缺的理性——只有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才可能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才可能发现真理!
人们只会讴歌民国大师群星灿烂……就像后人只会赞叹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轴心时代”云云。对这个诸子百家时代倾注了无尽的赞颂之情。
然而“赞颂”中却鲜有人看到:决定了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社会走向的先秦文化,仅是农业文明社会的“齿轮与螺丝钉”,没有提供历史赖以进步与发展的任何思想资源!先秦后的中国在农业文明社会里停滞不前两千多年,不是个很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秦汉以降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所以最后出现转机,所以有了1840年以后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学习先进文化的结果!按照这个思想逻辑去认识民国大师,后来历史中的人们,难道不会感到仅仅讴歌民国大师,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那些“未竟”的方面,才是今人最应该思考与研究的何等重要的问题所在!
那么,这些“未竟”方面都有哪些内容呢?下面谈谈这个问题。
(一)民国大师中虽然有很多人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但没有一个人把杜威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实用主义传播给中国人。这些大师没有发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多么重要的启蒙意义;以及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杜威思想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的“更化”所具有的重大引导作用。
杜威认为任何真理意义上的理论都必须能解决实际问题,都必须有实际效用。真理不是空谈出来的,真理必须是经验过的,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所以,不是经验的知识是不可信的;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不可信的。杜威的这个思想具有重要的普世意义。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乌托邦思想家的理论一度流行的时候,杜威思想不啻为防疫苗:杜威提醒人们注意:任何拿未来说事的理论,不管怎样宏伟壮丽,都是不可信的。如果把拿未来说事的理论付诸实践,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杜威进一步指出:所有的真理都应该是对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的描绘!
然而事实上,那代大师几乎没有人真正掌握了杜威思想的精义。从那代大师的著作及其社会实践活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从先进思想的角度深入认识他们批判的东西。更缺乏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眼光认清拿未来说事的革命所必有的弊端。这一点从那代大师的学生出现的革命崇拜更可以看出来。
(二)那代大师对兴起于清末的中国现代教育(数理化等的分科专业)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已经载于史册的,这里不必赘言。
遗憾的是,从蔡元培到潘光旦,从晏阳初到陶行知,这些如雷贯耳的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没有一个人完善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他们虽然都知道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人的。但人是什么?培养什么样的人?却都语焉不详。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德育,不无道理。却仍然是教育在道德意义上的方式方法问题。并没有解决教育的根本宗旨人的问题。潘光旦对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教育,普遍出现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感到义愤填膺。他向教育界疾呼:“教育是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但潘光旦并没有对什么是“健全的、完整的人”,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他的“位育”思想其实是孔孟教育的现代翻版。虽然不无实践价值,却都是实际生活上的生存“技巧”。并没有解决什么是“健全的、完整的人”的问题。
至于晏阳初的“文字教育,艺术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都是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内容,并未道出教育的根本宗旨——培养什么样的人?
陶行知的全部教育思想是“教、学、做合一”,也属于教学实践范畴的东西,并不触及教育的根本宗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民国教育家虽然大都有西方留学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走出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有道德的人这个基本立场。仍然是从道德出发,又以道德为归宿的教育思想。这是那代教育家共同的思想局限。他们没有提出、也没有解答:教育到底是以人为先呢?还是以道学家制定的道德律条为先?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的教育堕落为工具化的培训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代大师在教育的根本宗旨上为什么未能解决人的问题呢?
那代大师虽然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基督教文化世界的背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基督教文化!
有人说胡适曾经归依基督教,后来又脱离基督教了。这个问题不讨论。从胡适一生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胡适并不了解基督教文化。未能了解基督教文化,是那代留学欧美归来的大师无可挽回的精神损失。
纵观人类屈指可数的几种文化可以看出,只有基督教文化对“什么是人”做出了最真实、最全面、最深刻的解释!当然基督教文化对什么是人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
从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揭示了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到阿奎纳的“美德伦理”思想;到文艺复兴的重现人的个性;到宗教改革的直接与上帝对话所涵有的人的权利意识;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命题”;到弥尔顿《失乐园》的回归原罪说;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张扬。终于完善出人的“基本品性”:
(1)人有自由意志。
即人天生就有自己做出判断与决断的能力。所以教育告诉学生怎样判断、怎样决断,是越俎代庖。这种越俎代庖扼杀了人的天性能力,淹没了人的自由意志。人一旦失去了自由意志,就失去了自主能力。很容易沦为统治者的工具。
(2)人有理性。
即人天生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人天生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教育告诉学生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告诉学生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也是越俎代庖。结果是扼杀了学生的理性。人一旦没有了理性就坠入愚昧之中。
(3)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这里的思想是一种思维能力。即人凡事会问“为什么”。这不是教的,是人天生就有的一种能力。例如儿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问不完的“为什么”。其实没有人教儿童凡事问“为什么”。所以教育必须呵护、养育、完善、并勃发学生的这种以“为什么”为灵魂的思维能力。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以灌输“是什么”为宗旨的教育,恰恰扼杀了学生的这种天性思维能力。所以学生毕业来到了社会上后,反而不会问“为什么”了,只会问“是什么”。这是教育的失败。
(4)人有个性。
个性是人人皆有、又人人不一样的天生秉性。个性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即有个性的人便潜在着创造力;失去个性便失去了创造力。所以养护、勃发人的个性,是教育的主要职责之一。但,在统一要求、统一行动、统一说法、统一步骤、统一目标、统一理想……的“大一统”教育中,是以扼杀学生的个性为能事的!所以学生毕业后普遍地缺乏创造力。其实是“大一统”的教育扼杀了人的个性带来的恶果。
(5)人有灵魂。
人的灵魂是指:人固有的神性与魔性的或对峙、或较量的状态。神性体现了善;魔性体现了恶。神性战胜了魔性,便出现“活的灵魂”;魔性战胜了神性,便出现“死的灵魂”。“死魂灵”的人不是人死了。而是指人的神性失败了,恶战胜了善。神性与魔性的较量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及其理性。所以教育扼杀了人的自由意志及理性的直接后果是伤害了人的灵魂!
(6)人有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是与人的肉体同在的一种恒定的意识现象,与人的肉体一起来到尘世。精神家园的灵魂是爱;精神家园的表现形式是情感。所以精神家园是天生的,不是教育教出来的。即人天生知道爱;天生就有情感;天生就会喜怒哀乐。所以教育如果教导学生必须爱什么,必须喜欢什么,必须恨什么,必须追求什么,必须扬弃什么——都是对人的精神家园的破坏。诚然,人的精神家园需要后天的充实、丰富与提升。但,那都是个人的精神活动——例如读书中自然而然实现的。所以教育未能培养出学生终生不衰的读书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这个“失败”直接导致了社会人不愿意读书的普遍现象。学生时代未能养成读书的习惯,是社会人精神家园贫瘠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基本品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呵护、养育、完善、勃发这些天生的基本品性,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教育的所有目的、内容及方法,都是以这个“题中应有之义”为前提的!
遗憾的是,民国大师中的教育家所理解的教育宗旨,并没有立足于人的这些基本品性之上。
(三)民国大师虽然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却没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里为什么没有科学?”给出正确的解答。所以那代大师的文化批判往往停留在表层意义上,未能进入文化的深层问题里。这与那代大师缺乏对科学的透彻理解、缺乏对产生科学的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有关。所以那代大师中无人能总结出:
“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文化没有科学,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
“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用数学计算出来;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可以用数学方式予以表达的”。所以德国数学家高斯这样总结:数学是科学的皇后。
“中国文化里没有完整的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直到晚清时期,中国文化里的数学最高水平是《九章算术》。《九章算术》里连初等的平面几何都没有。”
如果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后”;那么,中国文化里没有完整的数学,哪来的科学?
科学研究需要逻辑思维,中国文化里没有逻辑学。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也不可能有逻辑思维。
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精神。有人拿实事求是比附科学精神,其实两者之间没有完全的“等理”关系。实事求是仅仅是从实际出发、从事实着眼的一种方法。但从实际出发、从事实着眼并不一定发现真理!真理既要有事实根据,又要经得住逻辑检验。所以科学精神是:“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但是那代大师对科学精神并无这种准确的表述。
(四)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诸子百家,特别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这些文化大师在内的历代文人,都不研究吃饭问题,不研究发展经济问题。所以有人说:中国文人都不食人间烟火!
那么,群星灿烂的民国大师,又有谁研究过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研究过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又有谁追问过中国有史以来的历代王朝为什么都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处于贫穷之中?为什么中国蹒跚在农业文明社会里两千多年,长期停滞不前?
所以说,民国大师与不计其数的历代文人一样:都不食人间烟火——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民国大师像历史上的历代文人一样,也没有注意到:吃饭问题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是文化的首要问题,是国家必须首先考虑解决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应该批判的!这样的民族是应该反省的!这样的文化是应该检讨的!
然而那代大师鲜有人站在如何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这个基本立场上说话;鲜有人发现: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能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致富的康庄大道!那些留学欧美归来的大师,虽然都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里完成了学业。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用市场经济国家的富裕与发达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去对比农业文明社会的中国之贫穷与落后,从而发现中国有史以来,社会的普遍贫穷与落后的根源在哪里!
民国大师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是对的,精神是可嘉的。但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学与民主为什么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出现在农业文明的中国?那代大师鲜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社会公正与法治,市场人需要在自由、自主的社会机制中参与市场活动。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这种社会机制才是滋生民主与科学的唯一土壤!但是那代大师只知道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却不知道离开了市场经济,民主与科学都是一句空话。与其说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难以出现民主与科学,不如说:缺了市场经济的中国文化土壤无法生长民主与科学。但是那代大师在批判传统文化中,却鲜有人会利用市场经济这个足以彰显中国问题的思想坐标,突出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对于“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育出市场经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代大师只有钱穆一人做出了解答。但钱穆的解答却是错误的!
钱穆认为,市场经济所以出现在西欧,与那里的地理环境有关;市场经济没有出现在中国,与辽阔的中原大地适于农业文明发展有关。很显然,这个说法属于牵强附会了。说明钱穆根本就不明白:市场经济所以萌发,与人的生活需要有关,与人的致富欲望有关:
实际上在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人类生活用品不可能都“自足”,总有些生活用品是他人拥有、而自己所没有的。于是人类想到了用自己盈余的物品去换自己没有、别人却拥有的东西。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便是市场交易的出现。随着这种市场交易的发育、发展,人们发现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替代物与物的交易,要方便得多。即用大家都认可的东西直接去买自己需要的物品,非常便利。这种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就是货币。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经济愈发迅速发展起来,终于出现大规模的市场交易,这便是市场经济的由来。
钱穆避开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这个基本常识,大谈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地理因素,是避重就轻,还是言不及义?
实际上钱穆不知道、他也不愿意知道: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展、市场经济的未出现,都是钱穆崇拜的孔圣人教诲的结果——
孔子告诫所有的君主:商人谋利弃义,投机倒把,总想发财,最不安分守己,他们是社会的最大隐患。孔子把商人视为可鄙的小人。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天地君亲师农工商。孔子进一步提醒君主不要发展商业。以避免或减少商人的出现。
孔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战国时的李悝、商鞅等——这些为维护君主统治不遗余力的“法家”,发展出“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项国策为历代王朝推行不辍。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不是中国人不想致富,更不是中原大地仅适于农业文明,不适于商业文明。而是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国策造成了中国商业的不发展!
钱穆人称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重农抑商”这个历史常识。钱穆避开这个常识高谈阔论什么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是源于他一辈子钟情不易的儒家文化,他不愿意承认:是儒家文化遏制了商业文明的发育与发展,致使中国人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社会的贫穷与落后中。钱穆做学问如此不能实事求是,真是有失一个学者的身份呀!
(五)如果说民国大师群星灿烂;那么,众多的民国历史学家更是“竞相争辉”了。但是,正像我在《批评中国历史学家》一文中所说的:民国历史学家虽然名家辈出;却鲜有在学术上创新建树者。他们的著作大都不过是二十四史的流风余绪。关于民国的历史学家,我已在《批评中国的历史学家》中详细谈过,不再赘述。这里仅指出两点:
(1)雷海宗是“众星闪烁”的民国历史学家中,唯一具有卓然不群的史学思想的学者。他的“贵为万人之上的宰相,与无立锥之地的贫民,都是皇家的奴婢。家有万贯财产,皇帝一句话便立刻化为乌有”——这个说法,在当年有着惊世骇俗的力量!其暗含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个思想,可谓石破天惊!然而由于雷海宗是“战国策”的代表人物,由于后来“战国策”属于反动的思想流派;更由于雷海宗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秋成了阶级敌人。雷海宗的这个卓越的史学思想被长期湮没了。直到今天,中国史学界、思想界也没有人重视雷海宗的这个不乏重要启蒙意义的史学思想。因为雷海宗的这个思想可以颠覆史学界流行的“中国历史上是私有制社会”的观念。史学界都忽视了这样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所谓私有制社会从何谈起?雷海宗之所以了不起,他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历史事实中发现了真理!
(2)民国的历史学家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像钱穆那样“泥古顽冥”;一个是像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侯外庐、郭沫若等人那样食洋不化。钱穆陈腐的史学思想,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批判过了,这里不赘。不过有必要重述一下为什么说那些历史学家食洋不化?
民国历史学家的食洋不化主要表现于:他们根据十九世纪欧洲兴起的历史规律论,误以为历史是有普遍规律的。于是便用西方的历史分期的概念,套用中国的历史。例如用奴隶社会套用中国的三代与春秋列国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完全不同。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西方的那种奴隶社会。
例如用封建社会套用秦汉以降至满清垮台这段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这段两千多年的历史,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西方那种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西方的封建社会虽然“封土建邦”,但却一直是“双套马车”统治社会。即教会与国王共同统治一个社会,这是一种“分权”统治体制。中国秦汉以降两千多年里,一直是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国家推行的是在所有的涉及国计民生的方面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要害是集权!这种皇权中央集权统治体制,在人类历史上为中国所独有的政治体制。
西方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的这种中央集权制社会。西方也从未有过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土地公有制,农村公社组织形式。
所以东西方的历史社会形态完全不一样。历史哪来的什么规律!规律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家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同,历史规律从何谈起?
(六)都说欧美留学归来的民国大师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代大师虽然大部分有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却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就是胡适这个大家常说的自由主义者,也并非是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更遑论其他人了。从胡适的著作及其社会活动家中可以看出,胡适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可谓知之皮毛。至少关于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他并不太清楚。例如关乎自由主义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从未见胡适谈过,这里试举几例:
A、自由主义源于基督教文化。其它人类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意义是:人天生就有自由意志。这是基督教圣人奥古斯丁发现的。
自由意志意味着人的判断能力与决断能力,以及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这些理性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保护这种天赋能力就是捍卫人的天赋权利。当然,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财产。所以财产权是天赋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
B、自由主义认为,如果说政治是解决人的权利、权力、利益问题的;那么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天赋人权。民主宪政的中心意义就是限制国家(政权)的权力。
C、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最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经济体制:人可以自己判断,自己决断,自己参与经济活动,自己挣钱满足自己的致富欲望。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性化的经济体制,任何其它经济体制都程度不同地伤害了人性。
D、自由主义认为,任何治国都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及天赋人权的破坏与掠夺。所以治国在自由主义看来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全部的人类史证实:国家的长治久安、民富国强,都不是治国治出来的,而是在民间自治中实现的。例如汉朝的“文景之治”所以能创造了国库殷实的财富为后来的汉武帝穷兵赎武瞎折腾提供了物质基础。都是文景两朝不同程度的民间自治中实现的。例如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大陆富得流油,都是北美大陆在英国政府推行高度民间自治中出现的。所以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社会形态是高度的民间自治。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里几乎属于阙如。只有《道德经》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晦涩地接近这个思想。
E、自由主义认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呵护、养育、勃发——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天生的基本品性。这些基本品性就是前边谈到的:自由意志,理性、思想、个性、灵魂、精神家园等。自由主义这个教育的根本宗旨的潜台词是:
教育不是道德律条意义上的;教育不是培养学生成为听(谁)话的人;教育不是培养什么接班人;教育不需要培养学生爱什么。爱本来就在自由意志里,在灵魂里,在精神家园里,爱是天性。所以爱什么是学生自己的权利。中国文化里的“孝为先”其实是多余的教育。动物都知道“虎毒不食子”,“跪哺”,“反哺”,何况人乎?
所以自由主义认为,任何违背上述教育的根本宗旨、违背“潜台词”告诫的做法,都不是人的教育,而是对人性的戕害!人类不同文化的不同教育的根本差异是:人的意义上的教育与非人意义上的教育之差异!这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
F、自由主义认为,劳动只能创造物质,却并不必然地创造财富。财富是在交易中出现的。自由主义的这个思想,不仅道出了农业文明社会里的中国人为什么一直贫穷、也指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经济匮乏、商品短缺”——都是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以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既实现了个人致富;又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里伟大的官民共识。这个共识思想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
上述这些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胡适等民国大师的著作并未具体表述过。所以说:没有掌握先进文化的核心思想自由主义,是民国大师最突出的思想缺憾。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