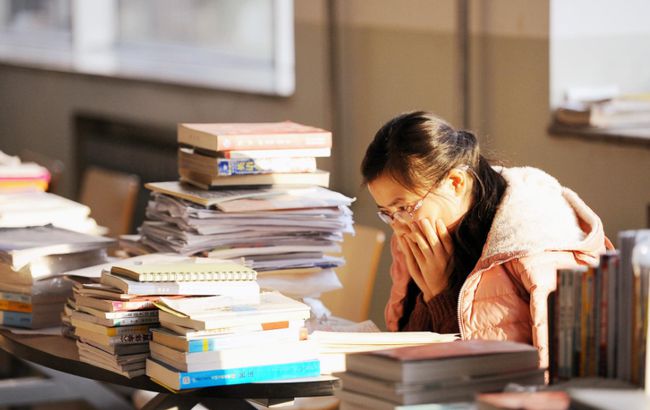210
写F医生的判断只是一家之言,对O的赴死之因仍是众说纷纭。不过,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相信:O已经不爱Z了。O对Z的爱情已不复存在(O成了整个笔记的突出人物,死亡成了整个笔记所关注的)。写O的遗书,谎言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要选择你。”(是的,这肯定是谎言。不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爱下去而要离开他,尤其是离开这个人世)。O不是能说谎的人,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曾子曰,他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实际上只对了半句,也就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不,连这半句也不全对,因为一般情况下,鸟死的时候是不叫的,只是默默地死去。除非受到天敌的突然攻击,会尖叫,有时连尖叫都来不及,成了天敌口中的美餐。受到人的攻击的时候,记得我小时候用弹弓打过鸟,打中的话,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从树上掉了下来。枪击的话,就更来不及叫了。另外半句则是谎话,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的一生是否诚实地活着,不论对自己,还是他人,这实在是个天问。或者说,只有上帝才清楚。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还有,人是特别爱说谎话的,尤其女人们。不,尤其男人们。不,尤其所有的。还有,一个人谎话的时候,已经是罪了。如果明明知道,还要谎话,那就又加了一层。如果明明知道,还要谎话,还要否认,那就又加了一层。我想起来的是索尔仁尼琴,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他说得更加尖锐,指向的不仅仅个体,指向的并且主要指向的是专制政权或极权组织)。写还有(这的还有是史铁生的还有,也是我经常说的还有的还有。一个语气性词语。是的,没错,词语或语句是有语气的。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往往表现出语气,只是没有意识到,不自觉地。有时候由于语气的不同,语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有时活泼,有时生硬。有时迷人,有时令人讨厌。到了写作的时候,一个人又往往失去了语气,意识不到语气的存在,自觉地去表现语气,反倒往往拿腔拿调,装腔作势,多么大的损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过“诗即语气”的诗论。诗要表现出的首先是一个人的独特的语气,才能把要表现的表现得活泼、迷人),如果(这的如果是史铁生的如果,也是我经常说的如果的如果。也是语气性词语。它常常被看作是数学进行证明或逻辑进行演绎的条件语句。在写作的时候,思考的时候,猜测的时候,特别说话的时候,又常常成为先导词,用得好的话,又成为语气词),如果她不爱画家了,如果仅仅是不堪忍受那“征服”以及“寒冷的燃烧”了,她为什么不离婚?(史铁生的还有和如果和我刚才的刚好是吻合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或者说,只是简要地点了出来,史铁生是完整地。这对于O的死因的理解是必要的。或者说,对于死亡的理解或欲望的理解是一个人必须去理解的,这不是什么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它当然是哲学问题,像加缪说的,更重要的是对于造物主的理解,人的原罪的理解,悔改的理解,惩罚的理解,甚至复活的)。O绝不是那种被传统妇道(从一而终——括号是史铁生的括号,说明下)束缚的女性,以往的离婚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她还爱着Z,那个死亡的序幕又怎么理解?而且在那序幕与死亡之间,O几乎没说什么话,从始至终不做辩解。或者,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可那显然不是仓促的举措——那条漂亮的鱼早就准备好了,已经晾干或焙干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了(还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一个人想死的话,其他人的人又怎么知道呢?救回来,上帝啊)。
211
写Z的同母异父的弟弟HJ说:“别人很难想像O曾经对我哥有多崇拜,简直……简直就像信徒对上帝。是不是T,我没夸张吧?”HJ笑着问身旁的T,同时指指T:“反正她从来没对我那样过。”(T的明智可能就在这了,即使不崇拜上帝,她也没崇拜过人,连她看上的男人。人不值得崇拜。人只需要人,就像情欲只需要情欲,性欲只需要性欲。有时候以爱的名义,实际上是情欲所致。有时候以恨的名义,实际上还是。又自恋又自弃)。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原词写的虽然牛郎织女的悲剧,实际上写的尘世间常见的无奈。这的金风实际上暗指的男性性器官,它好像金做的杵一样蠢蠢欲动,像强硬的风吹过树叶,树叶战栗不已。这的玉露暗指的女性性器官,它好像花朵上的露珠一样圆润丰满,等待着外部的力量的相融,又一碰就破了,又可以又一次一夜间产生出来。这的一相逢暗指的相交或性交。这是修辞的做作、虚伪。而胜却人间无数的无数,则是谎话。人不可能阅尽无数的女人们或男人们。或者干脆说,日尽或被日尽。O恰恰喜欢上了,上了它的当,O却不知道。说有点儿俗,又说千古绝唱。O不俗吗?不性交吗?不想吗?被日吗?为什么有点儿俗呢?还有,不说胜却人间无数了,起码胜却她的前夫的话,那又为什么不爱了呢?去死了呢?O不仅仅上了它的当,还中了它的毒,也就是陷入了拔高爱情的陷阱,陷入了对人性幽暗的不认识的深渊。而人正是认识了人的人性的幽暗的时候,才会理解人的爱或爱情多不好,又多好,以为以好的方面来减弱或抵消不好的方面,甚至以好的方面来影响不好的方面,甚至引领它、提升它、改善它。这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同一首,又不合逻辑又不合情理,不展开分析了。总之,汉语文化里面充满毒素,就像那条漂亮的鱼一样,又漂亮又剧毒。O表面上是死于那条鱼,实际上死于汉语文化)。T说:“其实他们俩谁也不大懂爱情。”(T真的现实极了,看穿Z那样的画家的才华,又看穿O那样的女人的心理)。T说:“他们俩,一个需要崇拜,一个需要被崇拜,需要崇拜的那一个忽然发现她的偶像不大对劲儿了……另一个呢,看吧,他或者再找到一个崇拜者,或者在自恋中发疯吧。”(T预言出了O的结局,又预言出了Z的吗)。写女权主义者(上世纪中期兴起的这个世界性的概念或运动,实际上是白左们为了政治利益而鼓噪、借用或吸引女性力量作为筹码或票箱的阴谋,夸大了女性的弱势现象,激发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仇恨,自愿合作的两性成了对立排斥的两极,演变成一场持久地反社会、反人类的政治运动,又成了一代一代的女性的观念指南或行为的葵花宝典,愚昧之至,好笑死人了。而最近或最新流行的概念或运动,叫metoo,女性受到男性性骚扰的代名词,性骚扰的案例一个接一个,所有的女性都好像成了男性的性骚扰对象,真是人类的壮举了。男性们又被搞得个个自危,人心惶惶,会不会由于某个女性的揭发、控诉上了热门的名单。实际上栽赃的多,真实的少。恶意的多,善意的少。真的日他妈的一样,花样百出,居心叵测,丢人现眼,无济于事,属于又坏又蠢的那种。真是蠢人垃圾运动。还有环保主义,也是白左势力所为,同样地迷惑人们,臭名昭著)。写“你还是那么相信平等吗?”T问我,“您不如相信自由。”(T真的明白极了。还有,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我前面引用过几句,T可能看到过,明白了。还有,关于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这几乎这个国家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或大V们的热门话题,也是糊涂话题,没有几个拎得清,明白的像T那样)。写servant。
212
写Z的继父说我们家的女人都是好女人,我们家的男人没一个像男人(我想起来的是我也感同身受,说过这样的话,对我妈,对我那个侄女,对她的上两个月才病逝的父亲。我本来还应当对我的父亲,可他不是上班,单位的工作离开了他不行了一样,没有时间。退了休又成了我弟家的servant,像我妈一样,没有时间。又死得比我估计得早得早得早点儿)。
213
写O,不管是因为Z令她过于失望,还是因为所谓“生命的终极意义”让她掉进了不解的迷茫,看来F医生的判断都是对的,她的赴死之心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但是,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赴死的序幕呢?或者干脆是对所有男人的失望。L说:“O真是一个勇者,为我而不及。”
214
写女导演N说:她是对男人失望透了。性是爱的仪式。
215
写WR的官运曾一度受阻,他好像是碰到过一个悖论:你是坚持你的政见而不惜遭到贬谪呢?还是为了升迁而放弃你(认为正确——史铁生的括号,说明下)的政见?写有一天傍晚,他心事重重地走出家门。落日又红又大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那园子,一下子便呆愣住不动了。不,树林他见得多了,比这更高更大;寂静和荒芜他也见得多了,比这更深更广。他望着祭坛,他看见了祭坛上的O。O正在走上祭坛,步履悠缓,衣裙飘动,长长的影子倒在祭坛的石阶上。他向那祭坛走去,拾级而上,直走到O的影子里才站下。这时他心里一凉:原来不是她,不是O,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这是N,WR以为是O(这时候的WR与N的相遇和前面写到过的F与O的相遇又混淆、重叠、重现)。写A(谁呢?Z的那个姐姐M吗)。写B(是谁呢)。
216
写这个A走进写作之夜,让我想起了Z的异父同母的姐姐M。回到了这个城市,回到了天国。女教师O后来说过:Z如果真心爱过谁,那就是M。
217
写WR对N是不是爱情,WR从未明确说过,是的,他不允诺(像Z一样。不允诺其实才是对的。允诺往往是谎话,谎话的开始。奇怪的只是女人们,喜欢男人们的允诺,甚至要求。不允诺不行)。N却狂热地爱上了WR。“你太伟大了!”N挂掉了电话(N比O果断嘛)。
218
写N说:O错了,她大错了。
219
写F说:“不不,也可能O和那个男人之间什么事都没有。所谓的越轨行为,那只是Z的猜疑,是他的愤怒所衍生出来的感觉。”O不解释。写就在这一刻O看见了死的契机。她最后说“你不要,你千万不要……”她希望Z不要怎样呢?
220
写不过,T又说。N也说。T和N都提醒我们注意O给Z的那句遗言: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要选择你。N说:这是女人们典型的自欺,其实O只是每一次都相信她还是爱Z罢了。Z爱的是那座美丽房子里的女孩儿,甚至不是那女孩儿本人,而是由那女孩儿所能联想的一切,正像他说的,是崇拜和征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倾向。或者说,施虐是由于被施虐,被施虐者又反过来施虐)。
221
写HJ说:“不不,我要为我哥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像别人想像的那样,只爱他自己。”(我想表扬下这个HJ:一个弟弟或哥哥站在哥哥或弟弟这边为哥哥或弟弟的情况辩护,就好像一个儿子、女儿或父亲、母亲站在父亲、母亲或儿子、女儿这边为父亲、母亲或儿子、女儿的情况辩护,一个情人、丈夫、妻子站在情人、妻子、丈夫这边为情人、妻子、丈夫的情况辩护,这个是说得通的,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上帝这边为上帝的情况辩护,一样。如果是相反的话,那就没有去配得上)。HJ说:Z也是爱M的,不是姐弟之情,其实Z是可以娶M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青梅竹马,一直非常要好……N和T都说:所以,O说她仍然爱Z,那是真的。但是她觉得她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如果她有,她还会爱他,把他温暖过来(N和T的母爱情结好像比较严重,拔高了母爱情结。如果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真的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怎么会过不下去呢?女人真的会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一个男人吗?女人们更多的时候爱的还是她自己的爱情,拔高了自己的爱情,从而认为男人的爱不如她们的。她们是百分之百的,男人们不是。她们总是想拯救男人的爱情,从来不拯救自己。她们从来不对自己的爱情失望,失望的是男人的。还擅长说谎话,猜忌男人。更容易虚荣、虚伪,对男人的期待、要求比对自己的高得高得多。更容易走向恨的深渊,恨起来比男人更恨、更狠。一旦对自己的爱情失望了,好像就剩下了一个方向:去死)。
222
写WR说:“不不不,如果她仍然爱着,她是不会去死的。毫无疑问O已经不爱那个画家了,但她是不敢承认。”WR说:很少有人能具备这样的勇气。虽然她说她仍然爱他,但那是不可信的。WR说:“O,她不敢承认旧的已经消逝,正如她不敢承认新的正已经到来。那序幕,无论发生了没有,无论发生了什么和到了什么程度,她的死都说明她不能摆脱旧的束缚,而且无力迎接新的生活。”WR说:“无力选择爱的人必定选择死。这才是她赴死之心真正的由来。”(我想对WR说的只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超过另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还是相反?或者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识越是超过对自己的认识,越是有益于对自己的认识,或者相反,越是对自己的认识差之千里?反之亦是。二律背反的悖论吗)。
223
写残疾人C倒是同意WR的某些看法,他说:“是的,爱着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包括只爱自己的人。”C说:能让O去死的,一定是对爱的形而上的绝望。因为,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往往是确凿存在的,理智不愿意看见的东西,本性早已清晰地看见了,意识受着欺骗,但潜意识不受束缚。实际上,O,她的潜意识一直在寻找着死的契机,或者是在等待赴死的勇气。她已经不爱Z了,或者,爱也是枉然,爱本身也是毫无意义。这样的宣布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需要一种语言或仪式。这语言或仪式能是什么呢?性!爱的告白要靠它,不爱的告白还是靠它。C认为:性,可以是爱的仪式,也可以是不爱的仪式,也可以是蔑视爱的仪式,也可以是毁掉貌似神圣实则虚伪之爱情的仪式,也可以是迷途中对爱的绝望之仪式。那个死亡之幕,是哪一种呢?C说:“这心理是:爱情原来也并不是什么圣洁的东西。”C说:O在走向那个男人的时候,借着酒意,潜意识指引她去毁掉一个神圣的仪式,O的心里有一种毁掉那仪式的冲动,毁掉那虚假的宣告,毁掉那并不为Z所看重的爱,毁掉那依然是“优胜劣汰”的虚假的“圣洁”,毁掉那依然是有些心魄被供奉有些心魄被抛弃的爱情,毁掉一切,因为存在注定是荒唐的心灵战争,光荣在欺骗,光荣在卑贱搭筑起的圣台上唱着圣歌,毁掉这谎言是何等快慰!C说:那便是死期的到来。在O的眼睛里,那也许是假期的到来,是平等的到来,是自由的到来。这时O才发现,她是恨着Z的。那个序幕之所以发生在那样的时间和地点,正是O下意识的报复,她下意识想让Z的高傲遭受打击,让他的理论遭到他的理论的打击。所以她说:“你不要,你千万不要……”她不要他怎样呢?(她不要他高高在上嘛!她不要千万得意洋洋嘛)。我为什么恨他?我曾经那样爱他,现在为什么已经不爱了呢?因为他不好。可是,这还不是择优而取吗?优胜劣弃,那么又与Z的理论有什么不同?不不,爱,不能是对美好的人或物的占有欲,而应该是对丑恶的拯救!但是,爱,难道不包括对丑恶的拒斥么?可这拒斥,这样的取与舍,不又意味了高低之分和心灵战争的酿成么?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她能够像死亡一样平等、自由、均匀地漫展、无处不在么?——这便是O至死的爱的疑问(我想起来的是我写过一个非诗,写我对爱的理解。我当然想起来保罗的话,更加想起来主耶稣的话。我把主耶稣及保罗的话,还有我的理解,分别写入了非诗。在这提到下,不放这了。其中我的理解的那个有点长了,比较占篇幅。还有,我还想起来要爱你的敌人的话,人几时才能啊,上帝)。
224
写F也请我们注意O的那句遗言: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选择你。F强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强调的是“这个世界”,强调的是“这个”。所以F说:“O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力量爱了,但在另外的存在中她仍然在爱,仍然要爱。”(我想起来的是,和我一起打过工的一个家伙说:你在这儿过不去的坎儿,你在那儿还过不去。我还想起来的是小时候,我的最好的同学陈桢——他后来离开玉门,去了新疆,在那儿英年早逝了,比我才大一年,他说:你可以跳过一个桌子,你却让一个板凳绊倒了。有一次,他真的没有跳过一个板凳,绊倒了,手腕的骨头骨折了。他打上石膏,戴上白纱布的吊带,吊了好球几个月,才拿掉了。后来他又说:你没有发现吗?我骨折的这条胳膊要比没有骨折的这条胳膊要粗壮得多得多点儿)。
(还有:
围着O的死因的一个个声浪中,喧嚣中,史铁生的写作之夜走向了结束。这时候的史铁生缓缓地舒了一口气,目光离开了电脑的屏幕,转向了窗外:天色麻麻地透出点儿光亮,窗外的天空的穹隆、楼房的上半部分或者古建筑的顶部现出了,树梢现出了,早行的人声或汽车的零星动静过来了,又过去。晨曦还没有,离出来还有一会儿,太阳还没有就不要说了,更加还有一会儿。史铁生会点上一棵,想到喝上一口?史铁生是个烟鬼吗?酒鬼吗?我呢,我也走向了我的笔记之旅的结束,缓缓地舒了一口气,目光离开了电脑的屏幕,转向了窗外:天色麻麻地透出点儿光亮,窗外的天空的穹隆、楼房的上半部分现出了,树梢现出了。没有古建筑,有海面,海面现出了。早行的人声或汽车的零星动静过来了,又过去。晨曦还没有,离出来还有一会儿,太阳还没有就不要说了,更加还有一会儿。我点上了一棵,史铁生不拒绝的话,我也发一棵,给他点上。也可能史铁生点上一棵,我不拒绝的话,我当然不拒绝,他也发一棵,给我点上。或者,不用客气,我只给我发一棵,给我点上。他只给他发一棵,给他点上。有酒的话,就好了。我会倒上一杯,喝一口。他不拒绝的话,我会给他也倒一杯,一块儿干一口。或者,他会倒上一杯,喝上一口。我不拒绝的话,我当然不会,他会给我也倒一杯,一块儿干一口。多好啊,多好啊。只是现在,我只有廉价的烟,我从7块钱一包的点8中南海,抽到了5块钱一包的黄果树。还没有酒,好久好久没喝过了,没酒了,喝不起了。不,不是喝不起,我当然喝得起,是买不起。我比喜欢烟还要喜欢酒啊。我混淆了。重叠了。现在。
不,我清醒地很,相信得很。我想说出的是,史铁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还在。我实实在在地能够感觉到,他在那,静静地看着我。不,是观察我,考验我,审视我,掂量我,评判我,走上这个笔记之旅的每一天、每一晚,像从未谋面的兄长一样。
还有:
我不认为笔记之旅要结束了。我也不认为我给史铁生的笔记增加出什么,扩展出什么。有的话,也远远不够。我甚至认为,我没有读懂,读明白。我增加的或扩展的因而显得不当、不妥。就像我不认为,史铁生的笔记收幕了,远远没有。笔记中的人物们还在笔记的舞台上,或者说,还在笔记的语言里面,只是在笔记内部的时间的意义上暂时保持在那。而笔记之外的时间没有停顿下来,还在运行。他们甚至跳出了文本,又生存在文本之外的现实里面。
还有:
我不会客气,更不会假装,史铁生也不会。这个意义上,不会出现互谢的情况。不用互谢,那太客气,见外。非要说的话,那也应当由我。没有他的笔记,就没有我的笔记之旅。他在前,我在后。
还有:
这次的笔记之旅可以视为一次灵魂之约的见面。也就是他的笔记是我和他见面的地方,虽然晚了一点。还有更好的地方,我信。
还有:
晚安。早安。
还有:
阿们)。
面海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