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月春风细如柳丝,裹着旋,从方外来,着急赶路,却对什么都陌生好奇,留了小心,犹犹豫豫古道上移,顺手把荠菜、苦菜、兔耳朵、麦蒿等幼芽,一棵棵泥土里拔出,枯草就萎下去,散开,腐烂,地皮现了绿,板板正正等春雨。三月风停在一丛龙柏旁喘息几口。它喜欢绿色。气息匀了,再下坡拐进一道弯路,听到溪水流下明山岭被鹅卵石砭出的响声,于是一支箭般地去了。春风钟情清澈透明的东西。
随后有辆毛驴车也拐下弯道。车崭新,去年入冬砍了几棵刺槐树做的。两只胶带的轮子,驮带厢的车架,双辕前伸,架在毛驴身上。驴儿迈开碎步,面无表情又挺惬意,鼻子一鼓一鼓,头一点一点往前挪,鼻喷热气。车架前坐个男人,不到四十岁,穿一身粗蓝布衣裳,披件黑袄,肩膀耸着,一手握根竹竿的鞭子,一手虚拉缰绳,鞭子半空摇晃,却不落到驴身上,偶尔一扬一甩,打声脆响,毛驴两耳陡起,皱皱眉头。车厢两侧的挡板,一边一双儿女,男孩大点,七八岁的样子,头戴瓜皮帽,单辫垂在脑后,穿对襟的红褂子,女孩也就四五岁,顶两根羊角辫,随着板车晃,却着淡绿斜襟的上衣,真个是红男绿女的搭配。男孩并不老实,一会站起,一会坐下,或干脆蹲在车厢里翻弄竹筐里的韭菜。韭菜一巴掌长,绿叶黄梗,沾着新鲜的黄沙土,韭筐旁还有半筐菠菜,看样像刚从菜地收割的,菜根红红的须,叶片上滚露珠。坐在另一边的是位母亲,不过四十岁,穿的是收腰素花袄,像朵全新的杏花,开在早晨,细看却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笑笑地,看儿女们玩耍,也不言声。
一家人穿戴过年的装束,离开铺集,不知去胶州赶集还是回娘家,抑或既是赶集也是回娘家吧。
拐上宽道,早起的日光,过了明山岭的半腰,冽着春的清冷和潮湿,冽着水灵,往道上洒,往驴蹄洒,往人的眼睫毛洒。车前草和吐绿的茵陈草中意这些时刻,支愣着嫩叶,不愿错过一滴。一条道就明晃晃、金闪闪的了。男孩这时正立车厢,往前望,整张脸浸在光里,愈加稚嫩,突然抬手一指:“柳树!”不远处果然一棵柳树,伫立道边,粗粗大大,枝干黝黑,一头嫩黄的绿。毛驴听到喊声,脑袋甩了两甩,喷声响鼻,可能想说男孩少见多怪,或可能要附和男孩的说话,认为柳树的确漂亮,与其他的不同。父亲也注意到了,偌大的岭坡,杨树、槐树、桐树赤条条着身子,少不了多生荒凉,只这乍现的柳树,裹了春天的巾衫,昂扬着,顿生朦胧,扬起的鞭子停在半空,嘴巴张开,仿如静止的画,遗忘的流年。
车便停在了道上。据猜测,车停下,还因一处景致。男孩、女孩、父亲,都在眺望柳树,女人侧坐着,却看到一片杏林。杏林在古道下方,隐约着几间瓦房,房顶烟囱冒出白烟。想必星星们赶了一夜的路,正没个去处,暂住杏林歇脚,却了无睡意,不停地眨眼,闪闪烁烁,煞是好看。过溪水稍远点,又一片杏林,深藏几间瓦屋,枝条也挑起花束,似开未开地开着,在另一片天空下,像天堂猛地门窗大开,众精灵探头探脑,迟迟疑疑,争相要看看世界,甚是动人,女人“呦”一声,像腹痛发出的锐叫,吓醒了痴痴凝望柳树的男人,鞭子垂至驴儿眼前,毛驴一愣,车便停了,胶皮轮胎的草屑簌簌地掉。
男孩先蹦下车,又扶了女孩由车后溜下,手拉手跑向那棵柳树。男人忙不迭瞅瞅女人,见她用手掩了嘴,“哧哧”地在笑,想是无事,待要扶,女人自己轻盈地跳出车厢,落到地上,像朵离枝的花瓣。
“还是当心点儿好。”男人嘟囔一声,挂了鞭子,也往柳树去。驴儿自己得了空,低头寻吃的,不断喷响鼻。浅浅的稀雾中,柳树拢着发髻,拢着春明,往四外翘首,静雅又安然。女孩仰着脸,视线顺着树干向上走,身子往后倾斜,羊角辫在头上像换了位置。男孩也这样看了,再猛力跳,手伸长了,要抓那些柳枝,可惜柳树是棵旱柳,根根枝条翘着向上长,就是够不到,只不停地跳跃,清辫子跟着在背后一跃一跃,帮不上忙。男人快行几步,望着男孩的样儿就乐,就有了“打柳哨”的念头。
他围绕粗黑的树干转圈,瞅准了,往手心啐口唾沫,后退几步,躬身往树干急跑,贴近树干一个飞身,抓住一根杈子,双脚踩上了树身,几个箭步就蹿近了树头,男孩女孩张开了嘴,直愣愣地不敢出声。只见父亲双脚踩实柳树的巨大分叉,一手拉紧一根树枝,一手在树冠中扒拉着找中意的柳条,先是掰断一根拇指粗的,再掰断两根细的,扔到地上,自己也回了地面,捡起柳条东扭西扭,白白的枝条脱了出来,手里只剩软软的柳皮,细细长长,却不见软,再折腾会儿送到嘴边一吹,居然发出声音来。
三人高高低低,色彩纷呈,站成一排,面对柳树,吹起柳哨,声音有昂扬有低沉,变成一板一眼,溪水的流淌声加进来,风的回旋声加进来,远处小鸟的飞鸣加进来,杏林炊烟的袅袅声也加了进来,居然是支乐谱,甚是清扬。女人本是立在车旁,眼见父子三人忙碌,这时被乐声勾引,终于按耐不住,几个回旋到了树下,在树与三人之间,扭起胶州“地秧歌”,手里虽缺少扇子手绢等家什,又有身孕,却不影响她一扭三弯的身段,活脱脱一棵胶北大白菜从地里旋转着往上生长,生生不息的脆生,活色生香的甜美……毛驴似被感染了,三条腿着地支撑躯体,一只蹄子刨地,把些新泥刨成飞花,飞去老远。哨音一落,女人双腿交叉,双臂斜伸,一个回头顾盼,眼角眉毛上挑,定住,风情万种,变回春风化雨的胶州大嫚,女孩小手张扬,猛扑了过去。
杏林里就出来一位婆婆,拄根龙头拐,一头白发,颤微微如一树杏花,她确是站在一棵杏树旁,拐头点地,合着柳哨声,合出个特别的节拍,眯眯眼望向柳树下的一家人。
2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谁的诗句?分分明明在我辞别庄园的鹅卵石,拽根白杨树枝上了溪岸时吟起。这溪岸正在古道边,木板车由我身边下了溪坡,上了横跨溪水的石桥,吱吱扭扭远去了。车上一家四口,也许五口,仔细打量过我,还指点着说笑,可他们似乎并未看见我,视我如无物,而我的确瞭望到了他们。我们隔着近百年时间的距离,他们从民国的古道上来,我往旧日的古道上走,我们迎面相遇,那些先前的人不能知晓我,而我却能明晰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时间便是阳关,西出之门关着,偶尔开启,为那些逆行找寻的人,那些看似游离的人——而故人终于不在。
一种萎靡袭击全身,我回到在明山岭庄园散步的当下,静静凝视那条古道。去年生长的占满道路的野苇割走了,留下一路苇茬,崭新的刀口根根直立于午间的日光,像些粉碎过的水纹。道北一棵柳树,不知是否还是那棵柳树,却一样温柔敦厚,远看像面扇子,颜色是绿的,打开了,扑闪着风。站在树下仰望,却是把阳伞的形,撑开着,白天阻隔声音,入夜驱散星辰。我凑近树干,它有苍老的皮肤和新生的枝条,折下来还可做柳哨,我抱住树干听,什么也听不到,又似乎听见它在写字,用深埋的根须,一个字一个字衔接,凑成了诗句: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于是转身,路南果然一片杏林,杏花朵朵,斑斑点点,开得合适,许是那柳树一不留神挥落的星星吧。我搜寻那瓦房,那炊烟,除了杏树杏花,无状之明,再无别物。近前一棵歪扭的流苏,正要发芽,像是婆婆遗失的拐杖,倒立着,无所依傍,仿佛在等待什么,是等那位男孩吗?想毕不禁又怅怅了许久。
忽一激灵,像道闪电,心道:这地方若没那棵柳树,没了杏林,失去遍地野草卵石、虫鸣水唱,失去季节循环和人的记忆,年岁与风,因丧失依附而没了形骸,人生该多空洞啊。
还好,道上总会有柳树。道上也总会有人。人们总会相遇。相遇纷纷,绝少恶人。若遭遇了那恶的,倒不失为一件稀罕事、一件有意思的事吧。
写于2017年
整理于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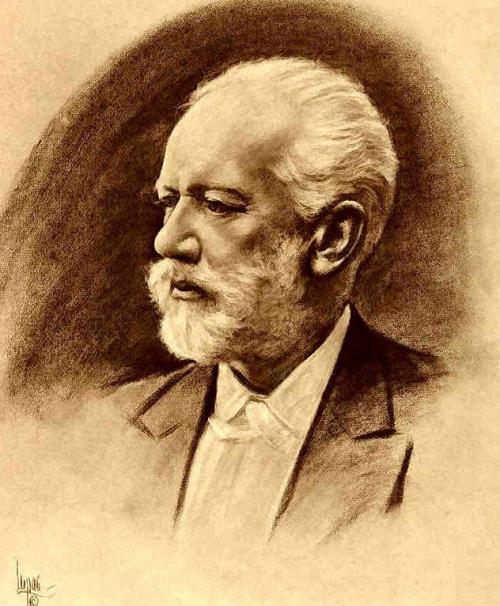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