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蓝底白字,写“黄岛路17号”的门牌,原先在券门门洞左首,靠芝罘路一边,中国电信一个线缆转接盒侧下方,现在不见了,空出的地方被抹了一刷子黄涂料。摘了17号的门牌,我想,也许为更换“黄岛路平康五里”的牌子,让这个里院从名称上恢复它旧青岛时的叫法,以正本清源,若这样,对“平康五里”百年历史的记忆或许更直面且完整些,至少称呼上,不用说平康五里即黄岛路17号,或黄岛路17号即曾经的平康五里那么繁琐了。我在它面前,站在巷子竖铺的青石板上,暮沉沉的天空下,正对黝黑的门洞,像个德国水兵,也像个日本宪兵,更像国民政府一名不怎么紧要的要员,琢磨着是否入内“打茶围”或“春风一度”。我感觉门洞里的历史就要把我吸进去了,我与之对抗,毋宁说是挣扎。我还是坚定地回到了现在,此刻比任何别时重要,过去与将来属于想象和幻觉。我重新观察平康五里,券门没了门牌,却不光秃,没少什么,也没觉得简洁,各种缆线从各个紧要部门,以不同面目,从券门穹顶争先恐后朝里钻,无半点儿迟疑,比人坚决有余。原因大概是缆线钻进去能吸收钱,而人钻进去大多需要交钱。人当然单指男人,女人很少愿意从外面往里钻的,尤其不常住里面的女人,常住里面的女人青岛本土对她们有个包含特别情感的称呼:姑娘。姑娘们住在里院四层楼内,楼上楼下斜站或仰坐门口,上百人。这么说我又回到了过去。这是个让人回忆和不时产生幻觉的地方。是个好地方。青岛人心里都这么说。但若逮住一个衣冠楚楚或气度不凡的人问:去过平康五里吗?那人便神情严肃,一脸茫然:平康五里?听说过听说过……在青岛,应是旧时的青岛,很少有男人没听说过平康五里,却很少有男人敢于说常去平康五里,特别在面上活动的男人。当然,想去终究没去成的也不在少数,主要囊中羞涩,乐费难支,与其他因素无涉。在这里一提德行让人喷饭。开了盘子,脱了裤子都一个德性。早年读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张恨水先生把一帮潦倒的报人和社会风流人物写得灰头土脸,乐池难离,尤其打茶围沐春风等举动渐成日常生活不甚理解,一到平康五里恍然大悟,原来北京的平康里、上海的平康里、深圳的平康里、高密的平康里和青岛的平康里本质上没区别,就是和古时唐朝大都长安城北的平康里比,内容亦无二致。代代相传,除了建筑换个花样,衣着愈加光鲜,腔调更似得意,人还是一样的人,灰头土脸,潮湿的地方依然潮湿,黑乎乎的地方依然黑乎乎,变白变整洁的希望渺茫。裤裆里的驴肠更多时候,不受理性和道德控制,它是非理性和堕落的产物,指向罪恶。世界上没有比人更让人绝望的了。没办法,我一头扎进长安城,在平康里不愿回来了,在那里我遇见杜秋娘,一代绝色姑娘,左腮一个酒窝,像枚月亮,明月的清辉,洒了一地。她不认识我,因此不点我,我自顾自喝我的摩卡,她自顾自吟唱她的《金缕曲》,长发飘飘,衣袂飘飘,洁如古梅: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2
平康五里券门外,几位清洁工似的中年男人,有人说是拾荒者,一辆板车上装了用蛇皮袋打包的丢弃物,主要是瓶瓶罐罐和废弃纸皮等物品,车子装满了,准备离开,又一辆空车即刻推至门前,一边忙活,一边彼此说笑打趣,像极相熟的人。我要扁着身子,举高相机才能挤进门洞。券门原用不施油漆的笨重木门落闩,如今换了轻巧的对开黑色铁栅门,向内开,贴在洞壁上。入门洞需下五级石阶,迈步约七、八米,再下两级石阶,即到院里。首先入目的是阻挡视线的影壁墙,左侧为上楼的外置单跑楼梯,向右视野开阔,既可院里闲逛,也可从里院东楼的外置楼梯上楼,楼梯从二楼直通四楼,可任选想到达的楼层,之间用单跑与双跑楼梯混合连接。四面合围的里院,视觉上由四栋四层西式商住楼宇分别占据东南西北方位合拢而成,实际上它们是个相互贯通的整体,不仅有外置楼梯方便上下,每一栋还有内置楼梯,所以即便住户较多,也不会形成拥堵。可能拥堵的是每层共用的洗漱间和厕所,它们藏于里侧建筑内,凸于楼体中间,外观则是一堵壮观的山墙,正冲券门门洞,山墙顶部的三角形高出楼宇屋顶,因是进里院的第一视觉中心,所以山墙上每一层楼开了对称的细长条百叶窗,一边两个,既为公厕通风,又使建筑避免呆板而成审美装饰,一举两得。由此,里院大院内一栋五间平房和影壁墙,疑为后来盲目建设,并非里院设计和初建之物,它们消极且有效地破坏了里院的空间序列和视觉风景线,犹如舒缓动听的钢琴奏鸣曲猛地蹦出咳嗽和吐痰的声音,不知这与教养有无关系。教养是什么?是苦读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书?还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仿佛都有关系又似关系不大。马洛伊?山多尔有句牢骚话:“教养是些别的东西,是条件反射。”不妨将之理解为教养是一个民族对美好事物的条件反射,即不用思考就能得出影壁墙不该矗在那儿,五间瓦屋不该横在里院的公共活动空间,马路斑马线没必要写礼让行人等字……若将它们移除或视而不见,这个世界会更好。
平康五里在青岛曾存在的众多里院中,说不上最美丽,也是极壮观和独具特色的,集中体现了青岛高层里院建筑的民情世情风情,是平民区的上等住宅,经百年沉淀,已是随时供翻阅的历史书册。德占青岛期间,1900年编制《青岛发展规划》,以观象山为界,以北大鲍岛等地为华人区,以南为欧人区,占据整个前海沿,而华人其实主要是平民集中在鲍岛山、台东区、台西区居住生活。这种民族歧视在建筑上也有体现。欧人区以德式别墅、商业建筑为主,容积率低,道路宽阔且风景优美,华人区则以高容积率的里院建筑为主,道路狭窄,院落逼仄,营商无序,人声嘈杂。但客观上,这些建筑,共同构成了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肌理,也铸就了人格层面的歧视性格局。时间流逝,德国人走了,日本人来了。日本人走了,国民政府来了,权贵区与平民区的城市布局未有大的改观。权贵区似天堂,风光无限,大都关门闭户,人们不断将之讴歌赞美。平民区也非地狱,拥有更多人间难灭的烟火,邻里绵延的情缘,民族文化繁衍的根脉,不知何故,却总被指责和诟病,冠以“藏污纳垢”之称——那挣扎着从平民区走出去的,有意无意加入了谴责的行列,仿若他们再非平民而属新的权贵一般,站到了平民肩膀或头顶,海鸟一样随便拉屎拉尿了,也是种“条件反射”。
入内先吸引我的,非里院壁立的楼宇,也非进进出出运送杂物的多个男人,是贴在影壁墙的六张彩纸,五张浅蓝色,一张淡粉色,除孤零零一张单在边上,其余随意贴成一竖排,一张耷拉一个角,遮住纸上的黑色数字,距离一米多也看得清,上面写:23乙,60乙,23甲,单着的写42,垂一角的只看清3甲,猜测为33甲,最底淡粉色那张写27户。我总在寻找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这些纸单,也许对我有意义。不管怎样它们让我想到“预约”。讲究的常客,若有处得妙的姑娘,或才艺特别出众抢手的姑娘,无论“打茶围”还是“春风一度”,都得事先约定。约好后,大班写个条子,黏墙上,人来了,拿条子上楼,比如取走那张23乙,找到合适的楼梯,到2号楼3单元乙房间,姑娘等在那儿,认条子不认人。若“打茶围”,跟班便端来一大壶茶,像崂山绿,四果盘盛放周围临街店面卖剩的点心,姑娘起身放下门帘,和你唠嗑,玩游戏,唱小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刚开口,你不耐烦地打断,说老掉牙了,换个,于是姑娘又唱:“蛐蛐巧,蛐蛐怪,斗完蛐蛐斗蟋蟀……”你趁机摸把姑娘粉嘟嘟的小脸,手赶路往下垂:“蛐蛐好还是蟋蟀好?”姑娘抬手一挡,脸一嗔:“蛐蛐蟋蟀都叫坏。”跟班的敲门,说添水,其实时间到了,要赶你走。你在兴头上,不肯罢休,干脆加个钟点,耍“春风一度”,跟班满足地弯腰退出,姑娘再起身,伸个懒腰,收帘子,关房门……那位钱庄的高级白领,半个月薪水就由着春风卷走了。
秋风不约而至,卷折纸单的边角。我凑近了瞧打印的小字,见浅蓝色的写“青岛供电公司电费友情提示”,原来是缴费通知。淡粉色一张则是“青岛供电公司催费停电通知”,原来此类费用也是不得拖欠的。淡粉色一点都不浪漫。依我之见,既然有了这堵煞风景的墙,干脆派它个正经用场,把唐朝另一位名歌妓徐月英姑娘写的《叙怀》诗,镌刻上面,也算物超所值。诗这样写: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一句话,无欲则刚的追求叫妙,简单纯朴的生活叫好。
3
置身院中,踩稳条石地板,旋转身体环顾,除两个角落不能尽视,其余一览无余,包括红瓦单坡屋顶之上深邃的灰蒙蒙的天空。首先是茫然。如同站立波涛汹涌的海边的茫然,眼球丧失焦点,散在各处,到处是浪花,却看不清。四周四层楼宇高耸,这面仿佛对面的镜子,高度相似,互相映照反射,层叠着景深,向极远的点玄幻而去,而我立足的点却似不曾存在,让我不知该选择从哪个楼梯上楼,到达几层,看一眼什么才叫合适。其次是震撼。这震撼让我惊呼一声,仿佛从现实世界坠入魔幻世界一声闷响。震撼的不是密布空间的缆线和晾衣绳,也不是各楼层循环的回廊和站队在回廊上的大红钢铁廊柱,当然也不是回廊中一家一户垒在走道的储物柜。说到晾晒在高空飘着、低空垂着的衣物和天长日久散落顶棚的碎瓦纸屑盆盆罐罐等垃圾,也不是。假如在某一层,前倾身子,手扶铁制栏杆,面朝下或对面,大喊自己的名字,四面包括天地都有回应,似乎叫喊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丢失的人,所有的物件都在帮你寻找,都在高呼同一个名字,足以让你瞬间患上失心症,可这也不够震撼。我感受的震撼,并非来自某个个体或单独的事物,也不是来自某一天或某个时间点,而是整体,一个时间与空间密不可分的整体,一个密度极高的整体,比如是个圆球,由钢丝吊在半空,它赞足平生的劲,用最大的弹力,从历史深处猛地出击,正好撞击到我胸口,震得我腾飞起来,让我边飞边吐尽一口长气,最后坠地而亡。接着,我意识到,我被撕成了碎片,每一片都轻飘飘的,飘去每个楼层的每个房间,落到门框上,窗台上,床上,桌椅上,大茶壶上,蛐蛐的尸体上,人的骨骼中,变成灰尘,毫无重量,却再也飘不起来了。
但是,即便我变成一文不值的灰尘,像世间万物那般消失了,我还是望见昏暗灯影下,从权贵区,走来一群德国水兵,接着一群日本宪兵,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大兵,他们从阴影中走过来,满脸酒后淫邪的皱纹,歪歪斜斜走下石板巷,极不适应地调整身体,一瘸一拐,一趔一趄,这个说“色她”,那个说“八个”,走进平民区,走来平康五里,他们用踹的方式搞开木门,下五级石阶时,腿一软,差点摔个嘴啃泥,狗吃屎。他们还是进了院子,一个美妙的院落,四面望望绮丽的景色,感到了震撼,更感到了诱惑。那诱惑他们的,是雕刻精巧的木栏杆和柱头,是一截壮美山河,是旖旎绝伦的异国风情,他们只需要攫取和发泄。他们四散在各个楼层,慷慨地施以乐资,纷纷扬扬,像漫山遍野的尘埃。然而最终尘埃落定,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他们的尸骨,被大海吞噬,再难寻觅。平康五里的屈辱,早烟消云散——历史不容遗忘。
平康五里这座旧青岛的二等妓院,与其他建筑一样,见证了青岛的百年历史。但请不要再说此处为藏污纳垢之地,那是旧中国一段真实的历史,正确正视历史才能坦然面对未来。1951年,人民政府终止了娼妓在青岛的公开活动,一座崭新的青岛开始建设,对我这个外来之人,她是个美丽的庞大的里院,前面有大海,海鸥自由翱翔,后面有青山,碧草绿树自由生长,忙碌的人们川流不息,我能够随意走走,看看,发些感慨。我们说百年历史,大可不必再谈辉煌还是耻辱。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可回避的耻辱,也有不必张扬的辉煌。把是非判断客观公正地留给后人,让保留下来的事物说话并见证就好。
等我放松了心情,捡回自我,我开始幸福地浏览这些美丽的建筑,毫无疑问,它们已破旧,但仍然美丽。美丽来自心情,来自时代。我抚摸一段残破的松木栏杆,表面被岁月腐蚀成一个洞,红漆因渗入松木肌理,洞内透着殷红,如鲜艳的记忆,并无脏污之感,只觉得楚楚可怜。一阵小狗的叫声,让我抬起头,望向对面。一对年轻恋人,早我一步到了这里,他们拍照留念,专挑那些让人楚楚可怜的背景。女孩抚摸立在门口高台上的小黄狗,抚摸它的头和耳朵,甚至搂着它的脖子,要和它亲嘴,男孩赶紧拍下这张照片。这一定是张让人落泪的照片。等他们离开,去了别的楼层,小狗着急地转圈,却不敢跳下搭建的高台,对它来说,在第三层楼望风景太高了。它只能发出急切的叫声,呼唤它的主人。
写于2017年
整理于2020年
作者简介:阿龙,高密人,生于1965年,大学新闻系毕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高密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散文专著《老家三部曲》:包括短篇散文集《发现高密》、中短篇散文集《夷地良人》和长篇散文《五龙河》。单篇(组)散文、诗歌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获第四届风筝都文化奖,第二届齐鲁散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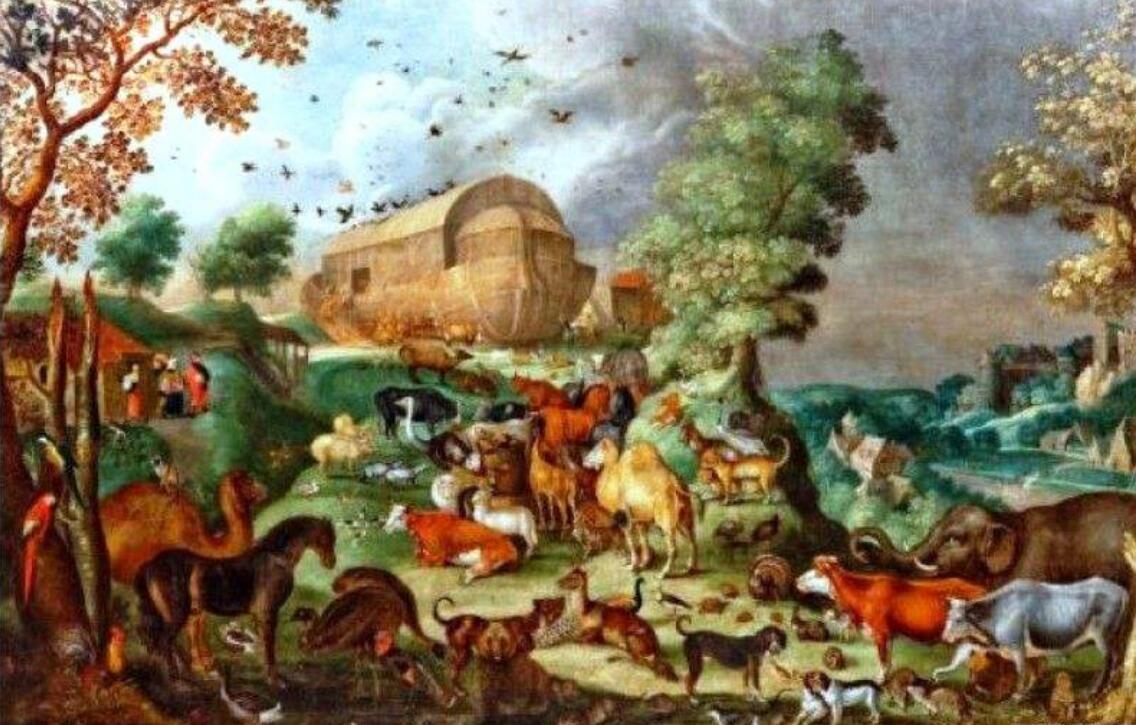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