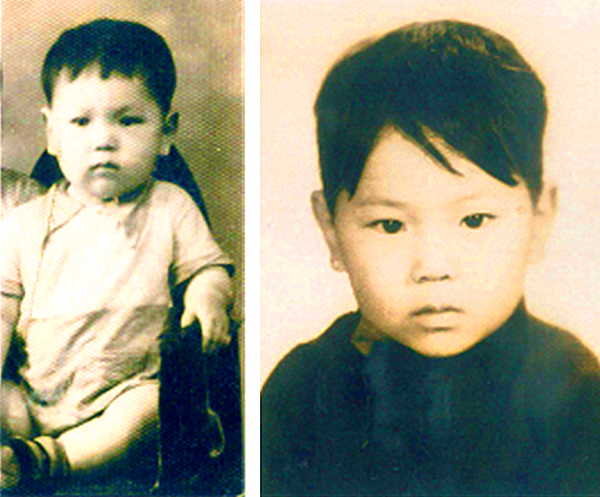大爷悄然地,永远地,走了。
四十余年,我们兄妹从出生、记事,大爷领着上街,买吃的;大爷带着下海,教游泳;大爷检查我们作业,讲化学:这些美好、温馨的记忆,点点滴滴,都已永存心中。若想在现实中寻找一点具体的痕迹,倒是还有物质的——大爷曾送我一匣红丝砚。
大爷学的是化学专业,教了一辈子中学,学生家长的礼,只收过一回,就是那一匣红丝砚。为的是我这个侄儿。
那会儿大爷总是当班主任,有个学生调皮,成绩不好,大爷死拉硬拽,拖着他考上了一个中专,让他那根本不抱升学希望的父母喜出望外,千恩万谢,跑来送了好几次大礼,都被拒收。这样的学生,在大爷的教学生涯中,不鲜见,他认为那是教师的职责,不用谢。最后,家长送来了一匣红丝砚。
“您是知识分子,砚台是文具,用得上,这,也不算礼啊”,人家这样解释。
“咋不算礼?可是我想,我用不上,你小子喜欢这些啊。哎,一闭眼,收啦。”大爷把砚拿给我的时候,有些惭愧,又有些得意地说。
我打开外面包着的报纸,露出一个碧绿色的长方锦盒,盒盖左上方贴着启功先生题的“中国红丝砚”金黄色标签。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块圆形带盖的砚台,一只笔筒,一个笔架,一对镇尺,两枚印石,一口印泥盒,都是红丝石制成。砚为仿辟雍式,砚堂在中间,四周是水槽。
其时是1990年前后,我有新砚旧砚约十余方,红丝砚,在书上读过,好像唐朝曾评为天下第一,地位超过端石,实物则是首次接触,欣赏半日,没舍得用,藏起来了。
直到1997年初,我结婚,父亲为我们订制的家具中有一张仿红木的大书案,我布置书房的时候,才打开了大爷送我的那匣文具,砚台、笔架、笔筒、镇尺,都摆上桌面。石与木,刚柔相济,融为一体,颜色也非常协调。阳光照进窗来,在几只肃立的书橱和安详的书桌之间,那一套红丝石的文房四宝,极具画龙点睛之笔。有一回,父亲和大爷来我们的新房,我指给他看,大爷头一扬:“我送的?早忘了。”
好景不长,婚后我们居处不稳定,搬过好几次家,那只石笔筒我用报纸包了几层,夹在书箱里,搬运中竟给活活压为两段,两方镇尺也摔成四截。我很心疼,虽然父亲将笔筒粘好,我也没舍得再用。再后来,我的书桌换成小三屉桌,砚也相对缩小,那方红丝砚收进匣中,只有断镇尺,仍然置于桌上,至今还在压书,压纸。
大爷还在监护室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大爷》,父亲看了,说基本是这样,但有一件事,他从未给我们讲过,当然我没法写。
这事对大爷的一生影响很大。
大爷自幼定过娃娃亲,对方是一位父执的女儿。这件亲事,两面的老人都高兴,两小也满意。父亲说那女孩子清秀、温婉,大爷引他见过,本来中学结束就该谈婚论嫁了,后来大爷考上大学,说好一毕业就结婚。断没想到,毕业前夕,大爷为了一个分配在外地终日啼哭的女同学而动了侠肝义胆,慷慨地将自己回青岛的机会让了出去。
冲动过后,他想到了未婚妻,想到了老人,赶忙写信给家里解释,可能还觉得不放心,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父亲到女方家看看,先代他赔罪。父亲接信,马上去了女家,女孩出来见了父亲,请父亲转告大爷,她要出嫁了,嫁到临朐乡下,今天就走。
父亲说,那女孩子说得很平静,可是他分明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幽怨。
听了这事,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大爷从青年到中年,一直都在回避婚恋,那实际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惩处!甚至他的一生,仿佛都在这种自我放逐、惩处之中。
几十年来,知道底里的老朋友们谁都没再提过这件事,可是,大爷心底的伤口,应该始终没有愈合过。
大爷谢世后,我几次取出那一匣红丝砚,摩挲把玩,对物思人,忽然想到,红丝石产于临朐啊……当然,以大爷的那种粗豪的性格,他是不会留心什么文玩的产地的,更不会将砚石和当年的恋人联系起来,可是世事有时就是那么稀奇古怪,大爷毕生收受的唯一的礼品,来自他毕生心爱,毕生愧对的女子的负气下嫁之地。
那个差一点成为我们“大妈”的女子,如果还健在,也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她的大半生的遭际,我们是一无所知,大爷曾辗转地打听过么?
我们生活着的此岸,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留下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有彼岸,真希望他们终有一日能够相见,能够谈开,即便是痛心疾首,即便是破口大骂,即便是雷霆万钧,即便是泪如雨下,总比隐忍沉默、心如刀割的好吧?
我在我的书桌上摊开这一匣红丝砚,权做礼器,祭奠我的亲爱的大爷,祝福那位曾经要做我大妈的老人。
2019年春
(刊于2019年11月19日《青岛日报》“随笔”版)
计纬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