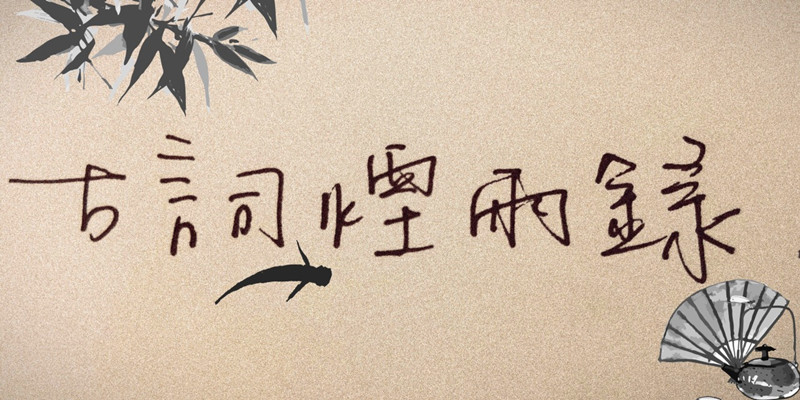三、由《招隱士》引劉安之疑
我們仍先研究一些暗示或質疑劉安與屈原關係的文字,希望由此接近結論。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二淮南小山《招隱士.敘》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作為內外書甚眾。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神仙傳》曰:八公詣門,王執弟子之禮。後八公與安俱仙去。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一)楚辭、王孫、小山,三推論
此可當作一段奇文讀之,主旨何在,值得探究。作者所言,可以導出意想不到的結果。而歷來無人能完全解通其文意。且不必說許多舊籍、學者都認為《招隱士》是淮南小山為劉安招魂之作、甚或是劉安之作。王逸之敘開頭指出《招隱士》的作者是淮南小山之後,乃用大半的篇幅解釋何之謂淮南小山,強調了淮南王劉安因博雅好古,有自淮南八公至小山這些慕德歸仁而竭忠盡智的門客,也有大山。王逸之敘,實際上把文章的重心置於劉安,等於在引導讀者思考劉安與《楚辭》的關聯,乃至和屈原的關係。看來劉安的門客眾人不但分工寫《淮南子》,而且有專門寫辭賦的。據王逸說,辭賦(或者辭賦作者?)分類,而稱為小山、大山,居然恰如《詩經》中有《小雅》《大雅》一樣。這已經甚為奇絕。至今鮮見能解大山小山之義的論者,我們尚未探明其義,也只好隨著王逸這麼叫下去。然而細析文義,利用大山小山比小雅大雅,王逸已悄悄把劉安及其門徒之作推向與五經之一《詩經》比高的地位,這種類比被後世完全認同,而幾乎成為詩騷並稱的最早認定;與《史記.屈原傳》所載劉安《離騷傳》文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相掩映,而互為表裏。劉安之名以此種方式逼近屈原,這是推論一。
下文接著說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亦在文理上不盡通而令人惶惑。「身沉沒」三個字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社會地位下降而湮沒無聞;二是投水淹死;此處似乎兼而用之。前者有時甚至可以被有意誤讀為後者,而贊同屈原投水說。屈原之所謂的因憂國至於沉江而死,乃名德顯聞,這「與隱處山澤」果然「無異」嗎?漢時的隱士,或以隱求仕,自高身價;或有優游卒歲,不問國事,因而名德不彰者;當時如晉代陶淵明那樣的、與當道者不合作而甘心陷於貧困的隱者,有沒有呢?難求矣。但屈原也完全不似陶淵明。「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這話說的很辛苦,也很勉強。王逸以屈原比隱士,無論是真隱還是假隱、大隱還是中隱,都十分彆扭。屈原「身沉沒」而「名德顯聞」了,與那些「隱處山澤」而顯名的隱者大異其趣,哪能說「與隱處山澤無異」?稱屈原如此,和王逸本人明謂屈原「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之言完全矛盾,而不合理。但從怀疑的角度推想,若細品味「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的各種可能含義,這几句話其實可另有一解:《楚辭》作者本人已死,他作為《楚辭》作者的事實和姓名不為人知、湮沒無聞,是為「身沉沒」;依靠「屈原」之名號(非作者本名),而傳美譽令德於天下,是為「名德顯聞」;如此《楚辭》作者就有點好像理想的隱士一樣沉其真身,不過顯其虛名,是為有似於「與隱處山澤無異」。這個解釋至少可以說得通,而勝於把不通的文字置之不理。這樣的人,指誰呢?其實從題目而言,全文也與習稱的隱逸之士無關。從「隱」的最基本含義出發,可以認為,王逸以此題目隱然涉及的「隱士」並非一般意義的隱士,乃是一個其姓其名被從楚辭作者中「隱」去而完全被遮蓋之「士」;這個呼之欲出的隱士,從此篇之序的可疑語氣推論,如果我們懷疑的話,便只能懷疑《離騷》的作者名非屈原,和劉安密切相關,或有別的什麼名。王逸若非有言外之意,是不至於如此落筆的。通讀《招隱士》全文,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是如何彰顯那個傳統認可的屈原之志的;說它隱晦地道出了劉安處境的倒是頗有人在。《招隱士》之題目,分明在招引和呼喚一個本有其名而失其聲之人;引誘讀者在文學和歷史的迷宮中,尋求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光輝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又為中國文化的陰影所遮蔽的人物,所謂「王孫」也。王逸呼喚「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是要讀者尋找和發現其本來面目,給以澄清,予以適切評價,使他回到正常的、不是仙也不是鬼的人的地位。這是推論二。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招隱士.敘》中提到「八公之徒,……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云云。其中大山、小山作何解釋?這本來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偶爾讀到《淮南子.齊俗訓》「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覺得其中「人上之而慄」正好移來作《招隱士》「憭兮栗,虎豹穴嵺穿岤也。補曰︰《淮南子》云︰虎豹襲穴而不敢咆。」之下句「叢薄深林兮攢刺棘也。人上慄」的注解。《淮南子》原文是要說明物各有所喜樂逍遙,各有所驚慌恐怖。作者大呼「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要身在恐怖山中的「王孫兮歸來」。《招隱》中「人上慄」就是《淮南子》中的「人上之而慄」,可見作者對《淮南》著作甚熟諗。連這樣的、也不是什麼典故的片語,都順手用上了,來強調淮南王及群臣生前死後的慘境,作者真不愧屬於淮南小山。淮南小山急急呼之,而望其歸來之人,既是《楚辭》的作者,則似應為淮南大山,此人似為淮南子神仙家的首領。其人自然應是死了,走了,名副其實仙去了。仙字照古寫法為「仚」,是人在山上;人在山上戰慄,就是死了成了仙,還在遭受被屠殺而死的恐怖。小山望「王孫歸來」,歸來陽世是不可能的了;所望者,使他不被斷絕姓名,並且回到正常人死後的狀態,這就是幸運的歸來了。從另一面思考「山」字,乃是「仙」字去掉了人,只剩下沒有人、充滿磨牙吮血野獸的空山。淮南王和群臣,大小仙者,血流成河,被殺的太多了,只剩空山了。故幸存的生者以小山互稱而以大山稱其故主也。至文末呼喚「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意思是,王孫啊,你快回到和平安全的環境中來吧。不在那死亡的山上,做什麼仙人,快到你人的本位上來。所以淮南大、小山之名,其實是大屠殺之後的餘怖中,淮南餘黨敬慰死者並互相諧謔之暗語。綜上所言,讀者其實被迫去解一個更難解的問題,劉安(王孫)之名為何似被屈原取代?換言之,要我們搞懂《楚辭》最深藏意蘊。這是推論三。
(二)仙者、文過、不容,三「又怪」
王逸隱然推崇的淮南小山們和屈原《楚辭》有何特殊關係?而閔傷之情如此深曲?他們「又怪」屈原之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作者似乎發現某個錯誤之外,發現屈原之文不應竟然這樣。這是不是說只有劉安及八公之徒才能「似若仙者」呢?考慮《史記.屈原列傳》的內容基本上不涉神仙,此處的「又怪」似乎在告訴不明真相的讀者:《史記》本傳所記那位頗似儒家忠臣的屈原本是個「似若仙者」的人啊!王逸是不是在曲折地暗示「小山之徒」閔傷的「屈原」就是劉安或劉安的某種代言人呢?分析王逸晦澀的文義,我們是可以這樣猜測的。「八公之徒」對劉安慕德歸仁,與「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兩個句子,其主語「八公」和「小山」都是淮南客,其謂語都涉及劉安。前者說劉安生前,後句則涉及其死後。所以這段話中所謂「屈原」者,似是劉安的一種代稱,他本就是小山之徒領袖人物,大概就是大山吧。劉安乃漢初以來最大的神仙家,他同時又是極有才能的辭賦家、思想家,以彼之才,應更能寫出「金相玉質,百世無匹」的文章來,而「升天乘雲,似若仙者」。當然,在有關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情況下,我們對這個問題很難期望一般意義上的嚴格「史料」證明,但我們總應找到說法,準確的「詩料」證明還是有的。如王逸此處之文一樣的例子,積腋成裘,不是也能透露問題的性質而引導我們怀疑並進一步鑒定《離騷》作者為屈原的說法之含義嗎?我們由此還可推斷,在《楚辭》初始編輯階段,似乎原打算把屈原打扮成一個很嚴肅的儒家忠臣的,後來鑒於神仙家材料之多,而更有利於用以神化屈原、因而神化聖君,屈原之本屬道家的神格才成了公認的不必忌諱的事實。此謂「又怪」之一。
班固《漢書.揚雄傳》(卷八七)以下語也非常值得推敲:「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能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這裡最有意思的是揚雄(班固錄揚雄《法言.自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能容」這句話。觀其「又怪」的口吻,與上文「小山之徒」所言,如出一轍。其意簡單地歸結,就是不但「文過相如,至不能容」是不可能的,「自投江而死」也是不可能的。看樣子,揚雄又覺得奇怪(或不對)的是,屈原文章勝過司馬相如,竟至於不能被容於君王。反過來說,揚雄所怪者,司馬相如文章不如屈原,居然還能取容於君王。讀來讀去,總覺得「屈原」和司馬相如應同時,而所事的君王也應是同一個人。因為如果所事君王非一人,則不同的君王「能容」的雅量不同,那麼文才也不同的二人的「能容度」就不可比較,也沒有什麼理由「又怪」了。其實,中國歷代史家乃至一般人,好像不約而同習慣於先把某人與他的古人或同時代人比較,而後對此人作出相關的判斷;其相反的例子在此是僅見。我們不妨依照上面的句式編造几個句子來說明:「李白文過相如,而不能容於朝」──這個句子比李白於前代文人司馬相如而後作斷語,意思通順。再如:「李白才過吳均,至不能學道」──因為吳均是李白同時代人,此話中的比較也合乎習慣。但是如我們說,「相如文過李白,至不能容」,以前朝人與後代人作比較,再對前代人做判斷;即使是唐以後史家縱論古人,恐無人會如此著筆。一言以蔽之,班固此話隱含的意思,是將他所謂的屈原當作和司馬相如同時代的人。那麼漢人當中有沒有「文過相如」的人呢?我們解《楚辭》到下文,就能說出這個人名來。揚雄還覺得不可理解的是屈原可悲的投江而死。得時不得時、遇不遇都是命,哪裏用得著投水自殺,儘管直到今天還有不少智者強作解人說他們理解和佩服屈原高尚的投水自殺,認為是極端理性的行為,揚雄卻覺得這是不可理喻的,恐也知道這是不存在的。此謂「又怪」之二。
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四)末的「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這段文章涉及甚多大題目。從根本上講,《史記.屈原傳》幾乎完全是憑空捏造,而且硬放在太史公名下污其清名,真是欺人太甚。我們將一步一步涉及《屈原傳》的有關細節,最後全部否定之。以下先僅就其「又怪」之句與上引二句相似的口吻,加以說明。作者(絕非司馬遷)認為,在屈原的時代,憑屈原的才能,任一諸侯國都會接納他,來保國打天下,而屈原堅決偏偏獨獨要為楚國之昏君效忠到底,還預先幾十年就計劃好了、效忠不成就自殺,這真是違反當時人情常理的咄咄怪事。作者意思明白:這是不可能的。此謂「又怪」之三。以上三「又怪」口吻一致,而且在漢人記載中唯有此三個記載,在有關文獻中頗為惹眼,故同論之。
三個「又怪」和三個推論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文例要說明。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敘》云:「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這裡王逸的盛贊屈原,仍然話中有話。說屈原忠貞高潔、不顧個人安危,正大光明、倖直奉公,這都是古老的話頭、「一般態度」也。關鍵一語,「言若丹青」的「丹青」怎麼講?王逸之語,源自揚雄,故錄揚雄之語如下。《法言·吾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翻成現代漢語大致是:「有人問揚雄,屈原明智嗎?(揚雄的)回答是:屈原有如玉一樣瑩潔的至性,乃至於能夠改變丹青。這便如他的明智!這便如他的明智!」其中重複的「如其智」應如何解釋,引起自漢以來很多學者爭論,而至今不休。可見連斷定屈原是否明智都事關重大,不用說斷定屈原這個個體的人是否存在過了。我們就從「丹青」一詞入手試解之。這個多義詞,一指丹砂、青雘兩種製顏料的礦石,因指繪畫(紅、青)顏料;二是紅色青色,可看成丹冊和青史的簡稱,猶言青史或者汗青;三汪榮寶《法言義疏》解作「玉之符彩」。其他各解或代圖像、畫家;或用作動詞指作畫或者美飾;有時可為丹墀青瑣的合稱,都與我們的議題無關。其中第一解見於《法言·君子》:「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不同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如丹青一樣彪炳),是把「丹青」當成可褪色的顏料了。第二解用於王逸話都可解釋通;而用於揚雄的話則第二解遠優於第三解。在這裡特定的上下文中將「爰變丹青」解釋成「乃至於改變了歷史」是比「乃至於改變(表現)了玉的符彩」要合理得多。其實,揚雄說屈原這個人物如玉一樣瑩潔的至性,竟然改變了歷史,這真是他的明智啊!真是明智之極啊!模楞兩可的表達之中,我們特別看最後的「如其智」的重覆,是包含著微言的。大概可解為:竟改變了丹青,真有智慧啊──這明明是諷「屈原」的「杜撰」者真明智,但他們乃至屈原本尊是不用負責任的,他們打扮人、屈原任人打扮而已。對比揚雄其他的屈原評論。尤其前引「又怪屈原文過相如」之語,令我們越發相信揚雄對於屈原的評論,更明顯地帶有「兩重性」。與班彪班固王逸不同,揚雄的兩重性竟然常常表現在言簡意約而生歧義的同一個句子裏,不是「一般態度」顯而「特殊態度」隱、表現在不同的場合。如此,我們乃解釋「言若丹青」為「(屈原這個人物說的)「話」就像丹冊青史一樣(彪炳傳揚);」而「爰變丹青」就可解釋為:原人物之出現本身,乃改變了歷史記載,也就是《楚辭》及有關《楚辭》作者傳記中屈原說或關於屈原說的話,把歷史改變了,而成為歷史。這影射的乃是屈原被嵌入先秦楚史的本事。這樣的話,在漢代,即使知情人也不敢直接說出;能夠如揚雄這樣模棱含糊地說出已極為難得。無論如何,即使古賢者敢說一點真話,今智者也把它抹掉了。多虧解「丹青」為歷史,畢竟也是該詞一不可忽視的選項。
從根本上講,屈原之名或者竟爾是一種社會正義呼聲的縮寫,集在屈原名下的作品自然多是孤臣孽子、忠魂冤鬼之作。屈原這個名字(密切涉及劉安而並不完全等於劉安)就成了這群無名作者的總的代名詞,成了功榮所叢,盡管《楚辭》主要作品並不多屬劉安。(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