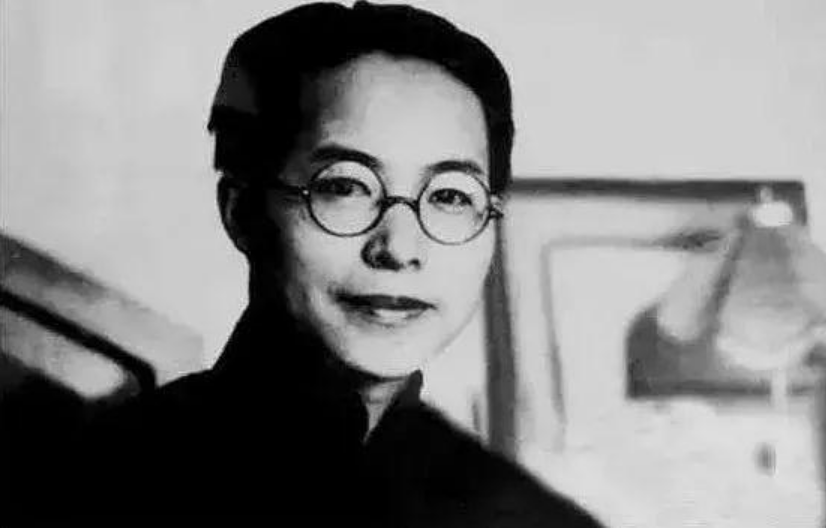四、屈原真身之驚鴻一現
現在,我們希望在以上所知條件下,先研究王逸的《章句》。希望僥幸能獲取更多「情報」。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以卷一至卷七為屈原所作《屈原賦》二十五篇,大致包括《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然後是卷八《九辯》,稱為屈原弟子宋玉「閔惜其師」之作。卷九《招魂》也斷為宋玉為屈原招魂所作。至《章句》第十《大招》則言「疑不能明」為「屈原之所作」抑「或曰景差」。第十一至第十七的作者則分別列為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和他自己等漢代文人。為《楚辭》文字做注,王逸常用「言己」如何如何,來解釋屈原的文字、感情、行為或遭遇;有些負荷重大消息的文字,也便藏在其中。
《章句》之各篇解題、注解之中,常有一些或明或暗、或曲或直、或荒謬不通或勉強回護,然而畢竟透露消息之處。不僅在《章句》中,甚至在他為之作章句注釋的《楚辭》原文中,都保有他對《楚辭》及其作者身世身份的關鍵性意見。確需專門探求討論。
(一)「微霜」引喻的滅門之禍
我們先研究一例。東方朔《七諫·初放》說屈原「言語訥澀兮出口為言,相答曰語。訥者,鈍也。澀者,難也。又無強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
復無強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淺智褊能兮褊,狹也。聞見又寡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從《史記》本傳,可知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此處為何說他「言語訥鈍」「聞見又寡」,而且「淺智褊能」?他作為臣子而若非藩王,需要什麼「強輔」?王逸說他「言淺狹者,是其謙也」很奇怪,為屈原執言可理解,但說屈原這樣表達自謙,何謂也?在此提出問題,希下文得到答案。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識別「複合式屈原」中心作者的令人驚嘆和不得不信服的證據。
以下先專研究一些帶「微霜」的相關句子,由「微霜」比喻嚴刑苛法,或導致嚴刑苛法的讒言,道出關鍵線索。王逸如此做注解,都是事先計劃好了的。他真是有心人哪。《七諫.沉江》「青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華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釼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王的解釋是「微霜」殺百草,就如讒人毀謗屈原自己,造成君令急促,顛倒忠奸,使自己死於非命。又《自悲》篇「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濛濛。言遭佞人群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早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也說到專事造謠誣蔑的奸佞,使得「君政用急」而傷及自己。王褒《九懷·蓄英》「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微霜兮盻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也用秋風和微霜,暗喻深酷的「天政」。
《九章·惜往日》說得更清楚「何芳草之早夭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嚴刑死有時也。」又「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淹沒隨水去也。恐禍殃之有再罪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陳詞未終遂自投也。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以上三例,尤其王逸的注釋,把「微霜」當成「嚴刑死有時」的表現,導致「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寧溘死而流亡」,字面上可解為寧可馬上死掉、放逐而死,王逸解為想投水淹沒,像是在維護「一般態度」,原文很明白,是怕「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就是怕遭滅九族之災。怕連累父母,這話似不是劉安說的,因他父親早亡。這個「屈原」是誰?見下文(是蓼太子)。「不畢辭」句,只是照前文我們提過的一般態度,謂屈原未把話說完就投江了,等於虛晃一槍。但王逸在此對「微霜」和「禍殃之有再」貌似出格的解釋,提供了《屈原傳》不載的消息,點明所謂屈原遭受的滅門之禍。我們讀《史記.屈原傳》,從中只知道屈原是很有才能、又非常忠誠的楚王同姓大臣,即使受到到讒陷,九死不悔,仍然不改其忠,還常望君王重新啟用他;從來想不到楚王還會把他滅族。令人難以置信。再檢查一下,發現王逸竟如此堅持己見,連在較輕鬆而似哲理詩的《卜居》中,也不忘提醒讀者「屈原」和「被刑戮」的關聯。「將游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榮譽立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
(二)劉安父子之臨刑細節
宋玉的《九辯》王逸稱是「閔惜其師」而作;在替自己的老師說話時,悲痛之極,几乎是己飢己溺、將心比心,深切哀慟老師的痛苦,不覺而用了屈原自述的第一人稱口氣。以下幾段宋玉《九辯》王逸注與「微霜」有關的描述和解釋,就不但證實上文推論,而且簡直令人驚悚了。
1.《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廩秋微霜悽愴,寒栗洌也。白露既下百草兮萬物群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又芟刈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台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也。……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之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欿傺而沉藏民無駐足竄巖穴也。」這段文字起於悲秋而言其肅殺,援引天時,從秋日的草木皆凋,導出嚴冬之刑罰刻峻。由此興出自訴式的「懷德君子」之「早遇霜露」和「忠而被害也」。再看下去:
2.「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顛僕,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王,而年老也。攬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行,而勿驅也。聊逍遙以相佯且徐徘徊,以遊戲也。歲忽忽而遒盡兮年歲逝往,若流水也。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之不長也。」這兒屈原自言不逢聖王,已年老,又說年矢如飛,恐命不長了。以下緊接上文說:
3.「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卒遇譖讒,而遽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煢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傷閔己,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惕動,沸若湯也。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及兄弟也。卬明月而太息兮告上昊旻,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在這一段中「屈原」表達的是生不逢時、年紀尚少,「卒遇譖讒」、面臨災難而五內俱焚、無所告訴的生命焦慮。他徒然仰望蒼天而自傷,也為君父、兄弟悲傷。這裡有幾個問題。
其一,王逸注解的「傷己幼少,後三王也」畢竟何意何指?上文方自言年老命促,今何故又自傷幼少?這年老與年幼都是指屈原而言,畢竟說明什麼問題?恐只能解釋為「屈原」者,有多於一人的身份。此處一老一少兩個「屈原」,是不是老者代表劉安,少者則為劉安的兒子呢?「後三王也」的「三王」當然不指前代三王夏禹、商湯和周之文武;那也太遙遠了,而與劉安父子命運都無關。王逸故意用了一個似乎模糊而有歧解的字眼「三王」,既可迷惑不求甚解者,又嚴肅地說出了他的本意。他是以「後三王」來說這個年紀小些的「屈原」因出生後於「三王」而生不逢辰。這「三王」只能暗指「淮南三王」,即淮南王劉安、其弟衡山王劉勃、廬江王劉賜。《漢書·鄒陽傳》「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顏師古注:「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漢枚乘《重諫吳王書》(見《文選》卷三九)「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此處我們且不管枚乘照漢家正統說法稱淮南三子欲報父仇。這裡所謂「屈原」就應是淮南三王的子侄了。而「內念君父及兄弟」,尤其「君父」而與《楚辭》相關者,只能是劉安;則「念君父」者當為「太子遷」,就是上文恐怕「罪及父母與親屬」者。《漢書.伍被傳》(卷四五)有以下記載:(淮南)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顏師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一一八)「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按,「荼」就是淮南王后蓼荼,太子遷就是蓼太子。而班固依《史記》述劉安和門客伍被商討「反計」時,故意加上「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這濃重的一筆。沒有這句話則《楚辭》主要作者便無從考證了。此處使劉安不稱其子為太子遷,看似遵舊俗從其母姓稱之為蓼太子,故意不提起本名。班固如此設辭是有深味的。「遷」者,改也(《說文》謂「僊,長生遷去也」)──已非太子原名;班固既不能也不便用原名(因原名已被禁止直用)而假劉安口稱之為蓼太子。尤其用「不世出」之語,強調這位太子的非凡才能、非每一代人都能出現的奇才;這種才能,大概指年幼時就智力超越的「神童」級別的人。所以他根本沒把漢朝公卿看在眼裏,說他們都是沐猴而冠。王逸說他「傷己幼少,後三王也」,意蘊是,如他早幾十年出生,生在父輩之前,以其出類拔萃之才,就不可限量了(大能當上皇帝)。這當然完全是虛擬語氣。但《史記》和《漢書》的劉安本傳之大部分文字,都把這位太子塗抹得面目全非;班固深心特意寫下的「不世出」三字對太子才能的高度肯定使我們不得不重視。
竊以為,這位太子必已表現了很不一般的才能方使其父如此讚揚他。他是淮南王為首的文人集團的二號人物。從淮南王最後慘遭滅門之禍來看,他似沒有表現出什麼超常的政治智慧。所以說,作為一種應是合乎事實的猜測,其非常之才更表現在文章辭賦上。後文將補證他在創作《離騷》之不可磨滅的功績。無論如何,劉安和蓼太子是《楚辭》主要作者,我們將繼續發現,蓼太子比乃父更重要。
其二,「屈原」可以老可以幼(這是王逸注解的實例告訴我們的),啟發我們認識第一人稱的妙用。王逸可用「第一人稱」式注解加給一般的「屈原」並不屬於一人的作品,包括言語、行為、感情、遭遇或品質,也難免加上與某一個特殊的「屈原」無關的事情,而《史記》本傳尤其《楚辭》因此有了很充足的材料可以選擇。這就增加了屈原「經歷」乃至人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不過我們不能兼收併蓄,全部相信,而應從中找出主要的人物。無論如何,《離騷》作者不是一人,是兩人、三人,乃至一群人;換句話說,「屈原」之名,只是《楚辭》編輯者迫於形勢而生造的、代表一群人的假名、筆名或代名。就上文所引 1、2 兩段而言,前段是蓼太子寫的;後段則是劉安寫的。應補充一點,無論多少個作者對《楚辭》原文有貢獻,除很少的幾個例外,大多數作者名字都被消滅了,被放在「屈原」之下,而有待分辨和鑒定。而劉安父子,尤蓼太子,乃是《楚辭》的主要篇章的作者,或核心作者。見下。
其三,王逸把最重要的消息不放在《屈原賦》二十五篇中,也不放在他經常用「言己」字樣表達屈原所遇所感的漢人《楚辭》篇章中,卻放在宋玉抒「悲秋」之感的《九辯》中。他是假宋玉為之代言代想的屈原言行感思,把劉安父子這二人的冤屈細節,尤其被刑前的悲慘無奈甚至淡定真實地原原本本道來。他真是煞費苦心啊。
為使行文不太枝蔓,我們仍先繼續玩味《九辯》接下去的有關選段,試圖深入察其貌知其心。「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君政嚴急,刑罰峻也。心尚幸其弗濟冀過不成,得免脫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威怒益盛,刑酷烈也。乃知遭命之將至卒遇誅戮,身顛沛也。」這幾句和盤託出了宋玉之師「屈原」所遭受的慘烈苦難,不但是個人被誅戮,且是滿門抄斬的滅門之禍。這是從劉安角度立言的。尤從後文「事綿綿而多私兮政由細微以亂國也。竊悼後之危敗子孫絕嗣,失社稷也」看,所謂「失社稷」,指一個諸侯被滅門,被取消王位而失國。禍起的原因,竟然是細微的小事。罪名是無中生有,蒙罪者卻難以自辯。承上文,可見,這一段與其說是宋玉讓劉安發言,不如說是劉安直接發言的。
再往下看:「願徼幸而有待兮冀蒙貰赦,宥罪法也。泊莽莽與野草同死將與百卉俱徂落也。願自往而徑遊兮不待左右之紹介也。路壅絕而不通讒臣嫉妒,無由達也。
欲循道而平驅兮遵放眾人,所履為也。又未知其所從不識趣舍,何所宜也。」這裡又換了敘述人。此處透露臨刑之前,這個蒙罪的「屈原」希面君自訴,得到寬宥,卻遭到讒臣阻撓。他當時所作所為,是遵從和仿照(遵放)眾人意見按常理把訟案理清;卻不知畢竟何所適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舉足猶豫,心回疑也。自壓桉而學誦弭情定志,吟詩禮也。性愚陋以褊淺兮姿質鄙鈍,寡所知也。信未達乎從容君不照察其真偽也。一本云:然中路而迷惑兮,悲蹭蹬而無歸。性愚陋以褊淺兮,自壓桉而學詩。蘭蓀雜於蕭艾兮,信未達其從容。」他猶豫之下,竟索性強壓愁情而讀書。自謂如我之愚鈍短淺,確不能從容道出全部事實原委(說也無用),而使君王照察真偽。這個人和眼前面臨的屠殺直接相關,而非劉安,當然是那個「年少」者蓼太子。
「然中路而迷惑兮」以下的四句,王逸時已另有一個版本,即上文「一本云」六句,與此四句有異同。這六句意思更清楚些。對此六句,我們可以方便地引用王逸原注,解與上文相同的句子;而模仿王逸「八字注」,解其不同的句子。大致如:「舉足猶豫,心回疑也」;蹭蹬竭蹶,悲無路也。「姿質鄙鈍,寡所知也」;「弭情定志,吟詩禮也」;良莠不齊,所見異也;「君不照察,其真偽也」。意謂猶豫之下,未能定奪;悲傷絕路,難以逢生;生性愚陋,所知甚少;自我壓抑,讀書定性。蘭蓀蕭艾,忠奸混雜;末路陳情,未能釐清(君王就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我們由此看出,在臨刑之前,「蓼太子」還在「遵仿眾人」,大概是為門客們利益考慮,又因門客們有忠有奸,互相齟齬,眾說難平,而沒有做出清楚判斷(這時他說什麼也不對),遭致暴君最後的集體屠戮。其中「性愚陋以褊淺」句,令人想起東方朔說屈原「言語訥澀」、「淺智褊能」、「聞見又寡」等語(見下),王逸說是他自謙。我們因此判斷蓼太子詞辯上大概並非長才(是長才亦無濟於事),他的不世之才,應是文才。在慘禍面前,他面臨門客齟齬,能否分清忠奸且不論,他居然不能決斷而聽由操生殺之權的獄吏決定生死了,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還能有心讀書定性。真是天才加讀書聖人,不可思議的「神仙」風格。在此,連蓼太子及眾門客怎樣全體被殺的過程周折,都寫出來了。《史記》《漢書》之《劉安傳》只說劉安父子自殺在元朔六年(前 123 年),班固《漢書武帝紀》則稱劉安受誅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不知其中是否還有隱秘或有何種隱秘。
以下為省篇幅,只再引幾個不相連續之句。
3「今脩飾而窺鏡兮言與行副,面不慚也。後尚可以竄藏身雖隱匿,名顯彰也。願沉滯而不見兮思欲潛匿,自屏棄也。
尚欲布名乎天下敷名四海,垂號諡也。賴皇天之厚德兮靈神覆祐,無疾病也。還及君之無恙願楚無憂,君康寧也。言己雖升雲遠遊,隨從百神,志猶念君,而不能忘也。」這個「屈原」是誰,王逸竟在「後尚可以竄藏」,這個明顯指罪犯流竄和藏匿的句後用「身雖隱匿,名顯彰也」來讚揚他?他又如何「身雖隱匿,名顯彰也」的?「思欲潛匿,自屏棄也」,假屈原之口表達潛身而自棄,寧可隱身逃名,「敷名四海,垂號諡也」,則是屈原揚名四海、垂譽萬年的歌頌。在此也可理解為宋玉設身處地為「屈原」立言,對屈原將來做出評價,當成屈原發言更好。而作注者王逸能把宋玉原文不曾說甚至未必願意說清楚的事件如此嚴肅、確鑿,毫不含糊地寫出來,王應是原來歷史事件的知情人。從「身雖隱匿,名顯彰也」而言,這幾句的說話人乃劉安也。蓼太子則是幾乎被剝奪名字的犧牲者。
王逸把如此重要的「屈原對話」不放在屈原賦二十五篇的注解中,卻放在《九辯》的注解中,當然是極費安排而大有深意的,加上《離騷》和《七諫》與之呼應,構成楚歌浩唱中的主旋律。「微霜」是它的預奏,「朕皇考曰伯庸」是它的基音和弦,「淺智褊能」則是它臨終的變奏,然後在旋律進行的高潮揭示了「平原」之悠悠無盡的尾音。為了讓細心的讀者完全心領神會,使它不至被種種喧囂的雜音淹沒,王逸在整部《楚辭》中讓它出現了三次。
見下。
(三)與主旋律和鳴的多音部
再看《九章·惜往日》4「秘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赦貰寬也。心純庬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而待臣兮上懷忿恚,欲刑殘也。不清澈其然否內弗省察,其侵冤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專擅威恩,握主權也。虛惑誤又以欺欺罔戲弄,若轉丸也。一云:惑虛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不審窮覈其端原也。遠遷臣而弗思放逐徙我,不肯還也。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偽,自亂惑也。盛氣志而過之呵罵遷怒,妄誅戮也。」這一段中「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屬於障眼法(或一般態度)的運用,是用假話掩護真話,我們且不論。全段敘述一個文士,他心知而不能說出的「秘密事」,即天災地變一樣的巨大事件,應是淮南王文人集團全部受牽連而被集體屠殺的事件。其後,他「素性敦厚,慎語言也」,應是不肯對被加罪者落井下石。暴君就信讒言,對他「欲刑殘也」。繼而先是放逐了他,又對他妄加誅戮。這位賢臣是誰?我們很難確定。其犯事之因顯然與《九辯》中所言被滅族者劉安及其太子不同。此人應是因淮南事受連累而被殺的朝臣。這一段意思應很完整了,尤其從注解看是完成了一件事的敘述。上例至少可對比《漢書·張湯傳》(卷五九)的例子;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之獄,別疏骨肉,藩臣不自安」。漢武就派狄山以博士身份去邊疆守一個哨所,假匈奴之手把他的頭砍掉了。漢武似乎要殺盡任何敢為淮南仗義執言者。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應是編輯者寫的,N 個「屈原」之一的經歷。
又《九章.抽思》云「昔君與我誠言兮始君與己謀政務也。曰黃昏以為期且待日沒閒靜時也。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讒人,更狐疑也。反既有此他志謂己不忠,遂外疏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握持寶玩,以侮余也。覽余以其脩姱陳列好色,以示我也。與余言而不信兮外若親己,內懷詐也。蓋為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願承閒而自察兮思待清宴,自解說也。心震悼而不敢志恐動悸,心中怛也。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懷猶豫,幸擢拔也。心怛傷之憺憺肝膽剖破,血凝滯也。玆歷情以陳辭兮發此憤思,列謀謨也。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琢瑳群佞,見憎惡也。眾果以我為患諂諛比己於劍戟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一云:豈不至今其庸止。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一云: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興復也。」這一段是一邊抒情一邊敘述,大意如下。當年君王和我有言在先,將一直任用我至晚年。但他半途就改變了主意,信用讒邪,說我不忠。撫弄寶玩來侮辱我,還讓我看到他的美人們來侮辱我。對我不講信用,假裝親近,然後橫暴怪我不盡職。本想找個機會向他自我解釋一下,又心中恐懼而不敢。我心中悲傷猶豫,還希望繼續侍奉他而得到提拔,真是摧傷得肝膽俱裂,心如刀割。想把這種苦情向他傾訴,君王卻充耳不聞,裝聾不聽。我不會向君獻媚,那些專以獻媚為能事的讒人們就把我當成眼中釘。當初我和君王論道,耿直明白,文辭尚在,難道今天全都置之腦後了嗎?為什麼忠言真的成了毒藥?但願君王有朝一日,恢復聖聽聖智,而重歸德化。所以這一段所描寫的、這位忠臣的經歷,怎麼看也既不像《史記》所記的「屈原」,更與劉安扯不上關係。尤其「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二句之特殊細節,即「君」向其展示寶玩和女色來侮辱他,令人懷疑其中的「吾「或「余」應是受刑而成宦官的人;受宮刑者失去男人立身之基本,對他炫耀金錢和女色就是嘲笑他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了。這個人之忠誠更有文字為證,越是如此君王和佞臣越是不能容他。雖缺乏更確鑿顯明的證據,我們也懷疑這是編輯者為司馬遷發聲了。在這種語境下,要求「確鑿顯明」,恐是戴盆望天。但由以上的分析,在代表「屈原」的人群中,我們已看到不但明明有劉安、蓼太子,還有一個作者,是為他人發聲或讓某人發聲的,他就是史臣,或叫做《楚辭》編輯者。作者群中,除宋玉外,淮南客、沉江者(見下)都是死難者;能精確分辨出多少作者和被代言者,待深考。
《七諫·自悲》(用屈原為第一人稱)也有類似的「老少二人」的例子。
「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己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言己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己患苦眾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恆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言己乘騰高山,以為痺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以上《自悲》中,屈原先說到自己,年且老也,命不長也,將消滅也。但接下去(一句也不隔),馬上「自哀惜死年尚少也。」當中竟毫無過度。而且都是假設屈原在「言己」或「自哀」。這種對前述《九辯》注釋案例之故意的模仿重複,究竟能使「屈原」多代表幾個人?這少年去過恆山,又去過會稽。從其在中國南北東西遄行的蹤跡,我們只能大概猜測他的身份。
去恆山者可能是漢庭從長安逐出的朝臣,去會稽者大概曾是吳王之臣,枚乘、鄒陽之流亞吧?這種「異而又異」所顯示的是,《楚辭》作者群雖以淮南王父子為主,還有不同的老少對、或曰父子罪人的。至少,它可以暗示:劉安父子為《楚辭》主要作者之確鑿無疑。
最後《謬諫》曰「悲太山之為隍兮,孰江河之可涸言太山將頹為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言己願承君閒暇之時,竭效忠言,恐犯上忌,觸眾人,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言己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年滔滔而自遠兮,壽冉冉而愈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悇憛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言己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其中的屈原又變老了,他悲傷泰山變成池水,王逸解為君之過惡已成,不能救了(這是《章句》全文中,對君王最大膽嚴厲的揭露和譴責)。自己想進言,又怕犯忌諱而遭刑誅,而完全絕望。王逸雖處處以「言己」解之,所解之「己」往往不同,這個「己」不但異於那個《史記》之「屈原」,而且也異於這個「屈原」所代之劉安。
我們在後文會看到「屈原」被貶多年多地乃至自沉的多種描寫,形成「忠而被屈」的種種,與劉安父子相映成趣,但不能合併。是出於不同的編輯角度。
《楚辭》很多篇章,行文真所謂天馬行空,雲霧開闔動蕩之際,往往如神龍現尾,而不見其首,或者到了高潮,又回波蕩漾。與此同時,有些段落又似重複,而且是故意的重複。往往使人在艷羡驚嘆之餘,產生審美疲勞,而又恰恰錯過了重要信息。《楚辭》既包含多位作者的筆墨,這些筆墨當然是由編輯者相當精妙地拼凑連綴在一起的。誰是編輯?大概劉向、王逸都是,甚至可能要有「皇家檢察官」身份的人審定。其事前後歷時幾乎兩百年。編輯們用了什麼方法,能既大體保留每一個原作者的面目,而若斷若連的行文中,又基本上不失整體性呢?可以看到《楚辭》中每個相關段落,常有「發言人」在,透露有關情節,往往可供讀者仔細辨認其作者身份。回思王逸微露訊息的方式,有時甚至似乎是在匪夷所思的注解中,尤其依靠第一人稱的普遍而靈活的運用中,點明個中微妙的。這種人稱之活用,有時自然順勢,有時突變回第三人稱。在涉及到屈原的年齡、貶謫的地點、時間、原因、後果時也變化多端,髣髴綽約,似曾相識,又不全然相同,許多段落意義差同,都含有玄機。這些地方很可能是分出不同作者的關節點。到底有多少篇章是這樣合成的,很難斷言。更深的玄機大概和王逸把《楚辭》解釋為「神篇靈章」有關。所謂「河圖洛書讖緯言也」是不是說《楚辭》的編輯者把有關段落按照「河圖」和「洛書」的啟示做出一種排列呢?在這裡,我們也體會到王逸所謂「其失巧而寡信」之妙語,一時也未能琢磨透徹,只好止步了。我們可以再從另一種角度舉出例子。
錢鍾書《管錐編·楚詞洪興祖補注·二《離騷》·(六)「前後失照」》有以下論述:「『眾女嫉余之蛾眉兮』引《補注》『眾女竟為謠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思美人之遲暮』句,《補注》謂『美人』或『喻君』,或『喻善人』,或『自喻』。謠諑謂余以善淫《注》『眾女』謂眾臣;女、陰也,專擅之義,……故以喻臣。『蛾眉』、『美好之人』;……『眾女嫉余之蛾眉兮』,又即下文之『好蔽美而嫉妒』也。上文『思美人之遲暮』,王逸注:『美人謂懷王也』;下文『思九洲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以求女』;不論其指臣皇皇欲得君,或臣汲汲欲求賢,而詞氣則君子之求淑女,乃男也。不然,則人疴矣。後之稱『自』與前之稱『余』,蓋一人耳;扑朔迷离,自違失照。」簡單歸結之,《離騷》之文中,或以女子自喻,或以求女者男子自喻(其實還有不可解者);所以謂之「前後失照」。錢先生又舉例說「《楚辭》中岨峿不安,時復類斯。如本篇云:『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鳳凰翼其承旌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飛龍為駕,鳳凰承旌,有若《九歌·大司命》所謂『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乃竟能飛度流沙赤水而有待於津梁耶?有翼能飛之龍詎不如無翼之蛟龍耶?」也是前後文義有矛盾的地方。
竊以為,錢先生所舉的類似例子,各篇尚多,恐都是編輯者把本屬於不同作者的段落或同一作者不同時的段落集於一文造成的。這是一個細部研究的問題。本文只好說到為止。
又《九辯》「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懼命奄忽,不踰年也。一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為一章。」「一本自」三字以下應屬於王逸之言。而後文隔十八句又有「蹇淹留而躊躇久處無成,卒放棄也。(洪興祖)《補》曰:舊本自『霜露慘凄而交下兮』至此為一章。」可見分章分段是原文相當講究的問題,可惜《章句》版本流傳兩千年,多次印刷,原來分段被弄得模糊不清了,非常需要仔細恢復。
在王逸《章句》發表之前有劉向、馬融、班彪、班固、梁竦、揚雄等或對屈原及《楚辭》發表過意見、或參加過編輯,甚至有專著;但他們多數文字被淘汰了,恐主要是官方禁令造成的淘汰。個別能流傳的有關批評,只剩二班的一些評論;揚雄等話中有話的文章,三就是王逸的《章句》了。應該說王逸終能對《楚辭》真相貢獻最大。還應說明的是,漢人作品如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似是《楚辭章句》中以「屈原」第一人稱寫的一種特殊「講校」參考資料。鑒於這種性質,上提各篇之作者也有點可疑了。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王逸對整部《楚辭》的章句解釋乃至《九思》的著作權,但《九思》本身肯定也曾經受王朝政審之監視和過濾。我們也只能根據並相信這些材料,來研究《楚辭》、屈原和劉安了。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