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求為史官,只得縣尉
實際上,庭筠自大中初,也就是開成後期和會昌之末牛李黨爭連續翻盤而政治形勢完全改變之後,便試圖從兩方面重入仕途。一是沿著當年等第罷舉的餘緒,他不時不得不再登考場,思以自己本色當行的文字詩賦之功有所建樹。二是繼續走當年東宮舊路。既然曾為莊恪太子東宮屬官,他努力干求臺閣重臣,想直接求官,尤其是求做史官。大中初年的《上令狐相公啟》和大中後期《上杜舍人啟》都是適例。但他的政治舊案因深涉宮廷乃至宦官內幕,像「沉疴痼疾」一樣難求良醫。《上令狐相公啟》(《全集》之外,參《文苑英華》卷六六二及《全唐文》七八七),是一篇頗為典雅而晦澀的駢儷文,其獨特的辭藻、詭譎的典故,乃至漫漶處的鑑別,若存疑或解之不到位,則無法考證。為使結果有說服力一點,先依原文順序註釋如下。
(一)多年所學,人才廢棄
某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憂國士,或義重門人。咸託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茵微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齊相。豈繫效珍之飾,蓋牽求舊之情。某邴第持囊,嬰車執轡。旁徵義故,最歷星霜。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
大意:有如舊詩的「起興部分」,借孔子重視左丘明作傳、庾亮支持王隱修史的史典振起,企望對方以優遇國士之情厚待自己,以器重門人之義助成自己,幫助自己實現修史之志。接下來,用典喻意:又聽說連被拋棄的舊席這樣細末的東西,都使晉文公悲傷;連「懷刷」這樣微小的物事都能用來干求齊相(靖國君),是因令狐念舊不棄微渺,自己才敢憑小才小用,常來干謁。而自己的干求,不僅是要有所獻納,也是因為舊情舊義。下文陳述自己多年靠父祖餘廕,混跡豪門為侍從、屬吏。也曾為令狐楚門人而聞其教(嘗與李商隱同學)。只是多年積學,未得所用,為末座下僚而已。
解釋:丘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裴駰集解序》引司馬貞《索隱》云「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曰《左氏傳》。」宣尼,指孔子。《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追封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王隱,據《晉書》本傳,「太興初,……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新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憂」,似當從《文苑英華》作「優」(厚待意),與「重」相對。所謂「門人」及「國士」,指王隱、左丘明,也兼自指。舊說或謂左丘明為孔子門人,溫《上蔣侍郎啟》二首之二也有「撰刺門人」語。所謂「門人」者,清惠棟《九經古義》卷十五「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溫師李程與令狐綯為僚友,溫又曾在令狐楚門下執弟子禮(見下)故可稱弟子,又可稱門人。棄茵,劉向《說苑·復恩》「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哭之,因使文公改其行。軫,此處解作「使悲傷」。懷刷小姿,《韓非子·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夕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以及「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懷刷」,未詳指何物事或何行為,然稱「小資」,便是微小可取資之物事。繫,繫心。牽,牽念,與「繫」互用;求舊之情,由此語可斷溫與令狐有舊。
邴第,指邴吉宅第,《漢書》本傳(卷七四):馭吏嗜酒,嘗醉嘔其車;邴曰「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溫《中書令裴公挽歌詞二首》「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即用其事。持囊,又作「持橐」;語本《漢書·趙充國傳》(卷六九)「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太平御覽》所引作「持囊」。按舊時帝王、大臣從吏手持書袋,頭上插筆,以備顧問,即所謂「持橐簪筆」也。嬰,由「執轡」,謂為之駕車,似用《史記·管晏列傳》(卷六二)御者被晏嬰薦事。義故:以恩義相結的故舊;此父祖餘蔭也。「三千子」句,《史記·孔子世家》(卷四七)「孔子……弟子蓋三千焉。」預聞詩禮,兼用《論語·季氏》典:此句向令狐相公表示,在對方如孔鯉一樣接受父訓時,自己也執弟子禮;把令狐相公之父喻為孔子般廣收弟子的大儒,而啟主令狐相公,必為令狐楚之子令狐綯也。
十七年之鉛槧,兼用二事,一是《西京雜記》卷三「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二是《藝文類聚》卷八五載揚雄《答劉歆書》云「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鏑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據此,「十七」或當為「廿七」之誤。尚委泥沙,謂多年遊學所得,尚被委棄而無所聞用也。鉛,鉛粉筆;槧,木牘;皆古人紀錄文字的工具。溫《上宰相啟》二首之二(約寫於咸通初)「三千子之聲塵,曾參講席;十七年之鉛槧,夙預元圖」也用了同樣的一組典故,表達了與啟主的「門人」關係和交往的連續性。其後句把「尚委泥沙」改成「夙預元圖」(即玄圖)則顯示自己多年遊宦遊學所得,由無所用到參與對方的一項(著作)計畫。可見《上宰相啟》二首,啟主也應是令狐綯(綯大中時為相十年,故以宰相稱之而免提其姓也),與本啟同,而本啟之求懇應是有一定結果的。「蠻國參軍」,出《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荊州從事」云云,出《世說新語·文學》「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按郝隆就是那位曬腹中書的文人,習鑿齒則是名副其實的史家,著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等。「蠻國」、「荊州」云云亦見《上紇干相公啟》「間關千里,僅為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亦自謂為屬吏下僚。這組典故出現於不同時期之作,其意重在表明自己多年一直處於下位,而非實指身在荊蠻(《上紇干》是開成二年所作,本文則作於大中初,前後差十年有餘,不會都在荊蠻);同樣,在投遞紇干啟或本啟中用這組典故,雖因郝隆和習鑿齒的幕主都是桓溫而暗涉桓溫,卻毫無以啟主為桓溫的意味,蓋溫此前為下僚甚久,鮮與令狐有瓜葛也。
自頃藩床撫鏡,校府招弓。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藐是流離,自然飄蕩。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鄰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豈知蕞爾之姿,獨隔休明之運。
大意:這段文字敘述自己最近十年的悲苦經歷。自從侍從莊恪、等第罷舉以來,十個年頭已過。自己的女兒已經十歲,未出門而留在外婆家;兒子也好像嵇家的兒子,已八歲,全靠故人的保護了。考慮溫屢自比嵇紹,而將求懇對方喻為山濤,「戴經」句,同時比喻自己久蟄當起,希求故人憐恤自己,說自己已如《禮記》所言「十年不出」而「留於外族」的女子一樣(應該嫁人,亦喻出仕了);而「嵇氏」句,也可解自己只能如幼年而孤的嵇紹,全靠故人提携支持。二句的兩種解釋是作者有意設計的(這也是「複筆」的例子)。既抒家庭流離之苦,亦抒仕途沉淪之悲。所以後文補上一句對於生涯無根的哀嘆:自己已是如此不堪流離失所,飄蕩不已。然後說:我傷心的鳴喚雖非那千里獨鶴,卻幾乎接近了商陵;我的沉痛的呼嘯很像那斷腸的猿母,況鄰接了巴峽。我究竟還有多少時間等待那不可知的天道啊?誰料我這微渺的人啊,偏偏和美好公平的命運無緣。
解釋:「自頃」以下,「藩床撫鏡」和「校府招弓」表示溫庭筠此前的兩個重要經歷,即侍從莊恪太子和「京兆府招攬人才」(等第),見前。戴經,此處指《小戴禮》,即今傳《禮記》。女子十年,語本《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外族,外家之族,謂妻族。「嵇氏」句,語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女年十三,男年八歲」(見前引)。藐是流离,用庾信《哀江南賦序》成句「藐是流离,至於暮齒。」藐,弱小或不值稱,是,此,指上文的「十年」及「八歲「也;藐是流離,不足提如此顛沛流離;所以下句解為,自來本是這樣漂泊無依。
「叫非」句,《樂府詩集》(卷五八)《別鶴操》解題曰: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後人因為樂章焉。」又《文選》卷十八嵇康《琴賦》「千里別鶴」句下李善注引《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嘆別鶴以舒其慎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以下亦引崔豹《古今注》,文字稍異,其末為牧子「愴然歌曰:將乘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能食」云)。商陵,是漢之侯國;據《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卷十九)《索隱》注「《漢表》:在臨淮;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又《漢書》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年表第五》亦云「商陵侯趙周」。臨淮,因其地跨淮水而名,治所在今江蘇泗洪縣南。
「嘯類」句,「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又《世說新語·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巴峽,此處其實概稱巴東三峽。以上二句自言其叫其嘯之褫魂奪魄的悲痛。其上句自謂鳴聲雖非千里別鶴,其憤懣悲愴卻幾乎逼近《別鶴操》中的傷心欲絕的商陵(牧子)。下句自稱嘯聲非常類似悽惻斷腸的哀猿,更何況簡直是鄰近了巴峽。二句中「近商陵」之「近」和「鄰巴峽」之「鄰」都是為了強化其叫其嘯痛徹心肺的程度,簡直可比商陵別鶴和巴峽斷猿,由此來形容自己的痛徹心扉的悲苦,而不含作者身臨巴峽或商陵的意義。或以「況臨巴峽」句推論溫當時所居地鄰近巴峽,誤;如照此推理,當時所居地應也「近商陵」(如上,在臨淮)了,二者矛盾。依此推溫其時住近巴峽,乃及其仕履,則謬以千里也。
(二)「野氏」考證,文饒是指下文第三段為「今者野氏辭任,宣武求才。倘令孫盛緹油,無慚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期。微迴謦欬之榮,便在陶鈞之列。不任靦冒彷徨之至。」
大意:現在前朝李太尉已經退位了,史館正在物色人才。如果你能讓孫盛一樣的我發揮他的文才史筆,不枉他平素喜歡著述的志向愛好;我就能像蔡邕被用編寫漢史一樣,終於得遇明時了。只要你稍為我說幾句好話來誇獎我,我就能受到你的大德栽培。我真是無限說不盡的慚愧冒昧不知所云啊。
這是全文主旨所在。這裡問題較複雜,先給出基本說明,再來專論「野氏」和「宣武」。
解釋:孫盛,《晉書》(卷八二)有傳,博學善言名理。曾任桓溫參軍,與俱伐蜀。盛與溫箋,而辭旨放蕩。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等,詞直而理正,敢忤桓溫,稱良史。緹油,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緹油:音緹,弟奚反。義,緹:鄭注《周禮》云,綠色也;又淺紅色也;《說文》:帛赤黃色也。下油者,絹油也;古人用以書記事」。則緹油者,猶言彩筆、文才也;此處用作動詞,謂發揮文采也(此義又見《一切經音義》CBETA電子版版本記錄:完成日期:2001∕04∕29。發行單位: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ccbs.ntu.edu.tw資料底本:《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54,No.2128《新譯仁王經序》)。《舊唐書·哀帝紀》(卷二四)《禪位梁王詔)「神功至德,絕後光前,緹油罕紀其鴻勛,謳誦顯歸於至化。」其中「緹油」即用「彩筆」義。又,緹油,車飾,古代車軾前屏泥的紅色油布、經常標識身份或恩遇,如《漢書循吏傳》(卷八九)載黃霸得此殊榮;此處不宜取此解。素尚,謂平素好著述的志向。蔡邕(132~192),東漢文史家。《後漢書·蔡邕傳》(卷六十下)載,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紀》,後因事董卓,王允欲殺之,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馬日磾稱蔡邕忠孝素著,曠世逸才,當成後史,為一代大典;然終死獄中;當時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獲偶貞期:謂得遇明時也;獲,得也;偶,假借為遇、遇合也;貞期,政治清明的時代。謦欬,本指咳嗽,借指在高位者之美言。陶鈞:製做陶器所用的轉輪;引申為治國者起用人才。
「野氏辭任」,指某人卸職。不把「野氏」所指考清,本文寫作時間則無以探明。「野氏」其人當指晚唐名相李德裕,字文饒。兩《唐書》有傳。原因如下。
第一,所謂野氏,察遍舊籍,唯「大野氏」與之粗合,而為「大野氏」之省稱。大野氏者,唐高祖李淵之祖李虎西魏時被賜封之胡姓也。據兩《唐書高祖本紀》(參《唐會要》卷一「帝號」、《冊府元龜》卷一《帝王部帝系門》)「李淵,七世祖暠。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儀鳳中,追尊宣皇帝),戍於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賜。天賜生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周閔帝封唐國公,謚曰襄。襄公生昺,襲封唐公,謚曰仁 (武德初,追尊元皇帝)。仁公生高祖於長安,襲封唐公。隋文帝復高祖姓李氏。」稱卸職的某人為野氏,說明其人為李姓,與李唐王室同根而為李唐先祖李虎之後,此人當然不是皇帝,必一度握重權。
第二,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論》上篇(三聯書店2009年北京第二版)確鑿證明李唐先祖為大野氏族,見於以下的論斷:「今河北省隆平縣(按即唐趙州昭慶縣)尚存唐《光業寺碑》(《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茲取黃彭年等修《畿輔通志》壹柒肆《古蹟略》所載碑文相參校,而節錄其最有關之數語於下:(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簡公謹追上尊號,謐宣皇帝(即上引李熙)……。案:《光業寺碑頌詞》復有『維王桑梓』之語,則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絕無疑義,而唐皇室自稱其祖留居武川之說可不攻自破矣。」檢《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趙州昭慶縣」:「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在縣南二十五里。」確與陳寅恪所引碑文相證,可據以論定李重耳以下各代李熙、李天賜、李虎(即大野氏)、李昺、李淵都是趙州昭慶人。
第三,《新唐書李栖筠傳》(卷一二七)「世為趙人,……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新唐書李華傳》「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李栖筠乃李德裕祖父,可見德裕乃趙州贊皇人。李德裕進封贊皇伯、父吉甫封贊皇侯。
第四,《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洛陽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十四冊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夫人趙郡贊皇人……祖贈太師贊皇文獻公諱栖筠」,末署「堂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德裕撰」。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贊皇縣,東北至(趙)州七十里;」「昭慶縣,東北至州九十里。」則贊皇、昭慶二縣近鄰,幾乎可以看成一地。換言之,李德裕確應是大野氏、即李虎後代之一支。只是由於當時「以關中為本位」的成見或者當時別的忌諱,李本人不便明言自己與皇家同根而已。但溫把實話講了出來,而且對方令狐綯自完全知之。這就為陳寅恪之說提供了旁證。竊以為,李唐皇室祖籍趙郡(而不是隴西),正是唐代趙郡多出宰相(尤贊皇、李氏顯宦甚多。宰相多達十七人,遠過隴西李氏)的根本原因。無論如何,以「大野氏」稱李虎後代的李姓自認為李唐之先,雖未得唐王室承認,在唐代也是半公開的事實。
第五,這位「野氏」李姓人物,能在給令狐綯的啟文中被提到,是因他與令狐綯之人生有明顯的交集,可見之於他「辭任」造成形勢的變化。他在前朝會昌時曾舉足輕重,在宣宗即位後無罪被貶;當時令狐綯卻快速得寵擢升。二人升黜形成強烈的對比。溫庭筠大中初向令狐綯投啟時所能涉及的這位「野氏」人物、不但與當時形勢相關而能對溫庭筠投啟事有所影響者,可稱唯一可能有關者,只能是李德裕。
(三)「宣武」舛誤,「史官」原字以下再校對並解釋「宣武求才」。「宣武」看不同場合又是可指桓宣武,即桓溫,東晉權臣。《世說新語·言語第二》「桓公北征經金城」條下劉孝標注引《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薨謚宣武侯。」《晉書桓玄傳》「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資治通鑒》卷一百三云「寧康元年(373)南郡宣武公桓溫薨。」桓溫一生,位極人臣,雖有事功,而後來跡近叛逆。後世文史縱有比某人幕主為桓溫之例,而鮮有或未見直接比其幕主為宣武侯宣武公乃至宣武王者。「宣武」二字在此處的出現,表現了多方面的不通,都與原文格格不入,而必須予以校正。
第一,「宣武「之最明顯的不妥,是聲調不諧。「今者野氏辭任(仄仄平仄),宣武求才(平仄平平)」十字中「今者」二字,在全篇啟文駢四驪六的對偶句式中,屬於不受平仄對仗限制的「發句語」(全文中另有某、某聞、抑又聞、或、自頃等發句語,均以斜體字標出);除這種「發句語」(和結句)外,其他各句或相應部分皆嚴格講究平仄(亦一三五平仄不論)和對仗。反復詠頌本文,發現「野氏辭任,宣武求才」中的「野氏」和「宣武」都是仄聲音節而不構成平仄對仗,成為此文中唯一音律不諧之處。為使平仄諧,可改「野氏」為平聲音節,也可改「宣武」為平聲音節。但是從意義上考慮,由兩個仄聲音節組成的「野氏辭任」,似無可挑剔和改動,則下句應是兩個平聲音節,故失誤在「宣武」也。這種基本音調的不諧,不可能是精通音律的溫不小心造成。據全文意脈猜測,應以平聲音節(平平或仄平)取代「宣武」而與「野氏」構成對仗,竊以為構成這平聲音節的詞應是「史家」(或史官)。
第二,這個取代,除因此使平仄皆合外,「野氏」與「史家」之相對仗,工整而雅穩;符合溫的造語習慣(《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為「野」可與「史」偶對之源)。妙在「史官求才」,可理解成有司「求史官才」的倒文。
第三,就意義而言,「野氏」和「史家」對仗中,上句指前執政李德裕已去位;下句指今朝有求史官之才的需要,這是當時的總形勢。以「辭任」言李德裕的被貶,不失敦厚;以史家求才表達新朝招攬史官,應合乎當時新君(唐宣宗)初立的歷史條件。唐代新君即位後不久,往往著手前朝歷史的修撰。裴庭裕《東觀奏記》序中就提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唐昭宗)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漸遠,慮聖績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在殘唐之時,猶且如此;說明新朝新君每議修史,是自然的;而當此之時,整頓史館、搜羅補充史官人才應是常事,換言之,「史官求才」成為自然的必要。
第四,晚唐文人自比桓溫門客,似不乏例證。因桓溫畢竟為一時之雄而曾延攬人才。不過,從全文前後各句的語境而言,前文固然用了郝隆(含抱怨)、習鑿齒(含揄揚)的典故,而似涉桓溫,但主要是說自己以前多年沉淪下僚的經歷,與啟主令狐無關。後文用了孫盛(含指摘)的典故,自比詞直而理正,敢忤桓溫,人稱良史,更無比令狐為桓溫而暗貶之的意味。在這樣的前後文中,當中冒出的、起連貫前後作用的一句「宣武求才」,如果真是以桓溫稱「宣武」而代指令狐綯的話,就等於把前文訴說昔日經歷的「蠻國」二句典故所暗涉的桓溫都當成了令狐綯,也簡直把後文對「桓溫」暗含的指摘和埋怨都放到令狐綯頭上去了。這讓令狐綯情何以堪?另外,李德裕方退位不久,則公開恭維初得恩寵而資歷尚淺、尚無建樹的令狐綯為勢壓朝廷,門下集結頗多文人的桓宣武,與上下文意相矛盾外,有恭維過火而產生貶義之嫌,遠非溫庭筠所能為。
第五,因為史官求才,所以求為史官。下文緊接就扣住主題,一言破的,自己願如孫盛那樣得以發揚文才史識而為良史;也讓蔡邕一樣的自己編錄國史,遇上好時機,不至賫志以沒。這又與本文的「引子」,即開頭就說的投獻目的「丘明作傳,先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即要求令狐推薦自己編史完全相合,也與「廿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自己多年的學識積累未得其用)緊密相扣,更與前引習鑿齒典故暗相呼應,使全文一氣貫注,主旨鮮明。
第六,重讀「倘令孫盛緹油,無慚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期。微迴謦欬之榮,便在陶鈞之列」數語,可發現其中「微迴」句是再次懇求對方(向有司)為自己稍盡美言、幫助自己成為史官。「倘令」是「如果使」之意,其前省略的主語就是令狐相公本人(應稱為「君」或「公」),這個主語若就是前文的「宣武」,令狐哪裏用得著自己對自己「微迴謦欬」啊?實際上溫要令狐向有司稍盡美言,應是要中書省有關「監修國史」的上峰向所轄史館,為自己求任史館修撰、或直館之類的職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史官」。蓋令狐綯當時仕途正看好,雖非宰相,說話管用也。
第七,且不說令狐綯大中初根本未曾為節度使;即使他在大中十三年去相位時為河中節度使(《新表》),「咸通二年改宣武節度使,三年冬,徙淮南」(《舊傳》卷五八),乃至「為四鎮節度使」(《新傳》卷一六六),由於他大中十年為相的經歷,人們包括溫仍習慣稱之為相公(《上宰相啟》第二首可以為例),而不會在其任職河中時稱之為河中、任職宣武時稱之為宣武。其實,在本文的語境下,「宣武」不但不能指令狐綯,指任何一個另外的前任官員也不行了,因為這個詞造成了前後文心的破綻,而且直接以幾近叛逆的強臣諡號稱人,人所不能接受也。第八,退一萬步說,「宣武求才」是指令狐鎮宣武時招求人才,幕府隨員的任免,都是節度使說了算。溫在襄陽依附徐商,徐自己決定則可,不用向任何人求「微迴謦欬」。
所以,「宣武」二字從平仄上、對仗上,從前後文相接的文理上,都是不通的。這種不通很可能是前代不通文人把一度漫漶的「史官」位置上的原字補上「宣武」而造成。我們不得不把它改回「史官」。
(四)求舊令狐,難申其志
首先,即使在整個唐朝的範圍而論,所謂「令狐相公」者,當晚唐之時,無非令狐楚(765~836)、令狐綯(795~872)父子二人之一也。單憑本文「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這句話,在令狐相公當年如孔鯉聞詩聞禮那樣接受父訓時,溫既也曾「預聞詩禮」,只能是在令狐綯父令狐楚門下為客,可見啟主相公應是令狐綯。令狐楚才思俊麗,名重當時,年輩學問皆堪為溫師。《新唐書·令狐楚傳》(卷一六六)云楚「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而《新唐書·文藝傳》云:「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舊唐書·李商隱傳》(卷一九○下)言「商隱幼能為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之文干之。」溫李並稱,年輩亦復相仿,相友相知,嘗共師令狐楚,應是是合理推測。其次,我們解決了「野氏」指何人和「宣武」為什麼要校改為「史官」這兩個問題,也就揭示了本文之作時和目的。由「野氏辭任」語,知李德裕已退位,而未卒(卒在大中三年即大中三年十二月),上此啟之時應在大中三年十二月之前。也就是如《舊唐書·令狐綯傳》(卷一七二)所記載的「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尋拜御史中丞」——這個時段內。
溫在大中初投啟令狐綯,要求任史職。這不是沿著開成四年「等第罷舉」之路求第,而是沿著開成二三年「侍從太子」的仕履求官。會昌中的形勢封斷了溫求第求官之路,大中初年唐宣宗一反會昌之政,使他看到微茫的希望,又與令狐有舊,所以來求官。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求第求官之路對他仍都充滿荊棘,雖然他終於在大中十三年「貶尉隨縣」後委屈地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以下對比一下李德裕和令狐綯彼時處境,正可發現溫為什麼前來求懇令狐綯。
一朝天子一朝臣,唐宣宗即位之初,就擯棄了李德裕,使牛李黨爭最後一次翻盤,很顯示了這位新君的權威和御人之術。兩《唐書》本傳(《舊》卷一七四,《新》卷一八○)記載,宣宗惡李德裕,聽政次日即罷其相位。《通鑒》卷二四八「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會昌六年三月),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會昌六年)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其後,根據《舊唐書·宣宗紀》(卷二十下):會昌六年六月為東都留守;大中元年正月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大中元年七月,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大中二年九月,可崖州司戶參軍;大中三年十二月病死。與李德裕此時的遭際構成鮮明對比的是,令狐綯短時間內得宣宗之殊寵,只是因為宣宗對綯父令狐楚有好印象。《舊傳》(卷一七二)曰:「大中二年(848),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傳》(卷一六六)曰:『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令狐為宰相直至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出為河中節度使,前後達十年。會昌中建立大功、為宣宗建好統治基礎的股肱之臣李德裕並無過錯而一落千丈、直到貶死之境;有點父蔭而尚毫無建樹的令狐綯則扶搖直上,炙手可熱。這就是「野氏辭任,宣武求才」所含蓄的當時形勢。考慮其意蘊,所謂「野氏」李德裕尚在(病逝於大中三年十二月,可換算為公元850年一月),故謹言「辭任」。如此,則令狐綯尚未入相。則此啟約作於大中二三年間。啟題中頭銜應是「學士」或「舍人」,因令狐綯久在相位,被後來傳人妄改耳。
投啟結果是沒達到目的,恐不是令狐不願、而是礙於政治原因不能推薦他。
劉學鍇先生《溫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認為溫是在為「荊州從事」之時(即在荊南節度使蕭鄴幕為從事的大約咸通二年冬?),向方由河中調任宣武軍節度使的令狐綯投遞此啟的。這個推理是由一系列的錯誤判斷構成或助成。略舉如下:
其一,雖知本啟「蠻國參軍」、「荊州從事」都是用典,但是卻謂「荊州從事」係「實指在荊州為從事」。據此結論再向後推理,則更謬矣。其二,「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鄰巴峽「之句必須正確理解,才能從中有所取證。如前注釋,用「臨巴峽」為證錯誤地推論溫當時居地在江陵,導致了結論錯。其三,在註釋「今者野氏辭任,宣武求才」時,一方面謂「野氏,未詳」;卻又解釋「野氏」句「謂前任宣武節度使畢諴辭任」,至於為什麼竟把這個「不詳」的「野氏」加於畢諴,就未置一詞。又解「宣武求才」為「以桓溫求才喻令狐綯汴幕新開,廣招人才」,便是為不合理硬做解釋,也就難通了。其四,對於啟中語詞典故,尚有一些未注出。如懷刷、撫鏡、招弓、緹油、獲偶等。這就有害於對原文的理解。
(五)「暫陪諸吏」,不得其職
一直到大中九年「攪擾場屋」案發之後,大中十三年貶尉之前,溫還在求為史官。這顯示為史官確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溫在《上蔣侍郎啟》之一中也提到自己「謬嗣盤盂」,自指還算能繼盤盂之才,即申誡帝王的良史之才。盤盂,本圓盤與方盂,古代盛物器皿,其上常刻銘記功或者銘誡;《漢書·田蚡傳》(卷五二)「(蚡)學盤盂諸書」,顏師古注引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也。」《舊唐書·溫大雅傳)「諸溫儒雅清顯,……皆抱廊廟之器,俱為社稷之臣。」《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錄》。《上杜舍人啟》是溫求為史官的又一例證。茲擇其主要相關語句說之。
某弱齡有志,中歲多虞。模孝綽之辭,方成牋奏;竊仲任之論,始解言談。猶恨日用殊多,天機素少。揆牛涔於巨浸,持蟻垤於維嵩。曾是自強,雅非知量。李郢秀奉揚仁旨,竊味昌言。豈知沈約扇中,猶題拙句;孫賓車上,欲引凡姿。進不自期,榮非始望。
大意:我年輕時曾經立志,到了中年多災多難。模仿劉孝綽的言辭,方寫成牋奏;偷學了王充的論說,才懂得言談。很遺憾每天要用的東西太多,而我的天分本來就太少。真是用牛涔之水測度湖海,憑蟻垤之土衡量嵩山。我曾經因此奮發圖強,可素來還是不善自量。後來李郢秀才遵奉宣揚仁旨,我私下體味善言;想不到閣下扇上居然題寫我的句子,就如孫賓石在車上,要薦引平庸的(如如趙岐一樣的)我(典前見)。自己不料有如此進身的機會,公賜我榮耀超過我原來的希望。
解釋:此處的「中歲多虞」,是說自己現在已無復中歲;而肯定進入老年了(不入老年不會如此提到自己的中歲)。溫「多虞」的「中歲」是指開成年間,當時溫經歷了「江淮受辱」、「侍從太子」、「等第罷舉」等重大事件,雖也有毀有譽,但謠言中傷甚囂塵上,《唐摭言》(卷十一)所謂「開成中,溫庭筠才名藉甚」是也。溫為此甚至不得不離開長安,「南遁」一段時間。到了大中後期時,溫已經多次失敗,仍一事無成、一命未霑。再向下讀:
今者末塗怊悵,羈宦蕭條。陋容須託於媒楊,沉痼宜蠲於醫緩。
大意:我現在正窮途失意,宦路蕭條。醜容難為官,得求楊得意推介,政治痼疾未治愈,應由醫緩之手治好。這裡的「媒楊」和「醫緩」都指杜舍人。而「沉痼」則指自己多年不能解決的政治病,所以這也不是大中初講的話。
解釋:陋容,自謙喻難登朝堂的人品。劉禹錫《上門下武相公啟》(《文苑英華》卷六六五)「藻鑒之下,難逃陋容。」媒楊,原誤作「媒揚」,依上下文語境改,指居間向漢武推薦司馬相如的蜀人楊得意,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卷一一七)。醫緩,春秋秦良醫。嘗醫晉侯病,二豎因藏於膏肓之間(見《左傳·成公十年》)。
亦曾臨鉛信史,鼓篋遺文。頗知甄藻之規,粗達顯微之趣。倘使閣中撰述,試傳名臣;樓上妍媸,暫陪諸吏。微迴木鐸,便是雲梯。
大意:我也曾寫過信史,學過前賢遺文。我很知道選擇詞藻的規矩;也大略通達修史者使文旨顯露或者隱蔽的旨趣。如果讓我任職史館、為名臣作傳;如鄭玄被馬融召見於樓上,能夠暫時陪同加官諸吏,貶惡而揚善。那麼你稍用一下你領袖群賢的權柄,對我就是通向青雲的階梯了。
解釋:臨鉛、鼓篋,前文已解。撰述,謂任史館修撰。《新唐書百官志二》(卷四七),「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元和六年,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二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又,(《唐會要》卷六四)「八年七月,監修國史鄭朗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准故事。」樓上,原指師門,此言對方之門牆。語出《後漢書鄭玄傳》(卷三五)「(馬)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妍媸,猶言賢不肖,當指歷史的是非正邪。諸隸,隸,疑作吏。諸吏,原作「諸隸」,今根據上下文文理改。《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輿車。」《太平御覽·職官部》「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這裡的「諸吏」,應即指「大中八年,增修撰四人」,當時史館改變編制。溫又處於大中九年「攪擾場屋」案發之後,當時朝廷尚未對溫的案子作出決定。因此溫抱志前來求懇求杜舍人。杜舍人,應是杜審權,根據《舊傳》 (卷一七七),「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溫上此啟的目的是要求杜舍人推薦自己做史館修撰。
(六)貶尉原因,喧騰物議
溫努力奔走多年,還是當不成史官,最後卻被制授隨縣尉。給溫庭筠下貶制的不是杜審權,而是裴坦。《貶溫庭筠隨縣尉制》(見《東觀奏記》卷下),是一篇頗有趣味的制文,其中褒多而貶少。這個貶制,就是對攪擾場屋的溫庭筠的處理。
「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庭,……豈以文學為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根據文中的「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庭」的話,知裴坦下《貶溫庭筠隨縣尉制》似當在大中十三年(至少裴庭裕如此認為)。而溫庭筠在大中九年的「攪擾場屋」的行為,即上引「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之事,《南部新書》卷五也記「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宏詞趙矩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當時負責吏部銓選的官員皆受到貶謫、趙秬等十人皆落下,獨溫一人,雖然作弊考場,卻安然無恙,而且過了四年,才最後被制貶隨縣尉。在此四年中溫曾上啟杜審權。這個「四年」,似時間過長。溫貶尉隨縣,也許早兩年,這樣他依徐商於襄陽時間也略長些(見下)。
我們先對《東觀奏記》所載《貶溫庭筠敕》(題目從《全唐文》卷七六四)作解釋:「勅鄉貢進士溫庭筠」——首句點出溫受官時的身份。「早隨計吏,夙著雄名」——說明溫的資歷和名望,還是二十年前的京兆薦名,或謂等第。此話與《唐摭言》之「溫岐濫竄於白衣」等值,其實對溫之多年厄於一第含蓄了很深的同情。「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這是文中唯一所謂「責詞」,而名貶實褒;就是真才直道、不為時所容的意思。行將滅亡的帝王專制制度當然不需要直臣。「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竟然毫不顧忌把溫比成正道直行而被放的屈原,當作懷忠抱屈而受貶的賈誼;「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則是冠冕堂皇地鼓勵溫有朝一日猶可重得恩寵、顧問左右,並且希望溫繼續潛心文章大業,結句點出授官主旨。難怪《東觀奏記》云「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這句話等於讓皇帝承認自己是昏君,代表皇帝說話的中書舍人裴坦難免要被君子嘲笑。《北夢瑣言》卷四也記「謫尉」(方城)事,但所載制文則與《唐摭言》有所不同。「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這裡去掉了「騷人、賈誼」之語而增加數句「責詞」;在不得不承認溫的文才的同時,稱其「德行無取」而於時無補,不合孔教。這樣的兩個版本,使我們對二者都不得不帶上一點懷疑。後來的《唐才子傳》則試圖揉合以上兩段話,把制詞改為「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為末。爾既早隨計吏,宿負雄名,徒誇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自未盡可靠。不管怎麼說,《東觀奏記》所引制文稱「可隨州隨縣尉」,可見已敕授溫庭筠官職,與一般的中第進士釋褐授官並無二致,制文之後作者評論「竟不中第」云云,是有問題的;「至是,謫為九品吏」正證明溫實際上是中第了的。中第算不算貶謫呢?也算也不算,因人而異。
從正面看,從盛唐到中晚唐的很多例子都證明,進士及第之後,在一兩年乃至更長時間釋褐而授縣尉(有時先要做校書郎之類清閒職),可謂司空見慣。例如許景先,少舉進士(神龍元年前),授夏陽尉官(《舊唐書》卷一九九);「張長史(旭)釋褐(開元年間)為蘇州常熟尉」(唐張固《幽閑鼓吹》);馮定(《登科記考》定為貞元十八年進士)登第,尋為鄠縣尉(《舊唐書》卷一七二);李商隱開成二年中第(《舊唐書·文苑傳》)「(開成)四年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附錄《玉谿生年譜》);「薛逢,會昌元年進士及第,為萬年尉(《唐才子傳卷七》〉;杜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舊唐書》卷一八一);等等。溫前後或同時之人登第、釋褐為縣尉皆為正常的遷升而不為貶謫。
但是各種有關記載,則不但眾口一詞地說溫被貶,而且還凑了諸多他被貶的理由。其一,《東觀奏記》所謂「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豈以文學為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把溫的「以才廢」歸因於唐宣宗靳惜祿位,當然不合理。這個「不可得而問」的原因其實是顧忌宦官,溫得罪宦官,連皇帝也畏宦官而不能用他。其二,《唐摭言》(卷十一)謂溫「以文為貨」、「攪擾場屋」,故貶隨州縣尉。這也不成立。我們看到在大中九年的舉場風波中,獨有溫不受處罰。我們可將《舊唐書·宣宗紀》(卷十八)所記大中九年發生的另一件事與溫「攪擾場屋」做對比:「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全質等三人偽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偽著緋衫,將偽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贊等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貫文。據勘黃續之等罪款,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敕並准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姦人,並放。」這也是作弊案,情節較考場作弊嚴重些。故當事人黃續之等被處以極刑。而大中九年事件,影響範圍卻更大,溫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負責吏部銓選的官員皆受到貶謫、獨有溫只是被「可隨州隨縣尉」而已,這能算得上貶嗎?其三,有人認為溫被貶是因得罪令狐綯。根據《南部新書》丁卷:「初綯曾問故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所以儘管唐宣宗很賞識溫,溫卻「為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尉」。《北夢瑣言》卷二,「綯益怒之,乃奏歧有才無行,不宜與第。」關於得罪令狐綯的另一種說法見《北夢瑣言》卷四「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綯)假其(溫庭筠)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曰:『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這裡說令狐綯密進溫所撰《菩薩蠻》給宣宗,溫不遵令狐所囑而泄露自己是作者,就得罪了令狐綯。按令狐與溫有舊誼,本是友好的,但對溫的政治處境卻無能為助;他自己的兒子因忌諱都甚遲得第,把溫政治上的不得意歸因於令狐綯,也缺乏證據。其四,還有一種記載,說溫不識在逆旅中遇到的微行的唐宣宗,因而被貶方城尉,就更是小說家言了;如《北夢瑣言》卷二「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北夢瑣言》(卷四)也有「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云云。
對於溫庭筠之貶尉隨縣,以下《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所記,更試圖給出一種甚為可疑的老吏之言作為解釋。「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辭送,惟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云云。」
首先,「無官受黜」的說法本身邏輯上就是矛盾的,這只是舊時雜說作者吸引讀者興趣的一種手法而已。「無官」則為平民,除非關入監獄,平民不可能再受黜,尤其不能受黜而反而成官。「謫為九品吏」須在原任職級別高於九品時方能成立。其次,我們考察當時情境。裴坦當制而「忸怩含毫久之」者,應是對溫這個特別案例,猶豫不決,久久不知如何措筆。只讚揚他是不周全的,因這是貶制;要斥責他也不合常情,因這是釋褐授官之文。所以他向身邊的老吏請教對溫褒貶毀譽的尺度。分析「老吏」所言,唐代前進士授官的制文,一般總是充滿讚揚和鼓勵;溫既是受貶,「舍人合為責詞」是對的。但老吏解釋「合為責詞」的話,「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就令人不得要領了。所謂「入策進士」,參見《唐摭言》卷一「試雜文」條云「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這句話,——也就是通過帖經試和雜文試兩場試,並且在雜文試中文章高妙者,被允許進入第三場「答策」試,也就是被「放入策」,成為所謂「入策進士」。而「答策」所試內容,神龍元年之後乃以詩賦為主。所以「入策進士」不過是進入最後一場筆試的鄉貢進士而已。又,所謂「望州」,本唐代七等州府的第三等。杜佑《通典》三三「職官十五」州郡下:「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又《新唐書·百官志四下》「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上州有)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而「望州長、馬」之官品,總比「上州長、馬」高一兩級,約為正五品(上下),竟比從九品上的「隨縣尉」高十六級。所以,老吏認為入策進士可與望州長、馬一齊資(解作同等資歷?或者退一步,一齊論資歷?都講不通),是不符合史實的。這種說法,不但更不能由溫為「入策進士」證明溫之任隨縣尉可稱貶謫,也完全談不上能說服裴坦「合用責詞」而使他「釋然」。這裡,老吏和裴坦之間的互動之因果,令人瞠乎其後,不知所云。裴坦撰制時是否想用責詞,是否受老吏啟發我們都不得而知,但裴坦名下所撰制文充分肯定溫高才令德,又比之為屈原賈誼,寫得確實相當出色,也相當出格的。我們從中看出,官方迫於當時士林讜論,簡直為授溫「隨縣尉」難堪而無以塞責。官方其實是一定程度上暗護著他,奈何他的政敵宦官勢力及其幫凶就是堅持和他過不去。
那麼,溫遭貶制而尉隨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除了自《東觀奏記》作者以來,認為所授官職品級太低而好像是謫的觀點前後承襲以外,其中必還有特殊原因。如我們前文已證,這個特殊原因是,溫曾侍從莊恪太子,位在司直(正七品上,因莊恪、文宗之死而未能實授);隨縣尉卻只是從九品上。二者相比,當然為縣尉是貶。而溫作為前朝曾侍從莊恪太子的舊臣,忠誠盡職、文才吏德都是已經被證明了的;雖反對宦官,而頗觸時忌,故連皇帝也顧忌重用他,但他在朝野都還是得到相當認可的。所以不管他如何大鬧考場,弄出多大動靜來,當政者都不認為他有罪。好像不給他好官做就是一種貶謫了。而他所受的這種貶謫,一是為了搪塞宦官勢力;二是含蓄著溫在開成二三年間從遊莊恪太子有所任職履歷的認可。有冤有理有才學甚至有功,卻常年屢次受挫,使這位詩人幻變出一種頗為詭激反常的行為:在考場為人假手。至大中九年他「為人作文」所引起科場風波已臻使執政者無法迴避而必須有所行動和表態的地步。經過朝中各派的折衷,制授他隨縣尉的九品官,形式上屬於前進士釋褐,所以溫實際上終於及第了。官方這樣做也是告訴溫,從此不要再考了,不要再攪擾場屋了。任職隨州隨縣,恐也與肯定溫庭筠的業師李程有關;李程元和三年至七年曾為隨州刺史,而溫則貶為隨縣尉。此事標誌著,溫已為官身,算是釋褐得官,他就這樣結束了求第的痛苦掙扎,而開始了求京官的頑強努力。所以,溫大中十三年(應略早)制授隨縣尉,是官方在當時政治形勢下對他自開成四五年間侍從莊恪太子以及等第罷舉」以來近二十年「濫竄於白衣」政治冤案的一個結論。
對溫而言,從正面講,這是「遂竊科名,才霑祿賜」(《投憲丞啟》)。從負面講,「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黃之末,則青草為袍。莫不顧影包羞,填膺茹嘆」(《上宰相啟二首》之一)。溫以六十有餘之年(大中十三年,62歲),才得如此小官、如此低就,談何當年雄飛之志。他感覺就像無心膏沐的棄婦,面對成了國級、副國級的「高幹」同學舊友,他卻最多是副處級,官場剛剛起步。他能不感到羞辱嗎?他多年想當史官的夙願又遠遠不得實現。所以他繼續堅定地努力向上,好像十分看不開的樣子,實際上是不屈不撓,求為京官,求能接近皇帝,求能做一點影響天下的事業。雖非可歌可泣,也是可悲可嘆的。這個貶謫是對他生命價值的貶謫,他對此安能逆來順受,他一定要再放出一些光來。以下我們還要從《送溫庭筠尉隨縣》詩的研究,確證溫的貶所只是「隨縣」,而絕不是任何別的縣。
(七)所貶之地,隨縣而已
《東觀奏記》卷下《貶溫庭筠隨縣尉制》之後,接云:「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只採此兩句)。』人多諷誦。」《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條: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庭筠之任對溫庭筠貶尉隨縣及紀唐夫贈詩這個基本事實,唐宋間筆記小說記載非常混亂。有認為是貶尉隨縣的(如《東觀奏記》卷下、《唐摭言》卷十一、《唐語林》卷三、《金華子雜編》卷上)。認為是貶方城尉的更多(如《北夢瑣言》卷四、《雲溪友議》卷中、《南部新書》丁、《全唐詩話》卷四、《唐才子傳》卷八等)。《唐詩紀事》,則兩項都認同;其卷五四稱「謫為方城尉」,卷六一則記「黜隨州縣尉」。《太平廣記》卷二六五「溫庭筠」條所引,作「隨州方城縣尉」,把兩種說法合二為一了。《舊傳》乃稱「(徐)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為方城尉,再貶隨縣尉」;竟然分出先後來,而且把楊收和徐商的入相罷相時間搞錯。《新傳》則言「執政鄙其所為,授方山尉」,又開新說,但不離「方城山」三個字。如認可貶尉隨縣及紀唐夫贈詩是同時發生的事,貶方城之說、先貶方城再貶隨縣之說、乃至授方山尉之說等就必須都有所澄清。今從以下紀唐夫《送溫庭筠尉隨縣》(〈全唐詩》卷五四二)原詩的解釋開始,希望能解決問題。
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
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卻累身!
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
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辭」,《雲溪友議》所引作「言」。「飲」、「遠」,《全唐詩》作「盡」、「路」。)
我們先把原詩譯成現代漢語,以觀其問題所在。首聯:為什麼你在當今聖治清明的時代屢屢像卞和一樣抱玉而哭泣?因為你不能金榜題名、參加杏園盛宴而沐浴春風啊!頷聯:雖然中書省鳳凰詔書下來、你得到了皇家一紙任命,你卻只為如禰衡才高寫鸚鵡賦,而累及自身仕途。頸聯:只好乾幾杯綠醽美酒澆滅你長期積累的煩懣怨恨,不必推辭縣尉的黃綬青袍,準備在風塵中上路就任吧。尾聯:照字面解好像是:如果方城比賈誼所謫地長沙遠,那麼它還隔著長安千山萬津呢。
尾聯的這個解釋可能被不少人認可,但其中有問題。《史記·齊太公世家》(卷三二)集解引韋昭注「方城,楚北之厄塞也。」所以位於楚之北疆的「方城」,無論照原意指楚北的楚長城,還是指楚國北部被(後世)命名為「方城」的某一城邑,離開長安的實際距離都比位於楚國南部的長沙要近得多。假設它比(所謂「若比」)長沙離開長安遠,這就構成假設複句的前半,而其後半,則是假設下的「結果」;「結果」是什麼呢?長沙已遠,若比長沙更遠,下句應該是「更隔千山與萬津」,而不是「猶隔」。「猶隔」的正確用法應是在讓步複句的後半,這時對應的上句應該是「方城(雖)不比長沙遠」。原文的「若比」和「不比」應該等值才對,這種等值只有在「若比」具有「怎能比」的意思時,才能實現。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怎樣理解「若比」二字,竊以為此處「若比」應理解成「若為比」,換言之,「若」字,是「若為」二字(意思是怎麼能)的縮略;這裡呈現的「若比」二字,是限於平仄和字數,在不能把「若為比」簡寫成「若為」情況下,不得不做的容易導致歧解的選擇。所以尾聯應該翻譯成:方城怎能比賈誼所貶的長沙更遠呢?但它離開帝都仍然是千山萬水啊。這裡含蓄了對溫庭筠的同情和安慰,同情他和賈誼一樣忠而被貶,安慰他尚不如賈誼貶得遠,而在安慰中仍帶有沉痛,雖然不遠,但離開京城還是千山萬水啊。
再回到詩的原意,該詩應是與「貶隨縣尉」相配的。詩中用「方城」這個更一般、涵蓋更廣的地名而不用隨縣,不僅是為了詩句的平仄,還因方城和隨縣本皆是「楚北之厄塞」,又是楚國之地名;而與「長沙」對舉,當然用「方城」比用「隨縣」好得多,故作者以方城作比而代指隨縣。實際上,自從《左傳》僖公四年「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以來,後世之古代楚國北疆因是楚長城所在、即「方城」所在,其地城邑乃至山嶺往往有被稱為方城者。《元和郡縣志》可以為証。其卷二一「唐州八到:西北至上都取葉縣路一千三百四十里。取鄧州路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方城縣,上。本漢堵(音者)陽地也……。隋改置方城縣,取方城山為名也,……貞觀中,改屬唐州。方城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左傳》屈完對齊桓公,『楚國方城以為城』是也。……隨州本春秋時隨國,與周同姓。……漢立為隨縣,……後魏文帝大統十六年改隨州,後遂因之。八到:西北至上都一千四百三里。西北至東都一千一百六十五里。隨縣,上。郭下。本漢舊縣,屬南陽郡。即隨國城也,歷代不改。」實際上,方城縣和方城山所在的唐州與隨州緊鄰,都在「楚國方城以為城」的範圍內。而觀《元和郡縣志》,或山,或城,名「方城」者,還有不少。例如卷二一「房州」竹山縣有「方城山,在縣東南三十里。頂上平坦,四面險固」;卷十四太原郡「石州」有方山縣;卷二一「太原府」之壽陽縣有方山,「在縣北四十里」。卷三一揚州有方山縣,這些地名中特別是位在楚北者,都和「楚方城」或多或少有一些歷史的聯繫。
所以,由紀唐夫詩中「方城若比長沙遠」一語,殘唐五代之際可能有人誤認為溫的貶所是方城而和隨縣有別,於是乃立新說,導致許多作者跟風。而「貶尉隨縣」說既然早已流行,就和新說並存。《太平廣記》卷二六五《輕薄》一「溫庭筠」條下作「隨州方城縣尉」,企圖將二說合併,但合併得不對,因方城縣並不屬於隨州。既然有了新舊二說,就產生了貶隨縣和貶方城孰先孰後的問題。《舊傳》大概考慮了隨縣所在的隨州「西北至上都一千四百三里」,而方城縣所在的唐州「西北至上都取葉縣路一千三百四十里」;而認為隨縣離長安遠,故判斷「(先)貶為方城尉,再貶謫隨縣尉」。《新傳》不同意貶二地之說,故將《舊傳》說法否定,卻又找出個「方山縣」來,離題更遠。當代一些學者認為,既然貶尉隨縣發生在大中十三年是有史料可證的,不可懷疑,則貶方城就是第二次了。殊不知若因過而受貶,方城應該比隨縣離長安更遠才對。而實際上,方城和隨縣都是上縣,方城反而離長安還近一些。以上筆者找出的方山縣或在揚州,或跑到溫的老家太原府去了,在可疑的史料面前自出機杼,就去事實更遠了,難怪找不出任何佐證。貶尉方城唯一根据是紀唐夫送溫庭筠詩的一種解釋,而溫貶尉隨縣是有很多旁證的,例如「溫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唐語林》卷三)。又李騭《徐襄州碑》《全唐文》卷七二四)「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十四年詔徵赴闕」,可見徐商大中十年以後就從河中節度使調任襄陽節度使;溫庭筠貶尉隨縣,正好是老友徐商的下屬,所以成了襄陽巡官。兩《唐書》本傳也皆記其事。後來徐商咸通五年為御史大夫之後,溫應是回到隨縣尉任上去了的。後文將附帶證明。
一言以蔽之,溫庭筠貶尉隨縣而已,什麼貶方城、方山,皆無根之談。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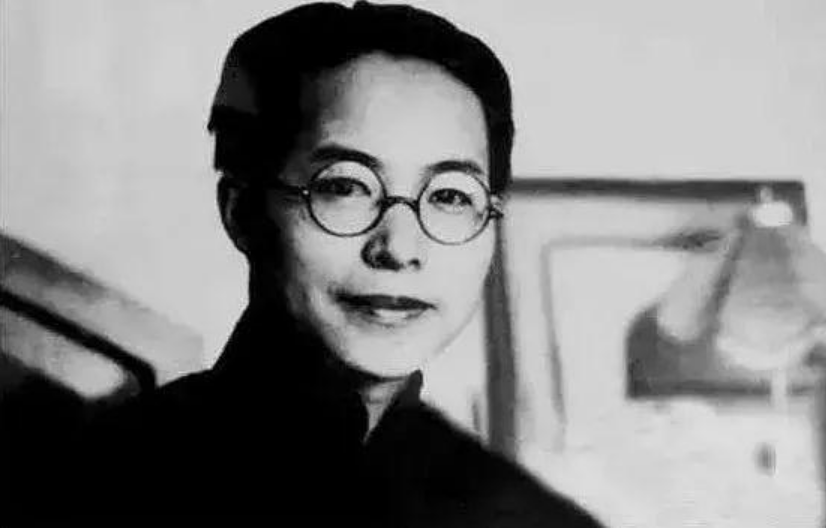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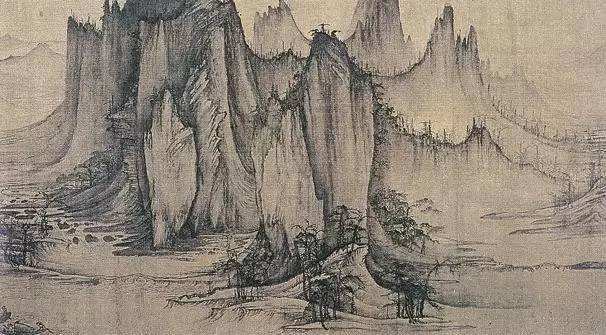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