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菩》詞十四,深情遠致
溫庭筠(798-866?)的代表詞作《菩薩蠻》十四首(以下簡稱《菩十四》),實是婉約詞派的開山之作,為歷代研究者所注目而頗有風流醞藉之美。本文將圍繞這組詞是否有寄託,對其相關藝術本質做一番粗淺探討。
一、關於「寄託」的爭論
歷來詞學研究者爭議的焦點是,作者寫這組詞時有沒有寄託?也就是說,美女詞面之下是否藏有深一層的主題?對這個有關這組詞根本藝術本質的問題,治溫詞者有以下幾種不同看法:
第一,「有寄託」說。湯顯祖稱溫詞「如芙蓉浴碧,楊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雋而妙入」(湯評《花間集》卷一)。從形式到內容皆予以高度肯定,顯然是認為溫詞有其寫美人之外的深一層的寓意。張惠言在其《詞選》中更評《菩十四》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節節逆敘。此篇(按即十四首之第一首)從夢曉後領起。『懶、遲』二字,含後文情事。
『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這就把「寄託」的大概內容也坐實了,甚至還指出了溫用「寄託」的具體手段。但是,「篇法」如何「彷彿《長門賦》而節節逆敘」?「照花」四句,如何便是「《離騷》初服之意」?語焉不詳,令人將信將疑。張惠言論詞重「寄託」,影響甚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言「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堪稱張論之嗣響。譚獻也認為「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懶起』句起步」(《譚評詞辨》卷一)。然則「寄託」說畢竟是一家之言,尚未得公認也。
第二,「無寄託」說。以王國維為代表的研究者對張惠言以後常州詞派的「寄託說」極力反對。《人間詞話》云:「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我們不否認王國維論詞有其獨到之境;他對詞史上許多重要詞人研究的結論不少已被詞學界所公認。然而他對張惠言的「寄託說」並沒有提出有力的駁斥,對《菩十四》也只是提出自己的讀後感罷了。這種看不出或不想看出《菩十四》「有何命意」的讀後感,不少人都有。
如近人李冰若《花間集評註》以《栩莊漫記》形式評《菩薩蠻》曰「鏤金錯彩,眩人耳目,而乏深情遠意」,且謂溫「亦不過一失意文人而已,寧有悲天憫人之懷抱?」——粗暴斷定詞作者是所謂「失意文人」,蔑視其人不能有「悲天憫人之懷抱」,所以不能寫出有寄託之作品;其推理的根據就站不住腳,更不用說由此推出的結論了。
第三,「折衷說」。施蟄存先生《讀溫飛卿詞札記》(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1978年10月)云「溫飛卿詞為一代龍象,固不必援比興以自高。然我國文學,自有以閨襜婉孌之情,喻君臣際遇、朋友交往、邦國興衰之傳統。……張皋文、周介存箋釋飛卿詞,亦是助人神思。然此乃讀者之感應,所謂『比物連類,以三隅反』是也。若謂飛卿下筆之時,即有此物此志,則失之也。」他指出張惠言等釋溫詞有寄託,作為讀者的一種感應則可,當成作者的本意就錯了。這就既抽象肯定把「寄託」讀入溫詞,又具體反對常州詞派論溫詞之寄託說,而自相矛盾。與認為溫詞之「寄託」也可能有,也可能無的折衷說是相通的。一般的讀者有這種推斷也就罷了。研究者是不能滿足於這種表層的結論的,「飛卿下筆之時」畢竟「有何命意」,還是應予深究,方能得出的論。丁壽田、丁亦飛認為至少就第一首而言,「張、譚之說尚可從」。又針對李冰若駁之曰「或謂飛卿不過一浪漫無行之失意文人,平生未遭何奇冤極禍,寧有悲天憫人之懷抱足以仰企屈子?此說可商。夫浪漫無行不過當時社會之片面批評,豈足以盡溫尉之人格」(唐五代四大名家詞》甲編)。二人部分地肯定寄託說,並駁斥李冰若言之太過。但他所留餘地太多,只好歸諸折衷一派。
第四,「存而不問」說。另外一種相當普遍的傾向,就是陳廷焯所說的「徒賞其芊麗」了。我們在多種《花間集》的注本和研究溫詞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對溫的《菩十四》各種各樣的細心文字注解和藝術分析;或極力鑑賞女主人公的形神之美,或批評飛卿能豔不能淡,或認為飛卿筆下的女主人公是完全客觀的描寫,更有不否定「寄託說」而不想為此立論的,也有蔑然指出其中有敗筆的。對這組詞畢竟有沒有「寄託」,則避而不談、「存而不問」,或論及而不論定。事實上,不徹底解決這組詞有沒有「寄託」的問題,猶如隔靴搔癢,就不能揭開其全部藝術內涵,任你變化多少種新理論、新方法,也說不到點上,甚至使研究的結果徒然離真實越去越遠,就很難從藝術上真正把握了。
《菩薩蠻》十四首之有無寄託的問題和爭論,實際上成了詞學研究中聚訟紛紜的一大公案。我們作為現代的讀者,應該怎樣通過古代作家遺留下來的作品去認識古代作家?或怎樣通過認識古代作家去正確理解其作品?上舉四種對於《菩薩蠻》十四首的理解,且不論其正確與錯誤的程度如何,它們的共同點就是:都沒有考察作者下筆之時的具體身世背景和可能的訴求,即作品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這就使對作品的立論失去了事實的基礎而帶上隨意性。事實上,溫庭筠平生偏偏遭際了詩人以來少見的「奇冤極禍」。尤其他以皇親貴族身份,侍從莊恪太子而幾乎被殺,「等第罷舉」多年後方中第,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經歷;而且一直處身南北司之爭和牛李黨爭的狹縫和陰影中,生前死後都受到謠言的誣蔑中傷。還有,人們罕有把溫詞與溫詩作一個比較研究,沒有因此看到溫在彼時彼地為文、寫詩和填詞的「文心」之共同肯綮所在。這就只好但從欣賞角度出發,而自然難免見仁見智了。
二、溫詩舉例
溫庭筠的詩文和詞在藝術上是密切關聯的。如果我們能從他的詩中找出「寄託「的實例,至少可以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他的《菩十四》中有寄託就不足為奇了。以下研究兩個例子。
例一:《織錦詞》(《全集》卷一)
丁東細露侵瓊瑟,影轉高梧月初出。
簇簌金梭萬縷紅,鴛鴦艷錦初成匹。
錦中百結皆同心,蕊亂雲盤相間深。
此意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
為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
象齒薰爐未覺秋,碧池中有新蓮子。
本詩十二句,前六句和後六句各一段,猶詞之上下兩闋。
細密的露氣浸潤了「瓊瑟」(美言寶貴的織機)而發出丁東之聲;由此美聲引出織機而託出下文織錦的美人。高高梧桐的影子已在星光下移動良久而明月方出,可知其人夜深猶織。然後,織者現身了。隨著「簌簌金梭」的神奇運轉,她巧手下的「萬縷紅」絲剛剛織就「成匹」的「鴛鴦艷錦」,她原是一位柔腸百結的望夫之女啊。那「艷錦」上的「鴛鴦」象徵郎情妾意、堅貞圓滿的愛情,這正與「成匹」(結對)同聲相應。南朝樂府《子夜歌》「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也用「成匹」諧音雙關締結良緣。接下來,寫錦上千百個同心結,花蕊散亂、深淺穿插掩映在彩雲般的底盤上。百結同心,是她對愛情美好的夢想,是「妾意」對「郎情」永不變的期望。把同心結置於繁花彩雲之間,更令人幻想愛情的天機雲錦。而同心結、連同上文的鴛鴦錦,以及下文的合歡被,都巧妙暗用《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諸句詩意,引人入愛情描寫之勝,不落俗套而韻味無窮也。
第七句,此意,即前六句所表達的柔情蜜意,這蘊藉鬱結的摯愛之情,為什麼想傳它而傳達不出呢?作者在此故作迴旋,讓讀者想像。第八句給出第七句所含問題令人驚異的答案。她所傳之情竟然如此高雅尊貴!只有嵌裝玫瑰琴柱的朱弦(練絲所製之弦)之琴才能為之傳達。這可真令人歎為觀止。玫瑰(美石)琴柱,極言寶瑟之華貴,寓意則嚴肅正大;正與「朱弦」相配。朱弦,據《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由首句的瓊瑟,在此悄悄轉成清廟之瑟;《詩經·清廟》鄭玄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所以「朱弦」者,竟可代指廟堂之樂,此意用之於織錦女,就超出了一般的言情詩,而正透露出作者捐軀報國之心。白居易《五弦彈》「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其中「朱弦」的用法,正同此意。第九句,上文微露其意之後,作者似又回到原來的女子角色,她說要把鴛鴦艷錦裁成象徵男歡女愛的合歡之被,待夫君來歸。第十句,然而眼前之境不過是兩地相隔,一心同望那滿天星斗而已,故此處又加一層頓挫,寫出女子癡情,實喻詩人報國的執著。
第十一句,香煙氤氳,似有暖氣繚繞著象齒薰爐,令人覺不出秋意。這只是詞面意思,韓偓詩所謂「已涼天氣未寒時」也。薰爐或香爐,本漢代「貴人公主」所用,有豐富的象徵含義。《西京雜記》「天子以象牙為薰籠」;曹操《上雜物疏》「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張敞《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鐘鼎彝器辨》考證「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唯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者,香爐之制始於此」。所以我們不得不說第十一句用特殊景物描寫暗示接近太子。第十二句就用雙關語直接說(自己)新得寵:看那園中碧池,正新結下蓮蓬子——「新蓮子」,諧音「新憐子」,此處就是「最近降恩寵於你」之意。可見詩人當時因驟得(侍從太子)高位,而喜不自禁,寫出這樣一首詩,讓讀者按圖索驥,慢慢追索。
可以看出,與這位織女有關的物事如瓊瑟(一樣的織機)、金梭、玫瑰柱、朱弦琴及象齒薰爐皆華貴之至。華貴到完全超出尋常實寫,而必然暗含寓意。觀其抒情過程,從瓊瑟美聲引出美物,進而寫美人和美人綺豔的夢想以及為實現夢想做出的美好設計,也引人遐想。把萬縷紅絲用金梭織為成匹的、繡滿同心結的鴛鴦艷錦,這種誇張而有力的描寫,不但表現而且超越了織錦女與郎君的深摯戀情。前六句作為言情詩,準確、細膩、深刻、豐富,繪聲繪色,令人目不暇接。細味其中委曲,真可媲美《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而更精緻,織錦女之意已經傳得千迴百轉深刻動人。詩人卻偏要說「此意傳不得」。而欲傳之,必待玫柱朱弦——就是「清廟之瑟」的朱弦。這就與首句所指、織出絢爛愛情的織機(由「瓊瑟」代指)前後呼應,開頭說織機如瓊瑟,這裡又隱隱呼應它就是清廟之瑟;通過如此匠心安排,「此意」能承上啟下,把前文織錦女的濃郁愛意全都訴諸朱弦琴的表現。這就超越了男女之情,而顯露廟堂情懷,暴露了詩人的自我。所以,接下來,「為君裁破合歡被」以下,雖還作女子口吻,其實相當直白地言君臣之事了。「合歡被」,以君臣之事論之,不像前六句中那樣帶有懸想(代指對報國仕進的切實期望),大概可以確定地代指君臣共濟大業了。以下「象齒薰爐」含著富貴熱烈的氣氛。「新蓮子」則幾乎直接寫出自己「榮非始圖,事過初願」(見溫《上紇干相公啟》)、即得侍莊恪太子的喜悅心情。
總結地說,這首詩表面看似織婦詩,看似相當精緻的情詩。然而華麗的誇飾描寫中有超出常理的內容,令人感到其中有非情詩所能包容者,而不得不深求。仔細觀察織錦女,她以金梭織錦,又以朱弦傳情,這個細節本身就是非現實的。我們只好把她理解為詩人自喻,或者說織錦女不過是被詩人導演的一個自我的藝術形象而已。由此推理,全詩所寫織錦女顯然不是寫實的,因為客觀現實中不會有這樣的織錦女;但是全詩卻寫得更合乎詩人的主觀現實:因為織錦女用一顆純潔堅貞的心所織出的絢爛愛情,正是詩人苦學成器、經世致用,效忠唐庭之夙志的象徵。從本詩實際存在著的詞面和詞底兩層意思,我們不得不說這首詩有寄託。
例二:江南曲(《全集》卷二)
妾家白蘋浦,日上芙蓉楫。軋軋搖槳聲,移舟入茭葉。溪長茭葉深,作底難相尋。避郎郎不見,鸂鶒自浮沉。拾萍萍無根,採蓮蓮有子。不作浮萍生,寧為藕花死。岸傍騎馬郎,烏帽紫遊繮。含愁復含笑,回首問橫塘。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流蘇持作帳,芙蓉持作梁。出入金犢幰,兄弟侍中郎。前年學歌舞,定得郎相許。連娟眉繞山,依約腰如杵。鳳管悲若咽,鸞弦嬌欲語。扇薄露紅鉛,羅輕壓金縷。明月西南樓,珠簾玳瑁鉤。橫波巧能笑,彎蛾不識愁。花開子留樹,草長根依土。早聞金溝遠,底事歸郎許。不學楊白花,朝朝淚如雨。
詩人運用「質文異變之方」,使此詩更有「驪翰殊風之旨」了。詩中濃厚的民歌色彩,可謂兼有樂府吳聲和西曲的特點,深得《採蓮》《陌上桑》等古樂府之妙。但詩人謀篇構思,又有明顯的意匠經營。用詩人自己的話說,雖然「尚慚於風雅」,卻也「劣近於謳歌」了。我們應注意的是,用一首似有民歌風味的樂府詩,詩人敘述了什麼故事呢?
當女主人公出場時,她自稱本來家在白蘋浦。「白蘋浦」應即「白蘋洲」,是柳惲《江南曲》中那位盼夫歸來的女主人公采蘋之地(《白氏長慶集》卷七一《白蘋洲五亭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她每天都乘著「芙蓉楫」蕩入茭葉深處,叫人如此難尋她的蹤跡,畢竟是為什麼呢?她竟「避郎」而使郎看「不見」她,就像忽浮忽沉而捉迷藏的戲水鸂鶒一樣。她在溪上無意拾得的是無根之萍、有心採取的是有子之蓮,她不要作那無根的浮萍活著,寧願學那藕花守紅而死。巧語出之以俏皮的女郎情話,形象生動、呼之欲出。「芙蓉楫」代指芙蓉舟,芙蓉雙關「夫容」,暗含對夫君的思念。蓮,雙關「憐」,「蓮有子」當謂所愛有人;藕,雙關「偶」,處處都是民歌式的雙關語愛情提示(《樂府詩集》之《子夜夏歌》有「乘月採芙蓉」;《讀曲歌》「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等語,應是溫所借鑑)。
當「岸傍騎馬郎」出現時,她「含愁復含笑」地避開了他,「回首問橫塘」了,此處的「問」從下文的追憶看來,應該是詰問、追索、乃至追憶之意。橫塘,地名,六朝以降詩中習指女子家之所在,本難以確指或不須確證。但由「吳大帝時自江口緣淮筑堤,謂之橫塘」(《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可知,橫塘所在之地,大致就是古稱金陵、秣陵的京畿之地。問橫塘,其實引導讀者詢問採蓮女在「金陵」所經歷之事,也是她自憶前塵。所以接言她曾住在金陵帝王之州的「金陵步」,門前就是朱雀橋;家中有流蘇帳、芙蓉樑,甚為富貴華麗。「出入金犢幰,兄弟侍中郎」,自誇舊業繁華,更勝羅敷誇夫的情趣。那時候,她「學歌舞」以求「郎相許」,飾容色以取郎之悅。你看她眉繞春山,腰細如杵,鳳管鸞弦,多少柔腸,輕羅薄扇,何等丰韻。她住在殿閣樓臺之中,瓊樓玉戶之內,眉顰目笑,「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度過一段十分愜意的時光,哪裏知道一個「愁」字。
然而「花開子留樹,草長根依土」之後,即繁華夢斷而種下前因、失去依託而退修初服之後,她卻嘆息悔恨昔日之嫁了「早知金溝遠,底事歸郎許」——既然我早就知道皇宮帝里是如此深遠難以高攀,我又何必嫁給「郎」呢?所謂「金溝」(《文選》卷二十二徐敬業(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玡城》「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句下李善注「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這就說明,金溝者,即「引金谷水」之「御溝」之別稱也,曲指帝苑、乃至皇家。只是她雖悲傷,尚能故作曠達「不學楊白花,朝朝淚如雨,」不願學楊白花,徒為昔日傷心、終日如女子一樣不斷以淚洗面。說是「不學」,大概是勉強自寬吧。
楊白花,據《樂府詩集》卷七三等記載,是胡太后為所喜愛者楊白花之南奔,傷心而作。柳宗元有《楊白花》詩(《全唐詩》卷三五三)「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全詩借樂府舊題,詠歌良臣投荒而朝廷無人的無限悲傷,是對樂府舊題的改造。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將看到,類似於柳所傾注的深度政治感情內涵,顯然也包含在溫詩末句之中。順便要說的是,柳宗元和劉禹錫都是溫庭筠業師李程的摯友。溫對老師的欽佩延及他對老師摯友的欽佩,所以在詩歌的創作上無論是有意或無意,效法柳宗元是可能的。
全詩故事情節很簡單:家居「白蘋浦」而篤於舊情的採蓮女避開了「烏帽紫遊繮」的「岸傍騎馬郎」後,自述曾經有一段華麗哀豔、恩情婉孌的「涉帝」(這個詞是筆者生造)婚姻。只是不知何故,或作者故意不說何故,她為什麼竟回到故地了。她的夫君畢竟是宮中什麼人物、結局如何?她本人嫁入宮中又重歸江湖,這是怎麼一回事?詩人走筆至此,竟不肯更著一字。但詩中的暗示已夠多了。
其一,採蓮女說「妾家白蘋浦」,如說西施出於越溪一樣,是指美女出身所在;如上文所言,是在越地。至於說「妾住金陵步」,其實是以金陵比長安,說她曾侍奉君王。
其二,一位江湖之女,自敘昔日富貴豪奢;她曾住在京華上都,瓊樓玉戶之內,又如此德容兼備,情深一往。她既有如此輝煌的昔日,為什麼在盛年又回到「白蘋浦」來了呢?「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只聽說有越女選入宮中的故事,豈有宮中豔妃又被送回越溪的奇聞?這個含蓄的細節是不現實的。我們只能把它理解為詩人杜撰,用來影射自己一度入為近臣,又回江湖之事。
其三,採蓮女又愁又笑、而避開的「岸傍騎馬郎」之服飾耐人尋味。烏帽,即隋唐時貴者所戴烏紗帽。紫遊繮,用紫色絲線做的可鬆可緊的馬繮繩;語出《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繮。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繮」(注意:年號「太和」,與晚唐也作「太和」的「大和」太近似了)詩人筆下的採蓮女為什麼避開「烏帽紫遊繮」的「騎馬郎」,該因此人「非皇太子」而委婉暗示她用情於皇太子吧?這和作者曾忠心侍從莊恪太子正可作類比。
其四,對「鳳管悲若咽,鸞弦嬌欲語」的解釋,若不深求,則可一般地認為鳳管美稱笙簫、鸞弦美稱琴弦(因琴聲如鸞鳴);二句不過描寫悲婉的笙琴之樂。但深求之,我們說,鳳管即笙,因「笙十三簧,象鳳之身」(見《說文解字》卷六)。「吹笙」又因「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的故事(劉向《列仙傳》卷上),成為與太子有關典故。溫的《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中「鳳懸吹曲夜」,正用此典。姚合《莊恪太子輓詞二首》(《全唐詩》卷五百二)「吹笙今一去」,則直接用「吹笙」指代太子本人。據此,我們說「鳳管」之悲咽所蘊含的採蓮女對故夫的悲悼,暗含溫對莊恪太子的悲悼,應不為過。而「鸞弦」,就帶上更深切的悲情,應涉及「鸞膠」或「續弦膠」的典故。《漢武外傳》「西海獻鸞膠,武帝弦斷,以膠續之,弦兩頭遂相著,終日射不斷。帝大悅,名續弦膠」;《海內十洲記》也載鳳麟洲上仙家煮鳳喙麟角煎為續弦膠。鸞弦在此可以理解成將斷而鸞膠難續之弦,「嬌欲語」者,含多少柔腸寸斷而不能說出。合言之,鳳管悲咽和鸞弦嬌語之中,寄託了採蓮女極力挽回不幸而又永遠不能復合的斷腸悲哀。這動人哀憐的細節所顯示的內容,暴露了她原是溫的「自家物」啊。
綜上而言,溫庭筠託興於美人而以兒女之情言君臣之事的詩篇,就謀篇構思的藝術而言,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詩中主人公的形象中帶有一種「非現實的理想性」:構成形象的各個因素、各個側面,其華美珍貴雖是現實的,而這些因素、側面之特定的組合卻是超現實而理想的;其鎔裁意象,既不為現實的某個原型所拘,乃能恰切地展現詩人極豐富的現實情感內涵。如對《織錦詞》中的女主人公,瓊瑟、金梭、鴛鴦錦、朱弦等美物個別看來都可以用來寫一個平常的採蓮女,但把這些形象因素用詩人的語言鑄成一個詩歌的整體,深究其中每個詞的底蘊和相互聯繫,這個織錦者的形象就發生了質變,變成了詩人的代言人。因為無論怎樣誇張美化一個實際存在的織錦者,詩人也不至於如此費詞。我們在這種理想化的描寫之中,在穠詞重彩之中,恰恰可以看見詩人的本心,也就是說,在詞面的異彩中窺見了詞底。認識到詩人這樣的顯微之趣,我們乃可以辨別他的具體篇章究竟是寫實還是寫意,是無寄託還是有寄託。二是詩中主人公的形象具有一種現實的特殊性:她那獨特的經歷和心理,反映出詩人自己具體的人生道路,以至連詩人本身的政治遭遇的特殊細節都通過女子愛情心理的刻畫、深刻細膩地表現出來。如《江南曲》中的採蓮女,她反常的遭遇、堅貞的愛情、欲言又止的心曲,令人深思的人格,恰可以印證溫侍從莊恪太子的人生際遇。但無論「非現實的理想性」還是「現實的特殊性」,都是一種藝術手段的兩個方面,各有所側重而已。質言之,詩人在詩中設下貌似不合理的語言或情節,使讀者發生疑問而循著詩人暗示加以追索,終可探到詞底,找到其寄託所在。詩人要使「微」者得「顯」,總留有蛛絲馬跡,否則豈不埋沒了他的深心!
中國先唐詩賦素有以「求女」喻「求君」的傳統。由於臣事君、妻事夫的封建倫理綱常的長期壓迫,兩漢以下更多以女子自喻。例如曹植的《七哀》、《美女篇》《雜詩·南國有佳人》等,都有這種表現。誠然,臣之受制於君更甚於妻之受制於夫。有的論者說晚唐溫李等人的詩篇多女子氣,似也近乎事實。然而對於溫而言,即使是寄興於女子,仍掩抑不住他的個性:那種至死不變的陽剛之氣。以兒女之情言君臣之事,溫庭筠已沿著這條狹仄的藝術之路走到了他的終極:在全是比興體的賦中,句句有言外之言,語語含意內之意;把比興的運用拓廣和加深,廣到無事不可,深到無情不可,豔到不能再豔,曲到令人費解——實際上,只要弄清他的生平,畢竟可以理解他的本意。
溫庭筠有詩如此,說他的《菩》十四首有寄託,應不奇怪了吧?
三、《菩薩蠻》十四首的創作原委及藝術總論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南宋王灼《碧雞漫志》云「今《花間集》溫詞十四首是也。」據此,溫撰《菩薩蠻》諸闋而由令狐綯進獻唐宣宗,當在令狐綯為相而溫求官求第屢屢不得意的大中三年後,也應在溫大中十三年貶尉隨縣之前。《唐才子傳》有與上述類似文字,其後且云「出入令狐相國邸第中,待遇甚優。」又,不知作者的《樂府紀聞》記錄以上《菩薩蠻》有關軼事之外,謂「『令狐綯假溫庭筠手撰二十闋以進』云云,且言溫曰『中書堂內坐將軍』,以譏其(令狐之)無學也。由是疏之」。通過研究溫庭筠與令狐綯的關係及當時情勢,我們得出以下幾個看法。
其一,對今傳《菩薩蠻》十四首,李冰若《栩莊漫記》評論曰:「為當日進呈之詞,亦為平日雜作,均不可考」。愚謂《北夢瑣言》關於令狐綯「假其(溫庭筠之)新撰密進之」的記載,說得很清楚,這二十首《菩薩蠻》就是「當日進呈之詞」。其實自後蜀廣正三年(即公元940年)《花間》結集,去溫庭筠之死不過七十餘年,這十四首詞,已經作為整體而共同出現,絕非偶然。其詞俱在,其情其文,有不可隔斷的連續性,它們當然屬於一個整體。然通十四首觀之,雲龍霧豹,千姿百態,婉轉旖旎、悱惻纏綿之氛圍中,敘事條理並不分明,首尾之間,似續若斷,故《樂府記聞》所謂原作二十闕之說,應是有根據而可信的。現存的十四首,比原作少了六首,應是溫將自己作《菩薩蠻》之事泄露出去之後,其中主旨太露而於「事體有妨」者被除去造成。但即使這十四首詞中,意脈仍一以貫之,都是託興於一個不幸的高貴婦人,描畫其貌態情懷和經歷的,是用「組詩」的形式,寫一個主題;絕無理由把它們看成「平日雜作」。作為溫詞的代表作,當初所進二十首,既要符合宜於歌唱的宮詞形式,每首各自成首尾而聲情搖曳,又要寄興於深,藏意於密,詩人慘淡經營而歸於自然,是費了斟酌的。在宮中傳唱而「遽言於人」之後,可以想見各方面勢力、尤其是宦官勢力的反應;給令狐綯造成麻煩,他因此對溫不滿是當然的。
其二,溫與令狐綯的關係確有「待遇甚優」到相對冷漠的過程。溫大中初《上令狐相公啟》乃求令狐推薦自己為史官之作。啟言「豈繫效珍之飾,蓋牽求舊之情」,明言與令狐有舊;啟又言「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與溫大中後期上令狐綯的《上宰相啟》之亦云「三千子之聲塵,夙與玄圖」,構成一種連續。所謂「預聞詩禮」者,暗用《論語·季氏》所載孔鯉「趨而過庭」「學詩」「學禮」之事,意為當年令狐綯受父訓時,自己是在令狐楚門下在弟子行的。「夙與玄圖」則更說明自己嘗參與令狐楚的某項文章事業。令狐綯入相,溫以舊誼來投而為令狐所接遇,本順理成章。但溫畢竟有前朝舊案,且為宦官所深忌。而令狐為相,亦不能不顧忌宦官之勢焰,又有黨人之偏見在作祟。所以他之善遇溫是有限制的。溫若不顧利害,違反了令狐的施政意願乃至個人利益,令狐對他就更無奈了,雖然還不至於仇讎相對。其實,令狐正因與他有舊情就更不能舉薦他。考慮溫與令狐關係的起伏和他自己長期厄於一第、以及大中十三年貶尉隨縣的經歷,這一組詞大約寫於大中八九年間。其時溫既未得官,亦未得第。
其三,令狐綯為什麼要把溫所撰《菩薩蠻》「密進之」而「戒令無泄」?溫是當時極負盛名的詞人,令狐綯找到他填詞進呈,可謂找到了國手,是很有知人之明的。查令狐之行實,《全唐文》卷七五九載其《薦處士李羣玉狀》。又《資治通鑑》大中十二年記其推薦詩人李遠(庭筠之友)事,可見令狐還是能推薦賢人的。他作為位極人臣的大中朝在位十年之宰相,在輔政上當然要迎合宣宗,但卻不至於強取溫撰《菩薩蠻》著作權為己有。所言「密進之」而不讓外人知道其詞為溫作,不是要瞞宣宗,而是要遮某些人耳目。但令狐會怕什麼人以至「戒令無泄」呢?只有唯一的答案:怕宦官。《通鑑》大中八年記唐宣宗私下避開宦官召見翰林學士韋澳,他對韋說自己還很害怕宦官。令狐綯密奏對宦官採取「有罪無赦,有闕無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的方針,其事泄,其後南北司仍勢如水火。溫是宦官的仇人,而且幾乎是個欲報仇的仇人,宦官對他十分嫉恨,不但曾阻斷他東宮進身和科舉進身之路,也不會容他進詞宮中而得志的,尤詞中含有對他們的譏諷時。
其四,溫為什麼要「遽言於人」?令狐不過想利用溫的精雅篇什取悅宣宗,他並不想因此招惹宦官。溫卻不能這麼想。他已因宦官之仇的干係多年受盡誹謗而被壓抑。現在能直接撰寫詞章、服務皇帝而傳唱宮中,他當然不肯自隱其名。它不但要極力投合宮廷趣味,發揮其擅長,由此炫才以市寵;還要藉此抒寫苦衷、剖白心跡,達到獻賦以明志的目的。於是一組精緻絕倫、曲意深包的《菩薩蠻》就產生了。
溫殁後一千一百五十多年的審美實踐證明,若不知《菩》詞作者(對當時人而言),或不知作者生平大概,尤其侍從莊恪太子前後之事(對後人而言),從中但見流金溢彩而為之目眩神迷,含英咀華而終罕能探驪得珠。這組詞,即使看作宮詞,也是登峯造極之作。而正因為其中含有更深厚的底蘊,或者說有作者政治上苦心的結晶,才使它超越了宮詞。那麼《菩薩蠻》十四首總的藝術特徵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一,從賦的角度觀之,這十四首內在的若斷若續的敘事線索,表明所寫的是一個貌比西施的失意宮人。她當年本「家住越溪曲」(第九首),繼而與她後來苦苦思慕哀悼的情郎「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第三首);但不知何故從綺羅叢中回到了江南,「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第十首);無限傷心地追憶昔日,「當年還自惜,往事哪堪憶」(第十二首);她孤獨地沉緬在絕望的哀思之中,「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第十首);而今只能在「玉關音信稀」(第四首)的情況下,哀嘆著「故國吳宮遠」(第十四首),而「相憶夢難成」(第八首)了。這位美人,像《江南曲》中的採蓮女一樣,曾有承歡侍宴的繁華舊夢;但是好景不長,自從遠適江南故地,便只靠追思回憶、傷心懷舊了;盛年獨處,無心膏沐,撫今追昔,不勝悲苦。雖然她的儀態風韻,比採蓮女更豐富深刻細緻,其惟妙惟肖,更像宮中嬪妃,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在她的形象勾勒中,套印著詩人的苦悶和追求,反射著他的人生失意,尤侍從莊恪太子的傷心往事和「等第罷舉」多年不第的無限懊惱。鑑於原作是二十首,這流傳下來的十四首應是通過某種刪削之後的劫餘,也就是說,在溫「遽言於人」而暴露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之後,很可能為了搪塞宦官,當時把一些主題更為鮮明而容易被看出者刪掉了。所以我們不能期望這十四首詩能給我們一個更詳盡深刻明確的故事。因為被刪而造成的空白,造成十四首中意脈不能完全連貫成完整一體的缺憾。對後代的讀者而言,只好如面對一個斷臂的維納斯而興嘆,而接受這個事實。也因此難怪治詞專家們的議論不能統一。
其二,詩中女主人公所相思的對方始終沒有亮相。但從暗示中頗可窺見他絕非尋常人物,而且已死。「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張惠言看出其中是有寓意的,卻未具體說清是何寓意。但我們至少可看出,男女雙方昔日之珠聯璧合是在宮中,男的是宮中人物,他不是皇帝,也至少是皇子啊。又這十四首,屢用「畫樓」字樣:「畫樓相望久」(第七首),「畫樓音信斷」 (第十首),「畫樓殘點聲」(第十四首)都表示女主人公所思之地。對比溫《生禖屏風歌》「畫壁陰森九子堂」與《蔣侯神歌》(此詩諷楊賢妃而憫懷王德妃),「畫堂列壁叢霜刃」中「畫堂」與「畫壁」之解,就可知「畫樓」可以理解成「畫堂」的隱蔽的同義語。據《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注「甲觀在太子宮甲地,……畫堂畫九子母」。如此平常而看似毫無出處的字眼,竟然也可掩飾著直指太子的所在。如果我們不深求其出處,詞中女子更具一般性。安知在這一般性之中,竟蘊含著如此的特殊性?溫就這樣善於似無若有地用「典」說事,不那麼坐實,讀之反覺更加空靈;即使直接影射他的親身經歷,終不許一語道破。例子留待逐首解詞時說明。
其三,注意到這十四首詞是以一組宮詞的形式出現的,每首自具首尾而合起來連成一體,它當然不能像敘事詩那樣脈絡清晰地交代事件發展的過程。然而作者所欲寄寓的有才而不用、忠而被謗的基本志節懷抱卻貫穿其中。具體地分析起來,雖然不能說全是「節節逆敘」,卻多在上闋(或其前兩句)憶及舊日之情,而在下闋(或其下兩句)寫到眼前之景。正是在這種今昔的情景交錯之中,突出了現實和夢想之間的巨大落差,使我們在其特殊的「情」的背後,窺見了詩人的事。而能大概地把這原來的十四首按照女主人公懷念的事情按時間排列起來(而標以阿拉伯數字)。所謂「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他所寄託者,已不是一般的志節懷抱,連自己具體的遭遇感受也託比興出之。如此一個「美人」形象,多處能與詩人的特殊現實經歷相印合,仍然是因為它的超現實性直接與詩人的自我相通,在似乎不合理的地方顯露了詩人寄託之端倪。這裡沒有乘龍駕雲、升天入地那種開闊雄渾的境界,卻在鏤玉雕瓊、拈花照影之工巧哀豔的描寫中別運機杼、獨闢蹊徑,把「美人香草」的傳統比興引向更深微細緻的運用,這是溫的特殊貢獻。無論承認與否,後世詞人,鮮有不受其影響者。
其四,這十四首中,除了大量的句子外(有些留待逐首解詞時再說明),「略露寓意」者尚多。影射宮廷的名詞,「青瑣、金堂、故國、吳宮」之外,玉樓、玉關、畫樓等也應算入。另外,花木蟲鳥之名,各因其意象的繼承性而引申入微,恰切地含蓄了各種感情。楊柳,凡八見,皆寓不同場合不同時段的離思;杏花,兩次,暗喻科舉相關的事。牡丹三次,多暗指遇合太子及文宗朝悲劇故事。其他如棠梨、梨花、夜合、萱草、竹、芳草,無不具有暗示或比喻作用。至於鳳凰、鸞鳥、鷓鴣、鴛鴦、鸂鶒、翡翠、子規、曉鶯、燕子、蝴蝶,也多是富於愛情內涵或悲劇精神、甚至報喜、報春功能的形象。
《菩薩蠻》十四首是溫應令狐綯之命為唐宣宗所寫,在精雅濃豔的宮詞形式之下寄託了自己的苦衷。其詞不但是對於莊恪太子的《招魂》之曲,而且是對他自己的《哀時命》之賦。固然千折百回,那是因當日極其複雜的政治形勢下,溫作為前朝謫臣向新君獻賦明志,不得不寫成宮詞所致。總之,《菩薩蠻》十四首是有「寄託」的,是確實有,而不是可能有,是作者有意為之,而不是讀者穿鑿的一種讀法。是典雅的宮體詞,又是以宮體為掩飾的的政治抒情詩。認識到這一點,是理解其詞的關鍵。這裡我們順便論及本文開頭舉出的有沒有寄託兩種主要觀點。張惠言主寄託說,可謂偶然言中。這除了與常州詞派論詞重寄託的時代背景有關,也與張氏本人易學家的學養有關。寄託說的反對者便譏張氏以說易家法解釋溫詞。但我們還是得重視《周易》多少世紀以來對中國詩歌比興之運用的的深刻影響。而溫夫子自道的「頗識顯微之趣」,正是得之於《易》。溫是自覺按照《易》法的誘導創作的。他不但自覺選用或質直或豔麗的詞藻而能質能文,文質彬彬,而且有意識地掌握著筆下形象對為文主旨的顯露或隱藏的程度,而能微能顯、能藏能露、能深能淺。我們今天研究他的一些晦澀曖昧的作品,當然也應彰其往而察其來,弄清他的身世和主要經歷;只有如此,才能把他的作品顯其微而闡其幽(當然,對作者身世和對其作品的研究,應該是互相促進的)。但張沒有這樣做,只是就詞論詞,而功虧一簣。
至於國學大家王國維的學說,他的「審美直觀」是建立在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哲學之上。他雖力圖成為一個「能忘物與我之關係而觀物」的「純粹主觀」(1904年發表《叔本華之哲學與教育學說》很難成為我們讀溫李詩的指導),但在這種純粹主觀制約下的審美直觀,就被《菩薩蠻》詞溫軟豔麗的辭藻所眩惑,而稱之為「有何命意」了。實際上,任何移植過來的西方文學或哲學理論,都不能完全無誤地解釋極其複雜的中國文學和文學史現象。
四、《菩薩蠻》十四首簡釋
對這十四首詞的解釋和分析,前輩學人發言已經夠多。以下只就其宮體的結構而簡言之。全十四首表面上寫一個失意的富貴美人之撫今追昔的貌態和心事,每一章似乎總可得出有無寄託之二讀。雖然景中情、情中事有時故作曖昧,我們還是能就溫之主要人生經歷而言,嘗試把這十四首幾乎按作者的原順序排起來(當然當中有斷裂)。
其一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
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
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第一首,上闋寫美人晨睡,懶起弄妝。首二句美人亮相,主要顯其「內美」:她眉額閃爍如春山明滅,鬢雲散亂而欲遮香腮;對晨睡未起的貌態,工筆細描,表現了作者對女性美極端細心的客觀觀察。三四句轉而揭示她的心態,是理解此詞的關鍵:「懶起」畫眉,遲遲弄妝,無心打扮,是無「悅己者」可「為容」的表現。這裡暗含「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詩經·伯兮》)的惆悵。這種心態,關乎其昔日高升之夢和今日沉落之悲。溫《上宰相啟》(二首之一)說「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黃之末,則青草為袍」;也把自己為九品縣僚、懷才不遇的狼狽無奈,用美人的懶於梳妝來表達。當然,依照以美女喻良臣的慣例,美女之美及其不偶是要比喻良臣之良和不遇的。但是他對女性美之驚人形似而近於純客觀的描寫,不能不說是基於他的實際生活體會,尤其是愛情生活體會。下闕前二句正面寫弄妝。簪花照鏡,前後兩鏡相映,鏡中復有鏡,層層影像,花面和鮮花交相輝映,美不勝收。這裡所呈現的女子的貌態,正暗示了她當年無限風光的得意春夢。這個夢在後二句的新裝上卻失去了鮮活的生命。那「繡羅襦」上新貼的「雙雙金鷓鴣」表明,女主人公與其所夢對方比翼雙飛的願望只能繡在衣上,存在心裏,憶在夢中。其中「金鷓鴣」,成為溫詞品之濃艷而缺乏生機的定評。其實,溫筆下的美女,淡妝濃抹都是由他自定的;「金鷓鴣」是一個預定的美麗而無生命的形象。
張惠言謂「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節節逆敘。此篇從夢曉後領起。『懶、遲』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今按:謂十四首可以讀出「感士不遇」的主題是正確的,只是尚須求其詳細。反復誦讀《長門賦》,知其用心理的直接描寫加上景物的反襯,寫陳皇后的失寵之悲;是變換角度深刻表達失寵后妃的痛苦,其文之敘事順序則是以其賦寫出之時為時間原點,不時向昔日追溯的。統十四首觀之,也可把此首(也就是美人的現在)當成起點,後面的十三首回憶往日或往日的往日,這自是倒敘,而且倒敘之中復有倒敘;並且不時回到目前。所以如把「節節逆敘」理解成每一節本身都是第一首的一種逆敘,好像可通。「懶、遲二字,含後文情事」,即女主人公今日對於往事的種種傷心,正是這種「節節逆敘」的讀法之表現。至於「『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由《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可以推想,「入朝見嫉」的士之引退而「復修初服」,即去追求出仕前的樸素無求的生活模式,與「入室見嫉」的女失寵而「弄妝」呈美,很難說可以相通。溫從暫時的高位落下,百折不撓求進取,也並非「復修初服」。這第一首的主旨,寫美女之慵懶弄妝而孤芳自賞的姿態。如果非要與「士不遇」相提並論,應是表達了溫失意而仍盡力而為、不肯完全頹放的人生姿態。
其二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
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
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第二首,上闋寫當年的合歡之夢和夢後餘波。起首二句,畫面其實暗含二人。「水精簾裏頗黎枕」和「暖香鴛鴦錦」是今日「惹夢」之因,因為這些物事所昭示的環境本身就是女子與故夫兩情相悅的舊事舊夢。這個夢,亦是第一首「懶」「遲」之故。「鴛鴦錦」,溫《織錦詞》「鴛鴦艷錦初成匹」給了我們足夠的啟示,是象徵愛情好合的亮麗錦緞,亦是溫用來表達遇合君王(此處指莊恪太子)的隱語。所以對於詩人而言,「暖香鴛鴦錦」所惹之夢便是他的東宮舊夢,以艷語出之而已。從宮詞的角度看,精美的物事排比之中,不寫人而一雙璧人自在其中,《洞戶》詩所謂仙郎玉女也。
「江上」二句之景語,歷來歧解最多,它和上文有何聯繫?張惠言謂之「略敘夢境」,俞平伯則謂「說實了夢境似太呆,不妨看作遠景」。筆者解作「夢後餘波」。這兩句分明是行客羈旅所體驗的情景,所以有的論者寧可把本詞當作一般的思婦之詞,當作從思婦角度(從對面著筆)懸想遊子日夕行舟江上所見景致。仔細體味二句內涵,殘月雁飛,表明是拂曉時分的仰觀,江
上柳煙,則是初春季節的遠望。如把這兩句的景置於同一畫面,則觀察者應是行舟江上,岸柳如煙,望雁船頭,殘月在天,春色再來而鴻雁無音,那江聲月色,行人征雁,暗含多少傷春之情,離別之悲,用這種景語來比襯起首二句的歡合,可謂「以哀景寫樂」,而哀樂自加倍了。但其觀察之細膩,含蓄之微妙,非親歷者不能體會,更非不出門之閨中思婦所能想到或看見。這其實是詩人昔日(開成末)「南遁」旅途中的情景,現在移作女主人公之夢後餘緒而已。
歷來評論家雖交口稱讚此為「好言語」,卻未講出其詞微妙之所以然。其實,柳烟雁飛之景與上文之情本來若即若離,迷離惝恍中令人似解非解。俞平伯先生就此句評曰:「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心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即以此言,簾內之清穠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載以下,無論識與不識,解與不解,都知是好言語矣。若昧於此理,取古人名作,以今人之理法習慣尺寸以求之,其不枘鑿也幾希」(《讀詞偶得·詩餘閒評》——引自網上,未見過其原書)。其說誠為讀詞有得的經驗之談。然細味之,殆涉於不可知論歟?如果不知其相對確定的內涵亦可認「江上」句作「好言語」,填詞者就是這樣東一句西一句地湊「好言語」而毫無形象聯繫麼?古人名作,之所以為「好言語」,正因為更經得起「以今人之理法習慣尺寸以求之」。至於「今人之理法習慣」,若指在文學研究和欣賞中探明作者塑造藝術形象的方法和心理,本不足厚非。溫在此用了什麼藝術手段呢?簡言之,他用了好像是寫文人羈旅的景語寫簾內美人的情思。這是溫慣用的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我們稱之為「代入法」,就像以「朱弦」寫織錦女一樣,詩人暗暗地由描寫美女轉換成描寫美女所喻的良臣,正是實現「以兒女之情,言君臣之事」的必要手段。昧於此理,則雖知其好言語,實難求正解。話說回來,以此凄美悲涼之景襯託那鴛鴦舊夢,不正暗示良辰不再麼?
下闋,寫眼前伶俜寂寞,猶能褒美自重。「藕絲」二句,巧用諧音雙關和語義的雙關,表現了女主人公為情所困楚楚動人的形象,以及懷人亦復自傷的癡情。藕絲,顏色名,淡紫近白,又藕絲,諧音「偶思」,即思偶也。秋色淺,指女主人公所著香衫,這裡反文見義,正見相思之深。人勝,即人日剪彩勝為頭飾,紙花之類;參差剪,謂長長短短剪成。又,「人勝參差剪」全句,以語意雙關與「偶思」相對,似也可解作「人簡直有過於長短錯落剪成」、似弱不勝衣。末二句,寫妝成女子臨風玉立,雲鬢花顏,頭飾隨風搖曳的丰姿神韻。不煩多言,第二首中,託美人以寄興詩人事君王,微旨已顯,話說回來,即純以艷詩讀之,雖有令人不甚了了句,亦情緻纏綿,音韻諧婉,的是耐人尋味「好言語」。
其三
蕊黃無限當山額,宿妝隱笑紗窗隔。
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
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
上闋描寫夢中歡會,哀嘆初戀時節。首二句亦如第二首,也是寫夢境,表面寫女子「宿妝」的貌態和容止,其實是寫當年男女歡會。「蕊黃」即額黃,唐時女子以黃色顏料(可能是花蕊或松粉等製成)塗額為山形;無限,指額黃成暈染狀,沒有清楚邊緣。當山額,正在那「山額」上。溫《偶遊》詩(《全集》卷四)有「額黃無限夕陽山」句,與此句可相參。宿妝,夜晚就寢保留的殘妝。隱笑,含蓄半露的笑;「隱」與「宿」相對,做形容詞用。兩句之中,另有人在焉,否則,此女子之「隱笑」,就無著落了;而此人就是女主人公的故夫。紗窗隔,謂人在紗窗內,那麼誰在紗窗外呢?這樣似更神祕些,作者保留一層祕密給讀者猜測,令人有一種不能盡觀廬山的不足感而更企望其美,也許如有人說的倫敦的霧。三四句言女子與她的郎君相遇在牡丹盛開之時,謂相見恨晚,別離太速。牡丹盛開,已是農曆三月下旬,春光將盡,喻已非年少。筆者考得溫侍從太子,始於開成二年,已四十歲,正合此喻;而侍從時間僅一年,太子便被宦官和楊賢妃合謀害死,可謂短促,所以稱「暫來還別離」。
唐蘇鶚《杜陽雜編》記載,「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為樂。……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新唐書》(卷一七九)「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憑殿欄誦賦,為泣下。」舒元輿是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變中被宦官不分青紅皁白野蠻屠殺的四位宰相之一,由於宦官因甘露之變事尋機復仇,使唐文宗更受困辱,他吟誦舒的《牡丹賦》而淚下沾臆,悲慘而無奈。溫是唐文宗親自俞可的太子侍從官,他在那牡丹時(甘露之變後的幾年)「冥升而欲近青雲」之希望的幻滅自是刻骨銘心的。牡丹的國色天香映襯著莊恪太子慘死的命運,當然也承載著溫的慘痛回憶。這也是「牡丹時」含蓄的意味;對晚唐文宗至宣宗時代的讀者,這種意味應是清楚的。
下闋兩聯則是刻畫和剖析今日之人情了。「翠釵」二句,如前賢所言,是通過寫女子頭上兩股合成的金釵和金釵上的彩蝶雙舞,來反襯女子的形單影隻的,這孤獨的美麗和美麗的孤獨,有悲劇的底蘊。末二句說,這心事,這不可言傳又無法實現的心事,誰會竟然能知道呢?大概只有天上那輪明月,映照鮮花滿枝,可以鑒我心中之悲。前人浦江清《詞的講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引《說苑·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解末二句,認為「知」、「枝」諧音雙關。果如此,更增語音語義融合之美,動人哀憐的傾訴中,其中二人,是被無情分隔的情侶,還是曾經生死相託的君臣?當然兩種讀法皆宜,而淺者深者,皆有所宜也。而最宜者,從前者讀出後者也。
其四
翠翹金縷雙鸂鶒,水紋細起春池碧。
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
繡衫遮笑靨,煙草黏飛蝶。
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上闋寫鸂鶒戲水、棠梨盛開,以景物暗示昔日歡會之夢。首二句寫一雙翠尾金羽的鸂鶒,在碧綠的春池中戲水游來游去,應是喻指昔日的兩情相悅,可以想像那鳥兒交頸相歡、充滿生機的溫柔,碧水漣漪也蕩漾著愛的深沉和歡樂。那是怎樣的難得機遇啊。《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陸璣疏「甘棠,今棠梨。」海棠梨,就是開紅花的「甘棠」。一場春雨過後,雨霽天晴,池邊的海棠梨正開滿紅花,應也含「勿翦勿伐」的愛惜之意。溫《醉歌》「唯恐南園風雨落,碧蕪狼藉棠梨花」也透露對「海棠梨」的愛惜。那經雨而帶著水珠,紅花滿枝的海堂梨,也許象徵著美滿的婚姻遇合吧。下闋寫如今美人姿態心理及現狀。「繡衫遮笑靨」,寫其憨態可掬,用衣袖遮住了笑靨;煙草黏飛蝶,似是以信手拈來的蝴蝶黏於花草叢的物象比喻女子用情深固而徒然為情所誤;深一層看,這也是詩人婉轉抒懷和反思:願復修初服而自褒其真,不再為榮祿之途賠上性命;出之以艷詞而已。青瑣,舊用法主要指宮門,代指朝廷;唐李頎《聽董大彈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全唐詩》卷一三三)「鳳凰池對青瑣門」是其例。很多學者認為「青瑣」代指富貴之家,沒有說到點上。俞平伯解作「宮門也」,而斷「此殆宮體詞也」,極是。芳菲,香花,可喻指美女,乃至賢臣。溫《陽春曲》(《全集》卷二)「廄馬何能嚙芳草,路人不敢隨流塵」;其中的「芳草」與此處的「芳菲」可同指賢臣。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漢書·元后傳》(卷九八)「赤墀青瑣」句孟康注),則「青瑣」句,寫青瑣門面對芳草之景,暗含宮廷中美女如雲,或朝廷中自多賢臣之意。所以下句說難以聽到再度得寵的消息,或 (自己)被起用的音訊,即「玉關音信稀」也。「玉關」不是玉門關,而也指宮門,代指朝廷。
話說回來,我們若把「青瑣」當成非帝王專有的「青漆塗連瑣花紋窗」,並直接把玉關解為玉門關,則解本詞為「悔教夫婿覓封侯」的遊春美女所思所見也不錯的。能從中悟出平常之情,也能悟出非常之情,這不僅是因讀者而異,也正是溫詞本身的特點。
其五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
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
玉鉤褰翠幕,妝淺舊眉薄。
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上闋寫夢境和夢的延申,都是昔日事。首二句寫夢境,杏花含露欲滴、飄香如麝、如雪之結團,如錦之成簇,與陌上楊柳依依、傷別頻頻的情景在此被詩人寫到一起。多離別,當然是這位女主人在夢中(在過去)與其夫君的哀別,在杏花盛開、綠柳成蔭的道路上告別。是作者以女子視角從「對面著筆」,寫杏花似雪,也是以樂景對比寫哀,所謂「綠楊(即楊柳)陌上」之「離別」,是傳統的寫法。而溫更隨境變用。
就晚唐文人語境而言,我們只憑杏花如雪和綠楊離別被放在一起,就可猜測頗有科舉失意的衷曲纏夾其中。這裡的杏花,和進士杏園宴有關,而可與科舉有關,溫《長安春晚》(《全集》卷六)「杏花落盡不歸去,江上東風吹柳絲」——通過杏花、柳絲抒發落第的惆悵。其《楊柳枝》八首之二(《全集》卷九)「南內牆東御路旁,預知春色柳絲黃。杏花未肯無情思,何事行人最斷腸」——亦有杏有柳。安知不是含蓄著自己對帝京的眷戀、對中第的渴望?
所以就溫創造意象的習慣言,本詞首二句寫女子之夢恐亦暗透了自己追求名第,卻屢屢落第而奔走陌路的逐臣情懷。溫《春日雨》(《全集》卷九)詩云「細雨濛濛入絳紗,湖亭寒食孟珠家。南朝漫自稱流品,宮體何曾為杏花」,也似乎給出了我們啟示。詩人說,那在南朝專寫孟珠之類題材的宮體詩,雖被稱為南朝的流品,但哪裏只是為杏花寫的呢?不正可以表明這首寫杏花而似宮體的詞有所寄意嗎?這是不是為我們理解他的《菩薩蠻》十四首之原意留的一條線索呢?溫自詡賢臣,而不能盡以美女之情抒其特殊懷抱,有時未免稍露自身行跡,直接把自己詩中寫仕途感慨的句子「代入」了他的宮體詩。正如「江上柳如煙」,聽任它與美女的形象相結合,有時難免令人感到文思阻隔。但從溫的身世經歷和寫作藝術求解,往往可生面別開,而達到美人和賢臣皆深刻的表達。
回到本詞上闋第三四句。應是拂曉時她醒來了。室內殘燈熒熒,室外殘月悠悠。大概因朦朧的殘夢太不如意,眼前之景竟是夢境的延伸,這時她居然聽到嚶嚶的鶯啼聲,那「出自幽谷,遷於喬木」的嚶嚶聲,遷鶯出谷的夢想,空幻地彌補杏花陌路的失落。夢境就和夢後之情融成一片了。
下闋首二句馬上又正面描寫這位女主角現在的行為和容止,是宮詞本色。只見她帶著宿妝緩緩地起身,用玉鉤打開窗帷。經過一宿多夢之睡,其「妝」自淺,眉額漫漶,也變「薄」了;這句話和第一首「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異曲同工,美人失意,故妝淺眉淡,也懶得去修飾了。末二句點出她的深情和她的春夢是如此息息相關,以至於鏡中雲鬢衰減。回想夜來春夢,正是平日所思,怎能不「關情」?那「關夢」的「春情」就女子而言,大概是思念她離別的對方。但這夢既關杏花曉鶯,應是長安杏園之夢,應是京郊離別之夢。失意女子只能夢想如意,對鏡理妝,但見蟬鬢稀疏,玉容憔悴。那夢境也似鏡中蟬鬢,輕忽飄渺了。「蟬鬢輕」和前句「舊眉薄」呼應,細緻地寫女子宿妝蟬鬢之美外,還帶有一抹衰颯的餘韻;所以應理解為:美人輕柔的雲鬢消減了。為什麼呢?那是春夢關情折磨的結果。春夢,是她的夢,還是詩人的夢,還是二夢本一夢?有時是分不清的。換言之,美人夢中之杏花離別、醒後之曉鶯等,雖然也似表達溫的妻子思夫之情,卻同時套印了一個溫庭筠之「思君」。
其六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
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
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首句有二讀,既可解為女主人公「長相憶」的對象是「玉樓明月」,也可解為她在「玉樓明月」中「長相憶」她的良人。那長久思憶的玉樓明月(宮中人,宮中月),是十四首一以貫之的豔思,其實象徵永遠難再圓的舊夢,含有永生難忘的思念和近於絕望的悲哀。「柳絲裊娜」句,柳絲諧音「留思」,看似景語,萬縷柳絲,隨風飄拂,與前句那有情的明月,流光中的玉樓,構成相思無望、柔腸寸斷的情語之具象表達,尤其「春」之「無力」之「春」字,更令人聯想到連無邊的春色也無濟於事,簡直是命運在主宰著這人間的悲劇。那相憶的對象,就是第四句中的「君」。
三四句,用《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意;《招隱》為淮南王門客悼懷劉安之作,這兩句尤就春草生而王孫不歸呼喚他、為他招魂,成為名句。六朝和唐代詩人引用雖頻,能切合原文所「憶」王孫之確切身份者頗寡;而多將詠唱的對方、有時把自己當成王孫。而溫此詞,是準確運用原典含義的。本詞中所言之君不但是女子稱其夫,也是臣子稱其君,而且是名副其實的「王孫」或「帝孫」,即莊恪太子李永,深含悼念莊恪太子之意。此處所謂「送君」,就不是送行,而是送喪了。姚合《莊恪太子輓詞》(《全唐詩》卷五○二)也有「淒涼望苑路,春草即應生」的句子。下文緊接的「聞馬嘶」之「馬」,就是送喪拉柩車的馬,也就是溫《莊恪太子輓歌詞》「霜郊賵馬悲」句中的「賵馬」。連「賵馬」也悲嘶,人自更加悲傷。這裡不只是寄託了對太子年幼遭受摧折的傷悼,也包含了作為一個侍從之近臣失去進身之階的悲苦。誰能想到這兩句竟然含有如此意蘊。
話說回來,若不知溫生平事,不知其中典故,或不考慮典故深意,只寫一個在連天萋萋春草中為丈夫送行的女子,不也是相當動人哀憐嗎?只是那女子就不是宮中女子了,更不像溫在《菩十四》別的篇章中寫的女子了。
下闋又轉寫醒後。「睹畫羅之翡翠,香燭代為流淚;憶綠窗之殘夢,子規應共銷魂」(徐沁君《溫詞蠡測》,見《國學月刊》第八期)。這是從純欣賞角度得出的感興,頗能表現原詞的情感深度。「畫羅」句,以女子眼前畫羅上金色成雙翡翠鳥反興其自悲不偶之懷;「香燭」句,意同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乾」,含有直以生命化為淚水的深沉悲哀。最後兩句,則是在「流水落花春去也」之時,興「望帝春心託杜鵑」之悲。溫《錦城曲》云「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也是用杜鵑那悲劇精靈的啼血哀鳴唱出自己的傷心舊夢。往事是舊夢,思之成新夢。夢斷,故謂之「殘」;思亂,故謂之「迷」。殘夢迷離,萬古春歸夢不歸,永遠地演繹著女子和士子的悲哀。所謂兒女之情和君臣之義就常常宿命地被悲劇永遠織在一起。
其七
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
明鏡照新妝,鬢輕雙臉長。
畫樓相望久,欄外垂絲柳。
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回。
上闋寫美人夢中或昔日的裝束行止。首二句,寫金線刺繡的一對鳳凰,配上仿佛方經一夜微雨滋潤的、嬌艷欲滴的牡丹,成一幅含蓄著鮮明對比的鳳凰牡丹圖。它繡在女主人公的新妝羅襦上。那金線編成的金鳳凰,似象徵高貴而被拘束、缺乏活力的婚姻。特別其中的牡丹微雨形象,有似梨花帶雨,暗示女子為情灑淚。三四句與第一首上闕「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可以相參。女主人公日思夜想的舊夢已非圓滿,寫她鬢輕臉瘦,其憂慮和煩惱自在不言中。下闕「畫樓」可有含典和不含典二讀。含典故,則指太子甲觀畫堂(見前),不含典,也指女子久久懷念之地或者居處。由此引出美人和賢臣的不同失意。她久久地佇立、向往、相望,欄杆外的絲絲垂柳也被她同化而為她深情搖曳。她「相望」的人在哪呢?曾在那畫樓之中,如今也事在人不在了。春社前的燕子已經雙雙飛回,但是有關畫樓的音信,卻一點也盼不到。女子所戀對象,其實已不在人間。大中之時,溫多方奔走,沿曾侍從太子一途而求官,或接「等第罷舉」之路而求第。所謂「音信不歸來」,當然也可暗指溫求官求第都毫無結果而已。
近人李冰若在評注《花間集》的《栩狀漫記》中說此詞「『雙臉長』之『長』,尤為醜惡。明鏡瑩然,一雙長臉,思之令人發笑。故此字點金成鐵,純為凑韻而已」。愚以為「雙臉」後所當用的字只需與前面的一個「妝」字押韻,作者能把一百韻的長律寫的妥妥貼貼,還不至於貧乏到找不定兩個都合適的押韻字的地步。所以「莊』和「長」字都是預設的。李冰若讀出「醜」來,自是一得,也是勉強合於作者原意的一得。美人不快樂時大概瘦些醜些,這很自然。如理解成「憂慮使她變得都不如原來美麗了」,這一點也不可笑。更談不上什麼「醜惡」。
其八
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
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
翠鈿金壓臉,寂寞香閨掩。
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
上闋說昔日之夢(或事),首二句則是夢中之夢。那時牡丹花凋謝已盡,能報喜的黃鶯鳴聲也早已停歇。景中藏著事。這顯示春天已過去。牡丹花凋謝,謂標志侍從莊恪事的「牡丹時」(第三首)已經結束。「鶯聲歇」,既可謂春天的歌聲已停止,也可謂有關中第與否的消息再無下文,即得「等第」之後的努力都是徒然,只得接受「罷舉」的不公平。那滿院的綠楊,昭示的已不同於「綠楊陌上多離別」(第五首,表奔波道路、舊夢惜別),也不是「欄外垂絲柳」(第七首,重複和加強久久相思相望),也與「柳絲裊娜春無力」(第六首,表命運不助、近於絕望的相思)不同,而暗示歲華漸晚。中庭見月,則是夜不成眠所致。所以三四句接言她追憶當年舊夢,而不能入睡成夢,面對窗前孤燈熒熒,被思念所折磨;這是求夢不得、醒不如夢的無限悵惘。下闕又回寫到眼前,寫女主人公此時對此夢的感受。她雖金釵翠鈿,孤芳自賞,卻閉門自處,香閨寂寞,縱有國色天香,奈無人欣賞何。這直接啟示一個懷才不遇的士子不能事君。末二句寫相憶之苦,懷念遠人,珠淚闌干,不覺燕子又歸去,春天又凋殘,她只能年復一年讓青春虛度。景中藏情,因而敘事,說到情濃處,又歸結於景。情景之交融,無以復加。這和《離騷》之敘事寫景的無痕交替,確實可以相比。
其九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
金雁一雙飛,淚痕沾繡衣。
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曲。
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
上闋用含情之景所暗示的宮中舊夢,引出女主人公的孤獨和悲傷。首句謂明月銀光遍灑宮苑中,月光之下本來盛開的梨花更顯得一片慘白;這是女主人公心頭抹不掉的舊夢,「梨」諧音「離」,明月梨花中深含別離之悲。第二句則說到女主人公本人此時的慘境:她是故人,是宮中舊人,已與那「雲陣」的往事、哪怕相當凄慘的往事,萬里關山相隔,完全沒有聯繫了。三四句說,她的繡衣上徒然有金絲織就的一雙金雁雙飛雙舞,映襯她的孤獨,如今這繡衣只好用來沾滿眼淚,那是孤獨的單相思之淚、永離別之淚、思君之淚,絕望的被棄捐之淚。或解「金雁」為箏柱、書信,皆越說越遠了;直接將「金雁」句解為一雙大雁各自分飛,應更好。「金」字,與「金梭」略同,美稱之而已,與前文「白」、後文「綠」色彩相映。
下闕自報家門,先說家中小園芳草正綠,映襯她的盛年蕭瑟;然後說她像西施一樣是越溪美女,天生麗質,而且兼備修能。如此美女,得不到服侍君王的機會。那依依不捨的楊柳色,也是他萬難割捨的忠悃之情。當此青春之季,年年歸來的燕子又歸來了,但是「君」卻不回來啊。那「君」是誰呢?如果看作一般的閨閣詩,也該是離開了她、曾經寵愛她、賞識她的夫君!可這夫君是宮中的夫君啊!對溫來說,是信任他、提拔他的「君王」啊。有的論者為了證明這不是宮體,不嫌麻煩地證明「宮」其實和一般的民居沒有什麼區別。這是故意避免可能導致「寄託」主旨的讀法,也可理解。無論場景怎樣變換,還是「外託男女眷戀之貌,內寄感士不遇之情」(張以仁:《溫飛卿詞舊說商榷》,《台大中文學報》,1989年12月)。本詞首句同於與溫《舞衣曲》,它們之間有什麼聯繫呢?茲附原詩簡解。讀者可從中得出結論。
藕腸纖縷抽輕春,煙機漠漠嬌蛾嚬。
金梭淅瀝透空薄,翦落鮫綃吹斷雲。
張家公子夜聞雨,夜向蘭堂思楚舞。
蟬衫麟帶壓愁香,偷得黃鶯鎖金縷。
管含蘭氣嬌語悲,檀槽雪腕鴛鴦絲。
芙蓉力弱應難定,楊柳風多不自持
迴嚬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脈脈。
不逐秦王卷象床,滿樓明月梨花白。
原詩語言極端精美含蓄深情細膩。我們只能先把全詩意象內容簡陋地加以復述,再解釋。
首四句以浸透深情的語言寫女子抽絲、織錦、裁成舞衣的過程。尤首句以藕(偶)腸謂蠶繭,以輕春謂情絲(思),簡直把從蠶繭抽絲寫成了從愛人心中引出細密深情。第二句在織機旋轉迷離的視覺中讓織者蛾眉漫顰而亮相。三四句則寫金梭來回穿行在透明輕薄的絲縷間而織成錦綃,然後吹斷彩雲一樣剪斷輕柔的鮫綃,織成華貴的舞衣。五六句寫張公子夜聞風雨之聲,而當夜急急來到蘭堂想觀楚舞、聽楚歌。這時她穿上親製舞衣翩然起舞了,那薄如蟬翼的輕杉、那連綴的玉刻麒麟腰帶,竟使她纖細含愁的香軀不勝負荷。而那伴舞的歌聲,竟似把黃鶯在金色柳絲中的囀鳴偷借而來。她吹簫徐吐的蘭氣,化成柔軟嫵媚而含情的嬌音。她彈琴的雪白手腕輕輕飛揚,在鴛鴦絲上奏出柔腸萬轉的情曲。她輕移玉步,裊娜的風姿,如出水芙蓉,無力自定,她斜倚腰身,如迎風楊柳,難以自持。她對「西窗客」只能回顰淺笑,稍稍致意,河星寥寥,她亦神情黯然,欲言又止。因為她不能服侍秦王,為他「卷象床」。滿樓明月照耀著滿院梨花,無限凄艷襯託她深沉的悲哀。
所謂「張家公子」,即《漢書·五行志》(卷二七)「張公子,時相見」中之「張公子」,富平侯張放也。據《漢書·張湯傳》,放父駙馬都尉張臨,母敬武公主;放與漢成帝臥起,從帝微服出遊。溫之祖父溫西華是唐宗室女婿(其父也很可能是),與張放很類似,故以張自謂;而溫曾侍從莊恪太子,而與之保持過一段親密而客氣的關係,故有「西窗客」身份。「張家公子」二句,非常罕見地不是因疊字而重用兩個「夜」字,顯示當時情勢相當緊張。所謂「蘭堂」者,可指御史臺,此處則指「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下某處官署。而「思楚舞」者,則真的用劉邦謂戚夫人「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之言的語境和語義;它歇後式揭示了「吾為若楚歌」的憂慮,即劉邦對戚夫人求其子趙王如意做太子的擔憂,在此移作詩人對莊恪太子位置難保的憂慮。從章法上講,「思楚舞」把本詩前四句舞衣之製和下文緊接的六句歌舞表演無痕銜接起來了。最後四句,夜闌更深,歌舞已罷。「不逐秦王卷象床」一語,包含深深的失望。李世民武德元年尚非太子時封秦王,此用來暗指位置不穩的莊恪太子。這位以生命的熱情和忠誠裁就舞衣,妙舞婀娜,清唱如鶯,管吹芝蘭之呢喃,手撩鴛鴦之情絲,而準備全身心奉獻君王的舞者,竟然被剝奪了服飾「秦王」的機會。她怎能不失落和茫然呢?所以說,末句「滿樓明月梨花白」的情中之景,含蓄著無限凄艷的深沉悲哀。
《唐語林·企羡》(卷四)「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遂罷其選。」文宗雖曾想為太子選妃,先因太子尚幼,未急其事。至開成二年楊賢妃受封後,極力誣譖,形勢對王德妃和莊恪太子越來越不利。我們猜測,詩中的舞者,是莊恪太子侍從宮女中色藝兼備的佼佼者,能歌善舞,兼擅絲竹,一度有被選為太子妃的希望。由於種種原因,其事未成。溫庭筠很賞識和同情這位女子,因為她精製舞衣,又色藝俱佳、志在忠心服侍君王,與溫本人苦學成器、忠誠唐庭,頗有可比之處。可惜她生命的全部內美和修能,也如那美輪美奐的舞衣一樣,幾乎沒用派上用場就被閒置了。此詩未嘗沒有以舞衣比舞女,又以舞女自比之旨。
其十
寶函鈿雀金鸂鶒,沉香閣上吳山碧。
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
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
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
上闋寫女主人公弄妝沉香閣、情語景語中引出她多年苦苦相思的情結。
首二句,描寫女主人公打開華貴的妝奩(鏡匣)正梳妝,鏡匣上閃光的一對「金鸂鶒」如第一首的「金鷓鴣」一樣反襯她的孤獨。她所居的沉香閣,窗前是碧綠的吳山。沉香閣在此不指宮中樓閣,「沉香」之名,暗示她香玉沉淪(賢人失位)的處境。而「吳山」其實正指下文「她」所在的「江南」;「吳山碧」之「碧」自是山水春風之境,除引出下文的迷人春色外,也與她的玉容寂寞形成鮮明對比。「楊柳」句,言眼前柳絲經雨、柔條曼垂,含蓄了多少相思,尤其「又」字,可謂一年又一年,生命就在這樣悲苦的相思中走向凋殘。和第四句「驛橋春雨時」合起來講,對其意大致是,年復一年,又到了楊柳垂絲的季節,她所懷念的他依然奔波道路,小橋旁專司傳遞信件的驛站在無邊的春雨中,也沒送來任何消息。
這第四句,作為女子之思慕的具象表達,即使看作「從對面著筆」,也不甚恰切,蓋思婦之於「驛橋春雨」,必無如沐其濕、如過其橋之切身感覺也;「驛橋」也不是她剛好望窗外就看到的。前人已指出,它與第二首」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一樣,「皆晚唐詩之格調也」(浦江清《詞的講解》)。愚以為,單說它有似於「江上」二句是對的;說它是「晚唐詩格調」、甚或溫詩格調,卻未解釋其意,可見它在上下文中之意難解。其實,它是溫本人羈旅詩的一種語境:奔波道路,常居驛站,消息不來,愁思無限。用移花接木之法置於美人的所見所思範圍。以詩人感思代替了女子感思,間接讓美女所喻的詩人稍露真容。
下闕隱約暗示其情之所自來及其真正的性質。前兩句謂自從畫樓(應是太子甲觀畫堂的暗語)的音信斷掉以後,芳草只能在江南岸凄凄生長。那江南岸的芳草,引人遐想,可以引起對「王孫」的懷念,也可喻美女,喻賢人。那她畢竟是被從宮中放逐出來的美女?還是曾經一睹青雲,卻又流落江湖的詩人?二者各有其宜。從末二句面對鸞鏡的花枝,容易想見,她如「顧影悲同契」(《藝術類聚》卷九十范泰《鸞鳥詩〉)的孤鸞之對鏡,直欲「終宵奮舞而絕」,那是失去了她全部身心的依託、或者是失去了生命的另一半的悲傷啊!「鸞鏡」的悲哀故事,有極強烈的情感內涵:除表明了女主人公之盛年喪偶、悲哀欲絕,還以她的孤影自弔表明了她相思對方的不幸死亡,斷絕了她的繁華舊夢。這種絕望而孤獨的斷腸相思之苦,有誰理解呢?此情此悲,是那種生死相託的帶有濃重悲劇意味的愛之失落。溫是個真正敢愛能愛的人。他能真實而始終如一地愛一個身份遠比他低的妓女,他更能忠誠而矢志不渝盡心於與他身家性命相連的李唐王朝。他能寫出諸多愛得深沉、被愛拋棄而仍堅守其愛的美女之儀態、之深情,之靈魂,除了現實生活中對女性美之深刻而客觀的觀察外,全因他本性中深植的真摯與忠誠。這應該不是過譽的話。
其十一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
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
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
上闋由醒後眼前之景,聯想到她的夢。一霎清明雨後,兼之以風,柳絮滿地,杏花零落。花殘絮落,是春風春雨催成,總是風狂雨驟、摧花斷柳的破壞,所以女子醒後為之發愁。雨後又返晴,斜陽映照著雨洗過的有些殘敗的杏花。詩人借他筆下女子的感覺,把他詩的鏡頭聚焦在雖然零落殘敗而仍然散發清香的杏花上。從女子角度來說,她是在傷春惜春,春柳春花,牽動著她敏感的愁腸,未嘗不是在感嘆她的青春虛度。詩人借此傳達的用意,是他本人經過一場考試風波,雖然不得中第,但毀譽參半,在瞭解他的人心中,畢竟留下了美名。下闕則簡明地回到眼前,重新化妝或者補妝。想想前因後果真覺得毫無意趣。她不說「天色欲黃昏」,而偏說「時節欲黃昏」。可見「她」有點老了。「他」也差不多快成糟老頭子了。假設《菩十四》作於大中中(大中八年,854),他已57歲。「無聊獨倚門」的形象不是很漂亮。往好處理解,這大概是《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之意。
其十二
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
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妝。
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
花落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這首是十四首中唯一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光澤的。藝術上也平平。蓋因情景不能相富,故無可稱道也。寫一個寡居富貴女子,夜深難寐。她大概看到那光透簾幕的中天之月,簾內無人與之言,她很孤獨。滿屋子麝香煙氣,也不能治失眠。她就寢時是否卸妝也無人理會。她當年甚為珍重自己,許多往事都不堪回首了,如今就像萎謝的花無人過問、凋殘的月無人瞻望,獨宿空房,獨暖冷被,領略寒冷的孤獨。能使這首詞有資格和其他諸首一樣獨立存在於十四首之中的唯一原因是她「哪堪憶」的「往事」,一旦揭曉,當是她的宮中經歷,或曰「涉帝婚姻」。
其十三
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褭紅絲拂。
閑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
繡簾垂籙簌,眉黛遠山綠。
春水渡溪橋,憑欄魂欲銷。
上闋寫雨後夜合之美而引出昔日」金堂「之夢的旖旎情境。從「閑夢憶金堂」看,首二句應是女主人「情思睡昏昏」時所見之景。一場澍雨過後,夜合花在日光下盛開得玲瓏剔透,千萬枝紅花香氣裊裊,花蕊也在微風中飄拂。眼前美麗花開之象,刺激她憶起當年在「金堂」的情景,那時滿院萱草欣欣向榮,長得好茂盛啊。
「萱草」,又名忘憂草,又名宜男草。《詩·伯兮》「焉得萱草,言樹之北」;《毛傳》「萱草令人忘憂」。《藝文類聚》卷八一周處《風土記》「宜南草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萱草作為一種香花,在歷代詩人筆下積累了豐富的內涵,由上古時植於母親所居的北堂之前,其物象有思母、忘憂的含義;為后妃佩戴,取其宜生男而母子安康之意。此處把夜合(合歡)與萱草相連提到,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萱草又名宜男草,還有更具體的文化內涵。晉夏侯湛《宜男花賦》「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廷」就特別提到「萱草」,此處「滿庭萱草長」也可以有多層祝願,包括是否可使莊恪母王德妃「忘憂」,能否「宜」莊恪之「男」。可以肯定,「閒夢」二句暗示的是女主人公(作者)追念昔日在宮中侍奉太子的日子,反映其時的所望和所憂。溫《生禖屏風歌》「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桃千子紅」句亦稱此草,二句蓋有所指。詹安泰《讀夏承燾溫飛卿繫年》曾提到溫侍從莊恪太子事,他舉出的例證之一就是上述二句,並說「宜男之草竟不似櫻桃千子紅,這不正是說莊恪太子還不如諸子嗎?」詹先生的猜測方向是對的。但他把「宜男草」直接當作代替太子的一種物象了。從字面說,上引二句似可大致解作,後庭空有宜男草,卻不能宜太子,更談不上櫻桃多子多福了。
下闕「繡簾垂籙簌,眉黛遠山綠」顯然文思跳躍。這位女子掀開隔斷她與外邊世界的、低垂的繡簾,乃蹙如遠山之翠眉,而望如眉翠之遠山。人美,或山美?相得而益彰、相形而益美也。而春水溢漲,淹過了溪上小橋之景,也使憑欄眺望時的她為之銷魂。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趙兮千里」。可為這位美人之銷魂做注。尤其「況秦吳兮絕國」有巧合似的針對性。
其十四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
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
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
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上闋,言女子夜不思寐,帶著濃妝倚在繪有金鳳凰的綠色檀枕之上,她身感庭除間竹風輕動之微寒,欣賞珠簾外月影徘徊之玲瓏。一如既往,言「綠檀」、言「金」、言「珠」,不是珠光寶氣的俗艷,而是「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的高貴。下闕,兩蛾,即兩道彎細蛾眉。黛即畫眉之黛色顏料,愁黛者,謂緊蹙的畫黛之愁眉,因以「黛」畫眉,乃以「黛」代眉也。淺,謂淡掃蛾眉,形其天生麗質、淡妝之美也。「故國吳宮遠」句,有二解。若以其「故國」與「吳宮」遠相隔,而謂此女子在吳宮中思念故國越地,則成宮人思鄉之宮詞,雖有道理,歷來未見宮女思鄉之作也,溫也不至於在此處別開生面。若以「故國吳宮」為主語,「遠」為謂語,則此女子乃吳宮之妃,直以吳宮為其故國而懷之念之也;為吳宮之妃,當然是可為為唐室之臣的比喻。末二句言「春恨正關情」,而不是「春夢正關情」(第五首),正可見這位女子所「關情」者,是醒而不能自已的春恨、是「寐」而不能自已的春夢。那關情的春恨,使她徹夜不眠;所以她聽到來自畫樓的殘點之聲。如前所言,這畫樓,原來是畫堂的一種飾語。那畫堂舊夢,已經永遠失去,能夠聽到關於它的殘點之聲,也算幸運了。
(本文旨在揭開溫氏一生奧秘,引文隨文注明出處,不再立注。請參作者以下舊文)
《溫庭筠生年新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一期。
《關於溫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證和說明》,同上,1985年第二期。
《溫庭筠從遊莊恪太子考論》,《唐代文學研究》,1988年第一輯。
《溫庭筠改名案詳審》,《文史》,1994年第1輯(總第38輯)。
《溫庭筠江淮受辱始末考》,《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1期。
《溫庭筠<百韻>詩考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5年第2期。
《溫庭筠改名補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6年第1期。
(续完)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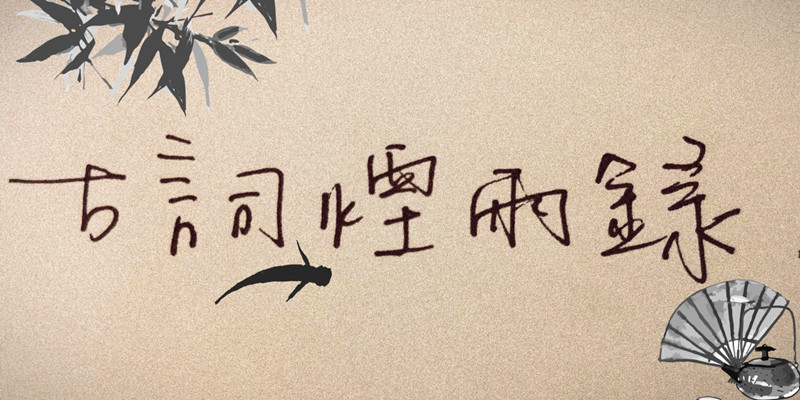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