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
1950年,我7岁时从青岛乘汽车来到掖县,这是我第一次回故乡,是代父母行孝,陪伴早已先回老家的祖父祖母。记得母亲与妹妹坐上长途汽车返回青岛时,我却被爷爷从车上强行扯抱下来,我拼命地挣扎着,嚎叫着,撕扯着……但全然无用。我不记得母亲是如何伤心,妹妹是如何惊骇,爷爷是如何粗暴,只记得自己痛苦地乞求和绝望地呼号,只记得回村时正逢暴风骤雨,一声通天贯地的大霹雳惊心震魄,我那时就认为这是人怨引起了天怒,因为我那时实在太小太小了。我记忆中苦日子从此便开始了,那是我们祖孙相依为命的悲苦凄凉的日子。苦难的童年,永生难忘。
我的老家是掖县城北五里路的西郎子埠史家村。掖县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历史悠久,古称莱州,亦称光州,6000多年前即有人类聚居。夏称莱地,商称莱侯国,周属莱子国,汉高祖置掖县,南北朝称光州,隋唐称莱州,明洪武元年升莱州为府,清朝延续称府,民国时期废府留县,现在又改回莱州市了。其实青岛地区在古代就归莱州管辖,有史书可鉴。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穷困而无聊,对一个刚从城市来的幼儿来说更难适应。
那时我们家土改定成分为富农,没被分田,也没挨斗,爷爷分家原有的六亩零八厘二毫地仍归自己耕种,那块土地是村西的涝坡地,土质很好,还有一口水井。家中房屋地基一亩零九厘四毫,瓦房11间,还有甜水井一眼,王瑞琪县长签发的土地证上还有我史在新的鼎鼎大名呢。当年的土地证现已随卖房契约转到董维正手中,那是1989年1月10日我代表父亲回乡办理的卖房手续,18300元的房款,父母给我们长子长孙各500元。16000元归母亲所有,80年代的母亲瞬间成了万元户,可是老家房产却从此归零。
当年我和爷爷这一老一小,就待在这所庭院打坷垃种地,推磨压碾,一年365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苦生活,不亲身经历是绝对无法体会到的。
春
春耕从正月下旬就开始了,因无牲口和耕地农具,农户大都请人代耕代种,但整地送粪就完全是自己家干。我在车前拉,爷爷在车后推,虽然木头独轮车十分笨重,在我国有九百年历史了,两手推起来还咿咿呀呀作响,枣木车轴还要不断更换上油,但当年的村子里仅有三五辆,大忙季节还是别人家羡慕的对象呢!这要比肩挑背抗效率高很多,比雇驴驮、雇车拉要省钱省人手。后来我家与三奶奶家合养一头小黑牛,随年龄的增长,每天放牛、割草都是我的工作,我那时还没有牛高,根本没有“牧牛图”骑在牛背上的潇洒,顶多踩着田垄趴在牛背上跑跑算是享受。
在地里耕种时,牵牛、上套、卸套天经地义分配给我做。再大一点,家中推磨箩面的活也完全成了我的份内工作,蒙着眼睛的牛拉着石磨走走停停,我在一旁单调地用不同的面箩筛出各种等级的面粉。头拨、大麸、二麸、黑面,磨出四个类别,不同的节日才能吃上不同的面粉,平时能吃到玉米面、高粱面就很不错了。总之,我与那头慢吞吞的黑母牛有了不解之缘,可能我性格的倔犟不屈,做事有板有眼慢条斯理,都与牛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然而后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将黑牛归公了,我始终惦念的这头牛不知所踪。
端午节前后是麦收季节,虽然不及三秋大忙,可劳动强度也很大,因为农民一年吃的精粮全靠麦收。为了留烧草,不用镰刀割,而是用手拔麦子,你想想有多苦多累?凌晨下地,土地尚湿软,为了颗粒还家,农民的手全是血口子。人背肩扛车运回家后,铡下麦穗打场收麦子,铡下麦秸好掐草辫,留下麦根为了烧火做饭,庄稼人珍惜点点滴滴的劳动果实。
单干的岁月里,我理所当然地参入劳动全过程,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老巴子。
夏
炎热的夏天是农民最辛苦的季节,每天顶着烈日下地间苗、锄草、打垄、浇地……经常被太阳晒得头昏脑胀。锄地最起码要锄到田间地头方可休息,现在看来十丈八丈远的田边并不算长,可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就像马拉松一样遥远,那时能在井旁的柳阴下歇歇,能在路边牌坊的基石上坐坐,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地南头的石牌坊从上到下都是汉白玉雕成,听爷爷说是为褒奖祖上的一位寡妇而建的贞节牌坊,后来查家谱得知,她是高曾祖的三弟史仙灵的遗孀。现在牌坊早已被毁坏,而家谱也无人再续写了,史家的这段历史即将灰飞烟灭。
农田里的劳作,我最喜欢浇地看水头了,撑着铁锨可以站半天,看看白色的浮云和绿色的庄稼,出不多少力气,只是铲土改改水道而已。不过万一不留神跑了水那就坏事了,立刻引来爷爷如雷贯耳的训斥,但孩子总归是孩子,免不了找理由申辩一下,可日久天长只能忍受,幸而爷爷也能体谅八九岁的孙子,心情好时一般不发脾气。那时在井上挽水浇地可是个力气活,一水斗能盛两桶水,挽上一斗水,轳轳把柄要转上十几圈,连续挽上几十斗水才可休息,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当然有钱人家能在水井上安装铁皮水车,由牲口转圈拉水,省力多了。十多岁时我可以站对面帮助挽轳轳把子了,有时单独向下放空水斗,可无论如何也不能独立挽一斗水上来。除了爷爷挽水外,大多数要请邻居史品先老二爷帮忙,他当年身强力壮,年龄比我爷爷小,辈份却比爷爷高,铁脚板能将干蒺藜碾得粉碎。他挽水浇地时呼喊的嘹亮号子声,在田野上久久荡漾,至今仿佛仍在我耳边回旋。可晚年的他脊背驼成弓型,腰弯得头快接触到地面了,看来与年轻劳累过度大有关系。我代父回老家卖房子时,送给他100元钱,那是我与这贫协主任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年轻时挖坟盗墓捞外快,却被久病的老婆和患精神病的女儿拖累了一生,乡邻都说这是上天的报应。
夏天的夜晚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最头痛最烦人的是那些碰头碰脸的蚊子,每日傍晚在房门口聚集成球,房间里要用艾蒿点烟熏蚊,可往往蚊子赶不跑而我们的眼睛却被熏红了,因为窗户是死的,有时为了通风只得将糊好的窗纸撕掉。劳累了一天的祖孙俩,吃过晚饭后已经是满天星斗,我们一起到村头的土墩上乘凉,和乡邻们天南海北说古论今。或拿芭蕉扇在自家院中谈天说地,爷俩一起依偎在藤躺椅上休息。个人的经历,家族的兴衰,乡间的传说,邻里的趣闻……多少个仲夏之夜,我都是在天方夜谭之中进入梦乡的,而醒来时,朝阳早已照进了灰黑色的蚊帐之中,我是在睡梦中被爷爷抱到土炕席子上的。
秋
秋季虽然是收获季节,但也是农民一年中最紧张最劳累的日夜,我童年就有切身体会。家家户户投入三秋大忙,我自然也要干不能再多的活计:掰玉米棒、割高梁头,皮肤被钢丝锯似的叶子划出条条红斑;拉车、牵牲口,推空车,晚间累得手脚抽筋发麻;打场、晒粮、垒垛……我们的工作从天亮到漆黑,难得休息片刻。一开始对牵牲口打场很感兴趣,以我为圆心,牵着捂眼的牛或驴不停转圈子而已,可转一段时间就单调无聊了,头顶烈日,时不时还得侍候牲口的屙和尿,石碌碡在谷穗或豆秸上飞滚,我却转着转着头昏眼花。
秋收麦收都是这样,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太阳越毒越要干活,要想颗粒还仓,必须抢在阴雨天之前。爷爷平时对我很是疼爱,尽量让我干轻活,少受太阳的曝晒,不过天气一变他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焦急吆喝训斥声并不亚于天上的轰轰雷鸣。
秋收的累,远远胜不过秋雨的愁,秋天连绵不断的阴雨,让我们日夜提心吊胆,常常是北墙倒了南墙塌,五间北堂屋也是八处漏雨,夜不敢寐。虽然我们家住的是瓦屋,却和杜甫的草堂没多少区别,所以中学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我的体会恐怕是最最深刻的,至今仍能朗朗背诵“雨脚如麻未断绝”。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绵绵秋雨中,深更半夜经常神经质似地爬起身来躲到南屋,唯恐北屋房倒屋塌死伤其中,待到天亮瞧瞧无恙,又后悔夜间虚惊了一场,再卷起铺盖回到北屋。
大雨过后总要垒墙,爷爷站在凳子上是瓦工,我理所当然是小工,打水和泥,搬石递瓦都是我的活。不过修墙的工作往往是徒劳无功,下一场大雨又会淋塌,因为省钱不买砖和石灰,全用捡来的碎石头和农闲时拖的土坯垒墙,哪里能抵抗风摧雨刷呢。哪如人家贫协主任的墙是用盗墓的坟砖垒成,不怕暴风骤雨。老家败瓦颓墙的雨后场景,至今还偶在梦中出现,可见幼年印象之深之牢。不过这段生活也锻炼了我,大学毕业我和妻子分配在公社医院,我在草屋宿舍旁用碎砖石独立盖过厨房,垒过鸡窝三层楼,房间里还扎过顶棚,修过带烟囱的炉灶。医学院的大学生还能当泥瓦匠?我多面手的表现,令医院同事及贫下中农们刮目相看。
农村要说全无欢乐也不对,中秋节还是满喜乐的,每年八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全村沸腾,尤其是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圆月啦,圆月啦,一亩麦子打担啦!”“圆糕啦,圆糕啦,一年就这一遭啦!”,此起彼伏噪杂的圆月声,肯定能传至月亮广寒宫中。月糕是庆祝中秋节的面制品,圆形有大有小,我每年也照例举着姥娘或舅姥娘精心蒸做的月糕圆月,不过我不和其他孩子们一块疯狂地呼喊,而是独自对月遐想,什么嫦娥奔月啦、什么玉兔捣药啦、什么吴刚砍树啦……当然每逢佳节自然也会想念远在青岛的母亲,在银白世界里偷偷流泪,深刻体会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我那时毕竟太小太小,身心都十分脆弱,实在缺少母爱的抚慰。
冬
农村的冬天最难熬,寒冷和寂寞像两具刑具牢牢铐在你身上,使你失去了任何生活乐趣。我每年都要冻手、冻脚、冻耳朵,虽然穿着蒲苇编的木底草靴,胶东俗称“嘎哒子”,走起路来“嘎哒嘎哒”响声一片,可两脚照冻不误。有时脚烂得无法走路,于是爷爷就对我精心治疗和护理,拿出几十年前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冻疮膏,认真为我涂抹和包扎,遗憾的是却全无效果。洋法不行用土法,在大雪天扫出一块空地,扣一竹筛支上木棍,筛下撒些米粒,木棍系一细绳躲在门后静候,这样很容易就捉到雪天觅食的麻雀,然后用麻雀脑浆涂在冻伤处。可悲的是土洋两法仍不管用,冻伤继续溃烂,致使左右两脚的趾甲剥脱变形,现在仍给我留下了溃烂的永久性标记。
在三九严冬,房子里到处透风,薄薄的窗纸难阻寒气,纸糊的天棚吱吱作响,小油灯在屋内也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在这漫漫长夜中,爷爷和我在火盆旁搓苞米棒子,或掐麦秸草辫打发时光,搓累了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那时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甚至连最简单的收音机都没有,爷爷顶多唱几句“愁愁闷闷唱支歌……”,或讲讲曾经看过的旧电影,次数最多的是《麻风女》,百讲不烦。而我的休憩就是看闲书,祖辈留下的《说岳全传》《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章回小说,繁体竖行,基本都是文言文,看不懂的就连猜带蒙,不过对我却是一种启蒙,这可能是我对文学和历史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吧。冬夜读书是看不多久的,因为耐不了寒冷,受不了昏暗,需要赶快钻进被窝里取暖,然而“布衾多年冷似铁”,只有困极乏极时方能入睡。在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季,因为珍惜烧柴,家家土坑难以烧热。因为被褥多年陈旧,我穿的是老爷爷的棉马褂,你想哪能御寒保暖?我们祖孙整日冻得麻木僵冷,生活哪有什么乐趣?那个年月根本谈不上未来,更不用说什么理想了,这真应了一句农村的老话——糊里糊涂混日子而已。
冬季的漫漫长夜中,农闲无事总要干点事,俗话说“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阶级斗争就要占用这段时间,就要对地主富农开会训话,从精神上到肉体上不让你闲着,这种会议一开就是大半夜,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个个心惊胆颤,家人自然也都跟着提心吊胆。
每晚爷爷临走前总得把我安顿好,大门、中门、房门上三道门栓,可爷爷不在身边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院子里呼号的朔风夹带着野猫的吼叫;纸糊的天棚上活跃的老鼠来来回回穿梭蹦跳;西套间内患病的奶奶整夜念念叨叨、刀杖乱敲;老式房门被狂风吹得咣咣乱响……孤苦零丁的我,既不敢熄灭摇曳的灯,使自己沉溺于黑暗之中,又牵挂着深夜不归的爷爷,只能躺在冰凉的被窝里,紧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着古代的章回小说,体会着现代的苦难生活。《二十四孝》中有个能温席的香九龄,我有时也跟他学习,躺在爷爷的被窝里为他暖被,可多少次都昏昏睡去。每当爷爷回家见到熟睡的小孙子时,往往不忍叫醒我,而是感动万分,自己悄悄睡到我那冰冷的被子里。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每当爷爷受到训斥侮辱,自尊心遭到戳伤而碰头顿足、痛不欲生、萌生自杀念头的时候,是我给予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赤子火热的爱心,复苏了爷爷那僵冷了的灵魂,是我延续了他的生命,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爷爷93岁的长寿之身。
原载轻博客12/19/2019 10:42:40 PM
史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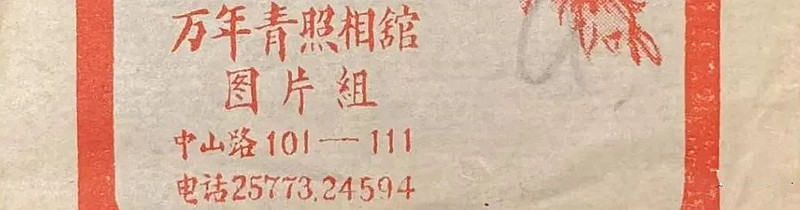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