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海瑞罢官》
1959年,是马连良艺术创作的丰收之年,这一年他创排了晚年代表作《赵氏孤儿》,有人认为这部戏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媲美。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号召学习明朝大臣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并建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话转告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让其撰写文章。吴晗于1959年6月和9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时任北京京剧团团长的马连良看到文章后,约请吴晗撰写有关海瑞的京剧剧本,1960年底剧本完成,定名《海瑞罢官》。1961年1月,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首演该剧,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中约见了马连良,并称赞:“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得知后非常高兴。
1962年3月上旬,江青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完《海瑞罢官》后,指示停演,并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部长、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谈话,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借古讽今、影射现实,要对该剧进行批判。但江青的要求并未得到回应。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在江青的指示下,姚文元的文章将《海瑞罢官》中海瑞“退田”“平冤狱”的内容与1962年以来受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将该剧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将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接着,文艺界、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狂潮。戏台上的事,马连良看得通透。但戏台下的革命、政治,他就一窍不通了。紧跟半天还是跟不上趟儿。他成功出演《海瑞罢官》,却被卷进了政治漩涡而招致灭顶之灾。
据马连良先生的义子王吟秋回忆:1966年6月4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出现代戏《年年有余》。马连良化好装后,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子。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完啦!”这让站在一旁的义子王吟秋很纳闷。原来是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说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是大毒草。马连良听到这个消息,怎能不联想到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南周北马,一个演《海瑞上疏》,一个演《海瑞罢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反党。马连良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果然,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剧团就有人在中和剧院给马连良贴出大字报。但马连良想不明白,《海瑞罢官》怎么就成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了”?1961年公演后,不是还受到了最高领导的赞赏,请进中南海吃饭,当面受到表扬,这才几年?
黄世骧先生以亲身经历写了十余篇微博回忆马连良最后的岁月。他写道:
“我以自己的良心告诉大家一些真实的事情,只说我亲眼见的,一些细节就是马先生的亲属都不知道。”
“对马先生的崇拜可能有点过头,就是他最悲惨最倒霉的时候,我看他哪一点也是美的。他扫地我看着美,他擦椅子也美。有一次他满脸胡子渣,头发松乱,手里端个小盆拿着抹布擦中和舞台的前沿,他那一步一颤哆哆嗦嗦的形象,我心里惊叹,天啊!这不就是张元秀吗?朋友们,我这可不是调侃,我是流着泪在写。马先生在‘中和’扫地,我过去和他说: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他说凑合着吧,我说吃饭怎么样?他说:家里给送点儿来,这儿能吃什么就吃点儿什么,我说别害怕,过些日子就好了,他说:唉唉,你回家替我都问好呵。我想说谢谢您,却没有说出口,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不礼貌,也是我欠马先生一辈子的一句话。”
“一次上班在‘中和’门口,我远远地看见了马先生。他在大栅栏东口下了三轮,一身秋冬装非常利落,上身好像是一件中式对襟,就跟舞台上的那行头一样漂亮,他左手腕上搭着一件皮领子大衣,小心翼翼急步快走进了大门。看得出他紧张怕叫人看见。也看得出他精神不错。我当时觉得他好像长个儿了。这闪亮一现,是马先生留给我最后的一个最美最酷最精神最漂亮的镜头。他穿着可能是要回来的也许是劫后残留下的衣装,他脸上有了些红润,走路也显得健壮了。想不到他没有熬过这个严冬,他没有看到春天,几天后团里面出现了一张抄录某人讲话的大字报。他就是看了这个讲话之后,再没来上班。”
1966年8月份“破四旧”,抄家打人已是常事。马先生家被红卫兵屡次洗劫。据说一次抄家后,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但据黄世襄先生说,二团只有五位红卫兵(珍贵稀缺),未做过抄家事。大串连时,某大城市京剧院的造反派赴北京来到二团,要见见和揪斗马先生,领头儿的那人在样板戏里有角色,咱就不提是谁了,结果给看了看却坚决不许揪斗。理由吗?马是我们团的,不用别人斗。
他甚至还回忆了马连良最后的一点逍遥,“一九六六年入冬以后,运动的矛头此时已不在马先生这些死老虎身上了。他们的日子也轻松好过一些了。马先生也不干活儿劳动了,身体精神都恢复了很多,每天上班来下班走,他不能和革命群众在一块,只和二团已靠边站的副团长尹君彦俩人凑在一块,在一间小屋子呆着,每天吸烟唱茶读报,没人理他们,苟安。”
但很快,一份抄录了军委文革小组某人的讲话大字报将马连良判为死不悔改的人,要求必须打倒,这是马连良被点名并被宣布为死不悔改必须打倒的一条催命符。黄世襄回忆:“当我在屋里听到有人喊:‘马连良,出来!’我一惊,赶忙地从屋里我也出来了。我的屋子与马先生屋子相距不过五十米。我出来见有俩个人站在马的屋门口,我过去见马先生和尹君彦坐在一张圆桌两侧,屋内昏暗,桌子上方吊着一个不大的灯泡,桌上有烟、茶、报纸。马被叫了出来看大字报,并被逼着叫他自己念。我当时也很紧张,不记得他是怎么念的,也不记得那二人训斥他的话了。原谅我不能说讲话的是谁,也不能说出那二位是谁。以后好像再没见到马来上班。不久大家就知道了马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突发心脏病,病逝于阜外医院。二团接家属通知,去了一位以前做总务工作的胡XX看了一下。团里沒有讣告,没有任何悼念,只知道他被化了。一代伟大的艺术家,就这样……!”
从香港北归,到猝然离世,时间正好十五年。马连良果然应验了大星相家袁树珊的卦象。为了悼念恩师,也为了光大马派艺术,安云武于1996年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北京民族宫演出了一场《海瑞罢官》,尽管是包场演出,票已经卖掉了,他还是建议剧院一定要有演出的宣传广告,因为剧院正对着马宅、马先生故居。安云武说:“我是想通过这个广告,告慰马先生的在天之灵。”遗憾的是,今天,《海瑞罢官》依旧不常见于舞台,或许,今天的马派传人也避讳着他们祖师爷的绝唱!
在接受阳光卫视的采访时,安云武抚摸着按照老师当年设计的戏服——海瑞所穿大红蟒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度哽咽:“……一个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大事件,偏偏最悲哀的是拿《海瑞罢官》开刀,海瑞够倒霉,马先生够悲哀啊!时时刻刻觉着先生太悲哀了。常常想着,先生其实身体真是很好,没有这场灾难,他不可能故去。如果真是能够再多活些年,他给社会的贡献,给我们传下来的会很多的。历史太悲哀了,我真是希望悲哀不再,我也相信悲剧不会重演!”(续完)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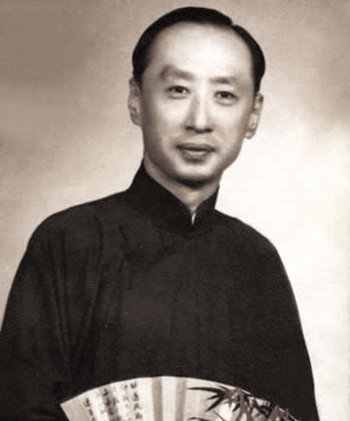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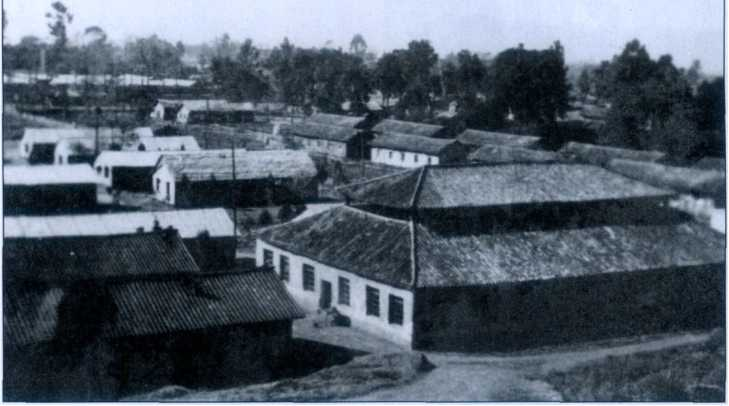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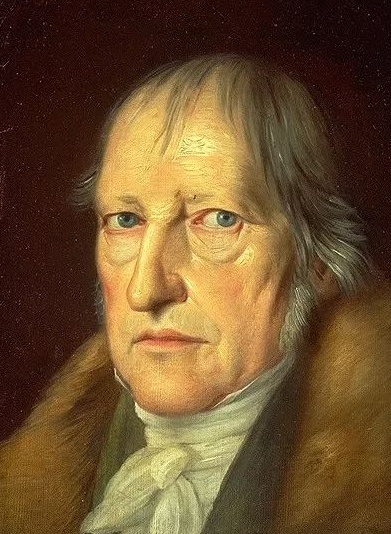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