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是感恩父亲的节日。每当提及感恩二字,想到的肯定是回报的内涵。幼时不懂感恩,更难理解何为回报。大多情况下,都是默默地享受一己的快乐。
比如,最亲密的与父亲的身体接触,是生病时到人民医院打针之后。疼痛难忍、满腹冤屈,就直接到了父亲的背上。父亲背着我,从安徽路的小上坡,转到黄岛路的大上坡,然后是三十几磴楼梯再入家门。现在回想,这种无规律的偶发而趴在父亲的背上,像是站到了他的肩膀之上。有朝一日若能看得远些,应得益于那个最初的端点。
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到他的工作单位美术公司上班。于是,又过早地接触和认识了他的许多同事。除此之外,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色彩、光影、构图、比例乃至颜料的特殊气味,这些都成为我对美术的最初印记。当年画画的叔叔阿姨们,早已是岛城久负盛名的画家。当我上小学时,也被冠以会画画的特长,但最终还是妹妹拾起了画笔,算是延续了点滴父亲的基因。
图片
小学三年级时,写日记是家庭作业。第一个笔记本,是乳白色的外皮。父亲将我的名字写在内页的封面,这样透过塑料封皮,便可清晰看到姓名。笔记本是某天的中午时分,父亲在曲阜路三角地的水池子旁给我的。因为之后,学校组织到安徽路头上的红卫兵影院看电影。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通讯工具,与父亲在马路上会面,完全依靠一种心灵契合的偶遇。
沿着曲阜路西行,下坡左拐不远,中山路西侧的54号就是美术公司。八十年代初,父亲调到了外贸公司,从事包装装潢、商标设计、展览宣传的工作。其中,春秋两季的广交会,是他必定要去参加的室内商品布展和户外广告绘制的前期准备。
那时的广交会会期长达一个月,加之前前后后的筹备和扫尾,一次出差常常要四十几天。有次返回青岛时,我按照头一天电报通知的到达时间在中山路29号的民航售票处等候。当往返机场的依维柯客车停在谷香村饭店的门口时,父亲见我后说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头发留起来了。之前几天,我是理过发的,但一名高中生的头发会留到什么程度呢。或许是一个半月未见,我在父亲的眼里就有了全新的形象。
高考那年,我被自己填写的最后一个志愿录取。因为不甘心,想来年再考。父亲又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托人将录取的学校再申办退回。这是游荡在政策与人情之间模糊地带的操作。巧的是,五六年之后,我被单位选派到湖北路4号的招生办公室工作。虽说是一种借调的性质,但对其中的各个流程也开始略知一二。最终囿于内容的单调,我又选择了离开。
后来,我到了外企,与父亲所在的外贸公司又有了直接的业务往来。父亲的同事,又是我在工作中的合作伙伴。我又认识和熟悉了不少父亲的同事。
十几年前,母亲患病住在东部市立医院。有天傍晚,我推着母亲与父亲去了奥帆博物馆。奥帆赛之前,父亲将自己设计和外协制作的奥帆赛实物火柴捐献给主办方。据朋友描述,奥帆赛火柴已展示在博物馆内,但父亲却始终未能前往一览。这次就近看到自己的火柴在展馆一隅,自然是兴奋不已。回来的路上,恰好又碰到我不认识的父亲的同事。一问岁数,年届八旬。他同事说,时间过得真快,简直不敢想象。屈指一算,退休已经快二十年了。而今再转眼,又是一个十年。
六月第三个星期日,是天下父亲的节日。想想,有父亲节,真好。
2023.6.18
张勇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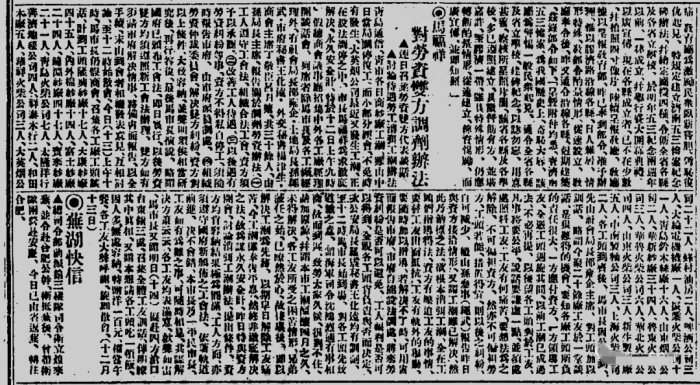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