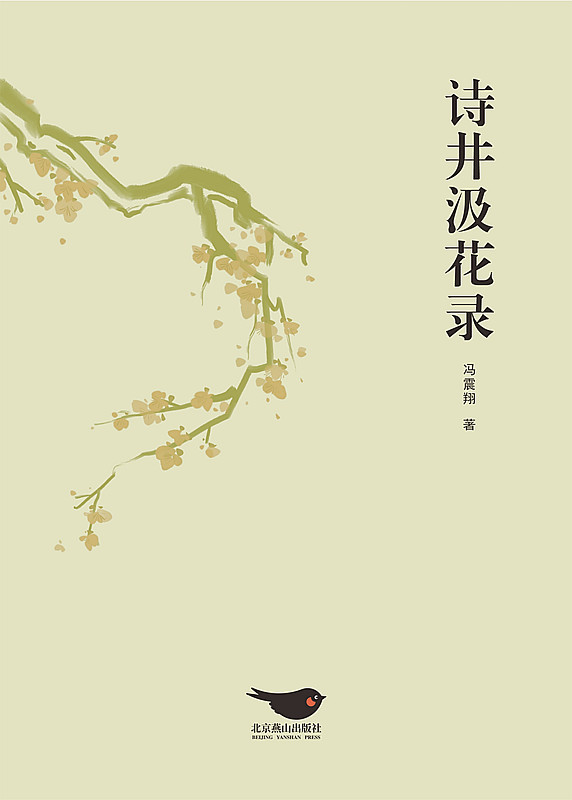一个是旷逸豁达,一个是阴狠毒辣;
一个文坛传佳话,一个青史留骂名;
曾经是一对好基友,到了成了活冤家。
苏轼和章惇,北宋中晚期政坛上一对不容忽视的双子星,以各自的异光投射在对方身上,千年之下依旧迷惑人眼。说不尽,道不完,扯不清,理还乱……
宋朝立国以来,崇文抑武,到了仁宗时代,这一国策结出累累硕果。仁宗嘉祐二年殿试是显著的文化昌明标志性事件: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榜上有名的进士有24人于《宋史》立传,其中9人位至宰辅,有三人文学成就位列“唐宋八大家”,更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程颢/程颐三双兄弟同榜高就,这一榜因此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这一年也被认为是“科举制的最高峰”。嘉祐二年榜单中,每位中榜者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在此说一下其中两位:苏轼和章惇的故事。
一、出身及个性
苏轼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眉州眉山人,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他还有个著名的弟弟——苏辙,和他同榜进士,后来在政治上与他同进退,成为他落难时的保障。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真义。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章惇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才智出众,学问广博,文采斐然,胆识超人。年轻时,喜欢修养,服气辟谷,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章惇小时候,其族父章得象惊异章惇的性情品格,认为章惇将来一定地位优越。这一评价,有点像曹操小时候的样子。
关于章惇的身世,穿插一点八卦,王明清《挥麈后录》载: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
王暐的笔记《道山清话》里,关于章惇的身世有这样的说法: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并没说章惇是父亲与外祖母乱伦所生,只说他生下来差点让父母溺死。
章惇身世传闻真相究竟如何?难以明晓。但是既然种种说法,恐怕不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样的传闻难免给章惇心里留下阴影,以致于后世据此推断章惇因此而和苏轼反目,且先把话头搁在这里,后面还会论及此事。
苏、章二人年龄相仿,才华不相上下,性格各有特点,从出身看,苏轼的家庭背景略输一筹。
二、同榜进士
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于嘉祐二年(1057)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正合考官心思。当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使得这份试卷只得第二。苏文中用了这样一个“典故”:“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这个典故出自《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想当然耳。”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欧阳修甚至击节称赏,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当即表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由此还催生了一个成语“出人头地”。苏轼名动京师,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只能与弟弟苏辙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也是嘉祐二年章惇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这一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状元,章惇耻于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家。后于嘉佑四年(1059),再次应试,再获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历官商洛(陕西省商洛市)县令、雄武军(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节度推官。至此,二人仕途平行,难分伯仲。
三、相交西北
苏、章开始交往是在入仕以后,苏轼嘉祐六年(1061)底初仕为凤翔府签判,而章惇则为商洛令,“轼始见公长安(《与章子厚书参政书二首》)”二人从此订交。也是嘉祐六年闰八月,苏辙入制科四等,以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本该成为章惇僚属,因在京城伺候老父苏洵而未能赴任,否则三人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嘉祐七年(1062)十月,苏轼与苏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苏轼自注: “章子,惇也”。苏辙在《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这里的“长吏”亦即商洛令章惇,说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并且一起提及过苏辙。
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九日,苏轼循行至盩厔,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二人同游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地,此行见章惇《游终南题名》: “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同游仙游潭时,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且以此夸耀于苏轼,曾慥《高斋漫录》(亦载《宋史·章惇本传》)记载:
仙游潭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 “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 “何也?”子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苏轼有诗为证:
留题仙遊潭中兴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
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攀书室窥岩窦,还访仙姝款石闺。
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將双脚踏飞梯。
二人个性差异于此亦可见一斑,苏轼在调侃之余,对章惇还是不无称赞的。
这一时期还有酒后观虎一事,据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 “子定不如我。”
青年章惇对自己表现之自负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类似记载还有: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 ‘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道山清话》)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自凤翔经长安,在王颐家观看《醉道士图》,苏轼因为不能饮酒,故随手跋曰: “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跋醉道士图》)。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作《题跋醉道士》: “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噱绝倒。子厚书。”其中“发噱绝倒”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赴京途中再过长安,见章惇题跋,争胜之意隐忍不住,故又随手再题,云: “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噱。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过长安,看到苏轼题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章惇揭苏轼之短,谓其虽好山水,却知难而退,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依次类推,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实不知酒中真味。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早期苏章二人间交往亲密,未曾龃龉,但二人年轻气盛,恃才不让的个性却也异常鲜明。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