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0月9日,父亲还待在位于河北路的商业局医院内科病房没有出院,他已经在那个小医院里几乎度过了整个夏天。在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这个小医院里度过。现在,我要暂时离开他,去四百公里外的曲阜去上学。
我的行装已经准备停当,还是那个和我去过塞外边疆的正方形木箱,装着我的铺盖和全部日常用品。这些用品中大部分,已经与上次离家时大不相同,特别是里面多了我这些年来购置的一些书籍和亲友赠送的为数不少的笔记本。但最大的不同是,这次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操办的。从那次离家远行距今,八年时间过去了,我已经没有也不再需要父母羽翼的护佑了。与此相反,由于他们的身体日益衰老虚弱,现在家里整个格局已经完全翻转。
春节过后,妹妹已经远赴哈尔滨一个院校就读。她的离家,使自认为身患重病的父亲感到了更大的压力。所以对我这次去往一个虽然位于本省但毕竟数百公里之遥的学校读书,他的内心十分纠结甚至非常抗拒。其实呢,对于到鲁西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师范院校就学,我内心的纠结和抗拒也许并不比父亲更少。
1977年初冬举行的高考,在当代中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届入学考试。从文件发布到开考,中间只有40多天的时间。我也参加了那次高考。虽然那年高考成绩没有公布,可是我知道我的数学得了零分,因为我一道题也没有做,自然也谈不上录取与否的问题。
过了春节,我开始在一个夜校里补习中学阶段的数学课。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帮我针对高考制定了一个补习方案。将于七月初举行的考试之前,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把初高中的全部数学都补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可行的方案显然是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把其中几个门类有针对性地补一下,确保不再次考零分。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制定的计划。首先,谁也无法准确判断高考数学的出题范围。其次,我的这门课实际上要从小学的算数开始补,因为从1966年下学期开始停课,我的知识也就停留在小学五年级上学期的水平。最后决定,代数和三角函数完全放弃,集中补平面几何和对数,再视时间和进度或许能补一点解析几何。总之,一切似乎都在未定之天,最终大概还要靠运气。
我从边疆回城以后,被安置在一个区政府的小工厂里,在一个电刷车间的钻床上工作。这是一个充满粉尘的阴暗的空间,我那时的工友中,好几个后来都得了尘肺病,不及花甲便早早离世。车间工作时间分早中两班。早班从早上6:00到下午14:00。中班下午14:00~22:00。这样我就有半天时间可以复习功课。当然对我最有利的是上早班。因为夜校的课都在晚间。同车间的工友们对我参加高考都积极支持。但是厂里领导的心态却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无非是1978年的高考给予了考生很大的自主权,报名时连工作单位的证明都不要,只需拿着本人的户口本即可,完全摆脱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这对于那些思维还处在文化革命中的各级革委会委员们来说,自然从内心极度抗拒。
红瓦绿树、波光潋滟的青岛其实是一个缺水的城市,那一年又出现了气候异常,降雨极少。随着天气转暖,城市缺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推出了一个计划,引大沽河水入青。各个单位都要抽调青工,参加位于即墨县的大沽河水利工程。
这件事正好给了厂领导一个合适的借口,用来给报名参考的青年工人设置障碍。他们把这些已经报名了的青工,通通编入了大沽河的水利工程队,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本来我们这个小车间的工作负荷并不大,人员实际上有点人浮于事。几个青年工友主动表示他们可以代我参加,可是领导的用心不在青岛的供水上,所以并没有同意。
不过恰在这时,我的老父亲突然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拒绝去挖河工地的正当理由。那个年代因为缺少社会服务,家里遇到病人住院之类的情况,单位还是允许请假陪床的,当然前提是仅限直系亲属。这应该说是那个严峻的年代里,计划经济社会的一缕温情。于是在距离高考前大约一个月,我获准去为父亲陪床。
我逃脱了前往水利工地的任务,但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充分的补习功课的时间。从此时开始,直到我赴校报到,我的基本活动空间就在那个位于河北路的三层小楼上。
我随身带着我所收集到的高考复习资料来到这个小医院。不管怎样,我在这里可支配的时间,比在工厂里上班还是要宽裕很多。当然补课的主要时间是在晚间。除了夜校,我也通过朋友的关系参加了附近几个中学为本校学生开办的复习班。但下课后我必须回到医院,在夜间陪伴父亲。幸而已是夏季,天气已经开始变得炎热。我从家里带来一张单人的草凉席。如果病房里有空床,我也被允许在病床上过夜。因为父亲常年在这个医院进进出出,我和这个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也混得很熟,其中的一些甚至成了朋友。如果病床满员,我就只有在两个病床之间的地板上铺开凉席过夜。好在这个医院离我们家不过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饮食洗漱等各种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回家处理。
(二)
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可是我对于这次考试还是完全没有任何把握。尤其是从零补起的数学。已经到了临阵磨枪的时候了,我和母亲商量,她是否可以请假来医院里替我一个星期。母亲同意了。于是在开考前的一个星期,我终于摆脱了看护病人的羁绊,全力以赴地开始备考。
1978年的高考对我来说有一个神奇的巧合,就是不仅考场设在我的母校青岛八中,而且我的座位就在我曾经呆过的教室。八年前,我带着一个洗空的头脑和一腔幼稚的热情离开这里去了边疆,八年后,我竟然在同一个教室里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当我重又坐在这间阔别八年的教室里时,心里很有几分感慨。这八年,我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现在,是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考试一场一场地过去了。其他的考试的细节我已经不怎么记得,只有那可以说是决定我命运的数学考试,经过我还大约记得。卷子打开的那一刻,我的忐忑和紧张丝毫不亚于前一年。终于,我看到考题里有几道我能够理解的题目。我遵照考前老师对我的叮嘱,做题时先易后难。我做完了几道分数不多的小题。心里多少放松了一些,不管怎样,我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再看剩余的大题,似乎都是一座一座巍峨的高山。在我补习功课的过程中,对数相对学得较多。而那年的考题中,的确有一道20分的对数题。在考前复习中,老师有针对性地把历届高考的对数题都让我做了一遍。可是1978年的这个卷子,出的却是一道求两个X的题!
我看了看表,离考试结束还有两个小时,就这样交卷,我有点不甘心。于是我把心一横,就权当爬一道山梁吧!等我把心沉下来之后,似乎还在这种解题过程中体会到了一点乐趣,我甚至还推演出一些没有学过的公式。交卷的铃声响了,题没有做完,但无论如何,这次我交上的不是白卷!
事后数学老师看完我重演的这道题,他很遗憾地说:“哎呀,只差一步!不过这种情况,判卷老师一般会给你一半的分!”
虽然半年来的备考一波三折,但是学习的过程也给了我信心,我在内心已经暗暗打定主意,今年再准备一年,结果肯定更为乐观!
但看起来那位批卷的老师并没有给我这理想的一半分,分数公布之后,我的数学成绩是可怜的12.5分,远低于我估算的20分左右。我始终没搞明白这个0.5分是如何算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位判卷的老师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把那一道对数题给我一半的分。他大概觉得这是一个来凑热闹的社会考生,而那两届考生中这一类人物也十分常见,这么烂的成绩,估计哪个学校也去不了。
还有一门带0.5分的成绩是我加试的英语,因为我没有报考英语专业,所以对我来说,这一门课纯粹是额外的自我测试。但其结果也有点儿令我意外,得分虽然不是很高,但却超出预期,竟然得了47.5分。
(三)
录取通知书下达的那一天,我正在车间里工作。厂办公室一个女孩儿来通知我,让我到区招生办去拿录取通知书。这让我吃惊不小,因为事先我们已经知道,今年的录取通知书分两天下发,第一天是重点院校和外语专业,第二天才是普通院校。莫非苍天有眼,把我抛给了某个重点院校?我抱着几分困惑和兴奋去了招生办。
当我来到位于市北区政府的招生办公室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不少人,其中还有几个熟人。当招生办的人把我的录取通知书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那是一个很小的用粗糙的牛皮纸做的信封。这个信封和里面的通知书,前几年搬家的时候在一个袋子里翻了出来,现在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当年我打开它的时候,感到意外又沮丧,曲阜师范学院外文系!这个学校此前并没有进入我的视野,虽然学校在省内,可是对于绝大多数青岛人来说,位于鲁西南的曲阜,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所在。至于这个学校,我只是依稀记得,当年在八中班主任老师曾提过他毕业于这个学校。尽管曲阜是孔圣人的出生地,但显然这所大学没有孔圣人那么崇高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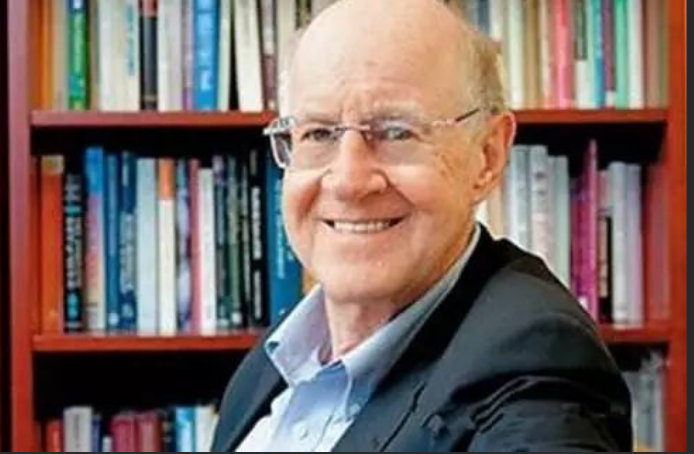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