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回乡探望父母,一路上尽是秋深景象,公路上照例是晾晒的玉米,田野里满溢着收割之后的寂寥。因为天旱太久,残存的绿色已呈疲态,临近晌午,越发显得无精打采。我想起小时候的农村,这个时候正是三秋会战的尾声,在野外竖红旗搭帐篷餐风饮露的农夫们早已疲惫不堪了,就等着冬小麦下种后拔营回家。我饶有兴趣地给年轻的儿子讲述,他一脸茫然,仿佛是在听天书,我不免慨叹,我亲历过的历史在他听来就是呓语!
回到家,弟弟正在院门洞用木柴架火蒸羊腿,一进门就能隐隐闻到肉香,父亲正在沏好茶,母亲和弟妹在灶间准备着炒菜,这一幕和谐的场景顿时让小小的旅途劳顿烟消云散!尽管农村离“新”标准尚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它的土气里的质朴还是让我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伪城里人感到由衷的亲切。
进到屋里刚刚坐定,院子走进四位不速之客,为首的有些年纪了,后面跟着的应该是他的子女,说是从蒙阴来的,这几位客人我是从没见过,也从未听说家里有革命老区的亲戚。我正纳闷,只见陌生老者进到屋里一言未发,直直盯着我父亲,眼里充满着期待,似乎想唤起陈年的记忆,我父亲也是一脸愕然,怔怔打量着来者,显然他记不起这位访客了,两个老人就这样互相看着对方,足足半分钟,时间似乎凝固了,这半分钟就显得特别长。还是访客打破了沉默,说,你忘了,我是你的老邻居,我们家就在你家东面。我父亲似乎想起什么,说道,你是不是几年前回过村子修家谱。老者说,是啊!父亲问,你的大号?老者说了自己的名字。两位老人仿佛都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老者姓刘(姑且称他刘大爷),我们村以“刘”姓命名,他算是村里的“正”姓。老人祖上是村子里的大户,他爷爷兄弟三人,两位是秀才,算得上是耕读世家,他爷爷排行老大,人称大秀才,宅院就在我家东邻,我小时候生产队的牲口屋即是他家的一部分,是他家庞大财产充公为集体财产的一部分,生产队的场院也曾是他们的私家场院。老人祖上在村里成分最高,一度是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家族,可这一切在1947年彻底改观。这一年的一个拂晓,这位如今的耄耋老人,当年还是刚刚记事的孩童,在夜色和好心人的掩护救护下,翻越围子壕沟逃离村庄得以活命,后来随家人辗转到了蒙阴,从此断了消息。72年后的今天,老人回到村子,找到当年的邻舍,说起来仓惶逃命前对村庄的记忆,尽管遥远,却仍让人不寒而栗。我在边上,听得真切却又恍惚,他们这一辈亲历的历史于我不也是呓语吗?
毕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刘大爷和我父亲的回忆七零八落,能够重合的已经很少,刘大爷反复讲我们家曾有棵枣树,他小时候总在枣子成熟的时候在我家院子外打枣吃,而我父亲则说是一棵杏树。为了这棵早就不存在的枣树或是杏树,两位老人叨叨了好长时间,我和老人的儿女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认真地说那棵已经不存在的树,会心对望一下,没有打断他们的唠叨。
这个村庄对于他们还剩下些什么?他们的记忆究竟还存留了什么?老人回到村子想找到什么?我们或许永远猜测不透,这就是历史!
刘大爷在我家坐了一会,起身告辞,父亲挽留他在我家吃顿饭,老人的孩子婉言谢绝,说是他姑家已经准备好了午饭,父亲和刘大爷依依惜别,送他们出了院子,我看到老人离去的背影,似乎在告别一个时代。
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午饭多了一个话题,父亲讲述了这位比他年长几岁的老者童年往事,老人家里在1947年遭了大难,一夜之间,宗亲遭到屠戮,这是我们教科书里说的解放,老人因为母亲改嫁了家里的长工,受到保护,在好心人的救助下逃脱凶厄,得以保命。其实,他一进门父亲就想起他的小名,因为当着他子女的面没有称呼,另外不确定他是不是随了外姓,不能随便称呼他。我问父亲,如果1947年他没有逃到邻村继父家会怎样?父亲说那会被投进井里淹死。他们家在1947年死了不少人,也逃了一些,其中有逃到青岛的,后来还被遣返回老家,我对这些被遣返的他的同族是有印象的。刘姓大户被屠戮后不久,还乡团就来了,回头杀了不少农救会的骨干。村子竟然有过如此血腥的一段历史,这些情景多像一部小说啊!可这不是小说,而是血淋淋的现实。
没想到这次回乡遇到这一幕,这两天我一直沉浸其中,因为假日,所有的东西都像魔镜里的映像,似真似幻,我不知道再过许多年,今天的历史会不会成为后人耳边的呓语。
原载轻博客2019-10-06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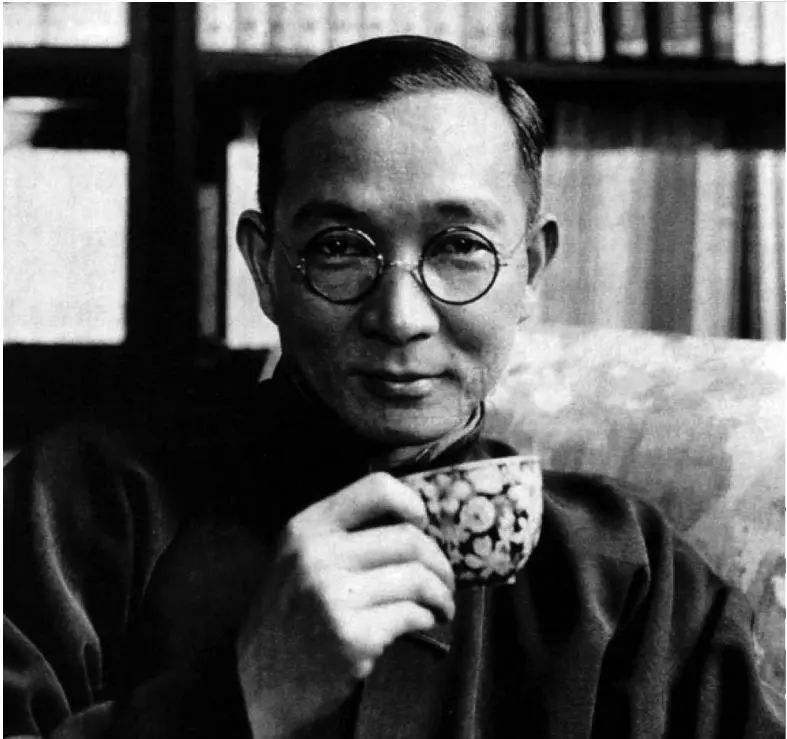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