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等待戈多》并非烂白菜帮子散发腐朽味的作品。它直白易懂,警醒世人。
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是主要人物,贯穿全剧。
第一幕结束时,弗拉第米尔说:“咱们走。”他们并没有动。
第二幕结束时,爱斯特拉贡说:“咱们走吧。”他们站着不动。
他们继续等待。
次要人物波卓和幸运儿半道上场,半道下场,仿佛只为了经过“等待戈多”的等待。
次要人物在第一幕的上场不同凡响:“附近传来一声恐怖的叫喊。”
“波卓和幸运儿上场。波卓用一根鞭子牵着幸运儿赶着他走,绳子的一头拴在幸运儿的脖子上。”
“幸运儿拎着一只很重的旅行箱,一条折叠凳,一只食品篮,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件大衣。”
“波卓手持一根鞭子。”
次要人物在第二幕即“等待戈多”的第二天的上场平淡多了。
“波卓和幸运儿上场。波卓已经变成了瞎子。”
“幸运儿跟第一幕那样负担着很重的东西,也跟第一幕那样拴了一根绳子,但绳子短多了。”
“幸运儿戴了一顶新帽子。”
旧帽子在第一幕被人丢了。幸运儿用帽子思考。离开帽子,他不能思考,不能说话。第二幕他戴了顶新帽子。幸运儿已经哑巴,波卓成了瞎子。
次要人物在第一幕下场时,波卓朝幸运儿挥舞着鞭子:“起来!猪猡!向前!向前!再快点!猪猡!”
次要人物在第二幕下场时,波卓对在场的“所有人”用愤怒的声音发表了一通演说,然后拉着拴幸运儿的绳子下台:
“一记坠落的声音,这意味着他们又摔倒在地上。”
首先我们注意到绳子,一头套在幸运儿脖子上,一头拿在波卓手里。波卓需要幸运儿做什么时,拉一下绳子,幸运儿受到牵引,便乖乖去完成,让他朝前走,他就朝前走,让他后退,他就后退。波卓让他走一步,幸运儿不会走两步。两人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彼此丧失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紧密性表现在越来越不能自拔的失丧中。实际上,两人都是失丧者,迷失者。绳子,既是幸运儿的轭,也是波卓的轭。在第二幕中,这种牵引关系完全颠倒,幸运儿在前面走,领着已经瞎了的波卓。幸运儿摔倒,波卓也跟着摔倒。他们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没有变。
幸运儿总是“负担着很重的东西”,两个主要人物也奇怪他手里总是拿着重物,不肯放下。他可不可以放下,让自己轻松轻松?看来不可以。因为一放下,幸运儿便会跌倒,他习惯了被重压,一旦失去重压,反而因失重而摔跤,非常费力才能再爬起来。
长期的痛苦虽然无法承受,但也可以习惯。习惯了,便离不开了。这就是幸运儿的“脚步”,他把自己的“脚步”,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手拿鞭子的波卓。他自己力不能胜这种“交给”。波卓握着幸运儿的“交给”,说:“将由我来给他指方向。”如果幸运儿不按照波卓的“方向”做事,波卓便挥舞手中的鞭子,鞭挞并谩骂。
鞭子是波卓的武器,也是他的轭,或者是重轭,他迷失于鞭子,如同幸运儿迷失于绳子。这些轭,套在他们彼此的颈项上,使生命越来越衰弱,无力解脱。
轭即罪,《等待戈多》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陷入罪的网罗,苦苦挣扎,过一日如千年,没有安息。
帽子是《等待戈多》荒诞剧中一件重要的象征物。幸运儿必须戴上帽子,接到“命令”允许,然后思考。当弗拉第米尔给他戴上帽子,波卓命令幸运儿:
“思考!”
幸运儿在波卓指定的位置(离开这个位置也不可思考)开始思考,开始独白(嚎叫),剧中设为独白碎片,一口气嚎叫了 1500 多字。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懂在说什么,仿佛一堆乱码。爱斯特拉贡、弗拉第米尔、波卓在幸运儿嚎叫的迷乱声中陷入疯狂,波卓高喊:
“他的帽子!”
弗拉第米尔抢走幸运儿的帽子,幸运儿闭嘴并倒下。舞台上,死一般的沉默。
丧失独立意识的人,需要思考吗?在第二幕中,幸运儿戴上了新帽子,但他不需要了,他连用帽子思考的可能性都放弃了,成了哑巴,全身上下,没一样东西再属于自己,包括思想,包括灵魂。他既是别人的奴隶,又是自己的奴隶,其悲剧性还表现在享受奴隶生活现状带来的满足感,沉浸并疯癫。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们得救了吗?
原载 阿龙书房
2025年1月6日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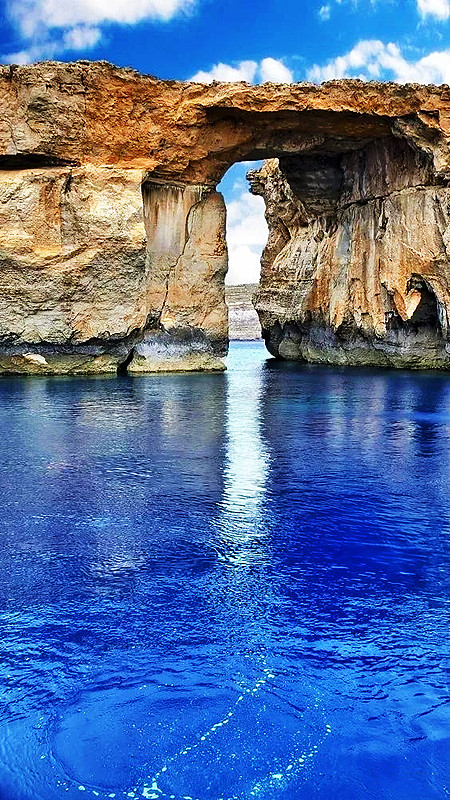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