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在北京引起极大的忧虑。这并非怕战争迅速波及远东,一般人担心的是怕日本将乘机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政策。这种担心不久即成为现实,威胁着中国的安全。(1914年)8月间,离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当然,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当最后通牒送达柏林时,日本军事当局早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对德国租借地发动进攻。所采取的方式是日军在山东登陆。本来德国建筑的炮台都是面向海洋以防海上袭击,而日军却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距芝罘(烟台)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事先日本政府并未通知我国,直至日军已开始在龙口登陆,才由驻北京公使馆告知中国政府。实际上,袁世凯还是从山东都督的报告中获悉的。
日本的行为显然是侵犯中立国领土,完全违反国际公法。中国则无力进行有效抗击,至少中国政府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采取什么行动。袁世凯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顾维钧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顾维钧发言,顾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
这话显然是对顾维钧和伍朝枢说的。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定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国际法呢?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德国由于在欧洲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有两天的工夫就结束了。德军投降,日军随后开入并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包括青岛在内,然后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这使山东都督大为吃惊,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遏制日本的行动。在首都,政府的忧虑增加了,唯恐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之后继续提出更多的特权要求。大家认为这是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它绝对不肯交臂失之。
1915年1月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日置益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大总统袁世凯面晤,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绕过外交总长孙宝琦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第一号有4条,是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旧德国权利、并扩展筑路权、定居权和通商权的要求。第二号有7条,要求将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南满铁路、安奉和吉长铁路的权益再展期99年,以及日本人在内蒙东部和南满的开矿、定居、通商权利。第三号有2条,要求日本独占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不将沿海口岸和岛屿割让他国。第五号有7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且日本顾问需多于他国顾问的总数。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器材由日华合办的军械厂供应,或向日本采购。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铁路建造权利交与日本。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承认日本的“布教权”。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他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霹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辣要求。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公使曾暗示某些要求必须接受,某些可以商谈。
谈判方针决定后,总统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徵祥被再度起用为外交总长,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与驻京日本公使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以加速进度,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商谈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报界对中国代表团究由何人组成,不免有所猜测。外交总长与留日的次长曹汝霖是两个主要的谈判人自不待言,至于其他三个成员,我的名字也被认为必定在数的,理由是这个谈判十分艰巨,结果如何要看中国能获得讲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多大支持。我的任务可能是负责向国内外新闻界宣传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但这时双方代表的人数又成了问题。
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构成三人代表团。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的公使有来往,特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的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问题。
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徵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
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已有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日置益先生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顾维钧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顾维钧认为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因为英国的在华、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很大的。尽管英国正在进行着生死攸关的战争,顾相信它不会不慎重考虑,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给予日本以过多的利益而影响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因为其他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无力干预亚洲的事务。法国正日夜忙于对德作战,俄国也已成为德奥发动战争的受害者。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顾维钧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顾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电询政府“二十一条”的详情,尤其是第五号时,东京开始焦急不安,显然东京并未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及谈判进展等详情通报其驻外使馆,据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谓的第五号。但国务院出示了“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难堪。此后日本政府也开始感到难堪,当然不是为了在北京的谈判中,而是在和华盛顿与伦敦的关系上确实是这样。秘密泄露后,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继续否认“二十一条”及其第五号的存在,非明智之举。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微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
这时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当然也感到舆论影响有利于中国。
在第五号上中国则采取强硬态度,根本拒绝讨论,而日方则继续坚持讨论。4月中旬,前四号告一段落后,谈判即陷于停顿状态。
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华盛顿的支持显然是为了让中国不屈服,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袁世凯决定派日人顾问为特使去东京和那些对日本政府,特别是对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便是西园寺公。袁世凯总统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4月20日,日置益不满中国坚拒不接纳第五号要求,宣告暂停商议。4月26日第二十五次会议,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二十一条要求改为二十四条。当然,这位日本人要完成他的使命需要时间,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
日本公使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而袁世凯总统指示外交总长不要恢复谈判,尽可能拖延下去。1915年5月1日,中国驻东京公使和日本顾问都从东京来电,说如果中国通过谈判已接受前四号,那么可以拒绝讨论第五号;但前四号的条款必须尽快签订,否则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日本公使也催促中国政府早日签订条约。袁总统不明日本政府恢复谈判第五号条约的意图,仍采取拖延办法,甚至日本公使暗示,如中国不接受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结果,日本将提出最后通牒时,袁世凯总统仍不明所以。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中华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要求可剥离此次交涉外,限5月9日下午6点前必须答复,承认各款要求,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事实上这个最后通牒并未出中国所料,因而也就没有引起想象的那种不安。5月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各部总次长及参政等人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特别会议,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其他参与会议各人除段祺瑞外也都同意,所以决定接受日本要索。5月8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往外交部面见陆徵祥,他说:“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40年,和大总统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5月9日23时,北洋政府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
最后通牒,有四十八小时的期限,中国面临的与其说是是否接受最后通牒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起草回文接受条款的问题。这个任务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那时,根据德国医院院长克礼大夫的诊断,因紧张、疲劳而发高烧,顾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外交总长来看顾,就最后通牒的内容和回文的要点和他商量。总长说总统指示接受日本要求并回文作复。复文不长,没多大工夫就草拟好了。前四号已经解决了,重要的是第五号如何处理。顾维钧草拟的复文异常简短,关于第五号,顾明白指出中国不能接受。外交总长认为可以,送呈总统,总统也同意。正在誊写复文时,中国代表团中讲日文的成员施履本提出,草稿最好先送日本公使看看。施这时按例正与日本公使及其僚属保持密切接触。他解释道,如果日方不能接受,正式复文送出后,将造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次长曹汝霖同意这样做。施带回了日本公使的反应,大意是语气过于决绝,建议关于第五号改为容后再议,东京可能更容易接受。顾认为没有必要,否则在中国公众和友好国家的心目中我们太软弱、太妥协了,而且也给日本将来重新提出此问题提供借口,因为据说日本公使曾表示,修改此句更易为东京所接受,并可顾全日本政府的面子。顾住在德国医院,未能参加在总统府召开的最后批准草案的会议,而复文中终于保留了修改的辞句。
5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陆徵祥与日本政府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顾维钧认为下一步政府应发表一份详细声明,说明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顾的建议未能迅速为外交部的某些同事所理解。照他们看来,中国的任何声明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敌意,招致不利的报复;中国既然接受了最后通牒,事情就完了,越少提越好。顾维钧解释道,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特殊要求有损国家主权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说明中国如何进行谈判,怎样谈判,中国拒绝无法接受的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必要的。外交总长赞同这个意见,总统也同意。至于这份声明究竟怎样写,曾征求外交总长、次长和驻华盛顿公使的意见。此事应由各司主管负责,但外交部认为把整个交涉过程回顾一遍,并于当夜或第二天发表声明,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顾维钧说,要使声明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迅速发表,使国内外报纸及时刊载。由于讨论到由谁写,怎样写。顾说他认为事情应该做,而且应赶快做,如果司里难于承担这个工作,他愿意做。外交总长很高兴,只是指出,鉴于顾的健康情况,应先问问医生是否准许他做。顾维钧向总长保证说,他虽然发烧到华氏101度,口授文稿还是没有问题的。经与克礼大夫商定,给他的两个秘书另外准备一个房间。克礼大夫虽然是德国人,中国话说得很好,他支持中国的斗争,特别是中日签约之后。他说他要把一位病人移到较远的房间,以免他听到什么。顾维钧请了一位澳大利亚人端纳协助。端纳是一家澳大利亚报社的记者,后来接替莫理循做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顾口述,端纳写,不用速记。他叫他的助手普拉特打字。他们从晚上九时三十分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一面说,一面写,然后立即打字,天亮前一份打好的声明就出来了,一共大概有十二页至十四页。然后部里很快把它翻译出来,由总长、次长送呈总统批准,立即发表。
其他参加者有:日本牧野男爵,英国罗伯特·塞西尔勋爵,法国布尔热瓦,南非史末资等
1919年4月,巴黎
该条约部分内容由于影响到其他国家在华利益,部分条款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被废除。此后《民四条约》内容不断被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彻底废除。
原载 读曰乐
2024年11月15日 17:25 青岛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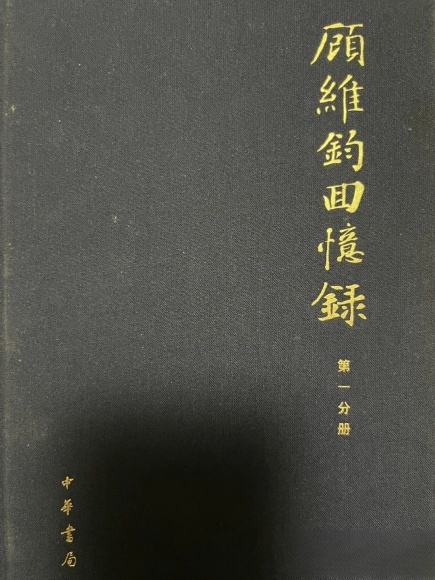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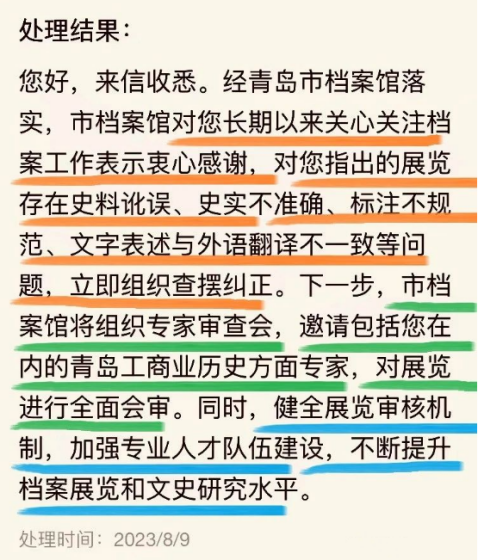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