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青生想,这不是居住的问题,而是生活质量能否维持的事了,他感到的确不能退,不能丢,不能让,要牛到底。可是,坚持又坚持得毫无结果,又坚持不动,坚持到自己都快要土崩瓦解了,坚持到妻子和孩子崩溃了怎么办?
这天牛青生又去提水。因为妻子要洗衣他来回提溜了五趟。他看到妻子将洗完后的衣服、床单、袜子、内裤等搭上院内的衣绳。他看看水缸,看到水离漫过缸沿还差一半。他又提起水桶出门接水。走出院门,他看到一辆辆汽车像驶进空寂无人的操场鱼贯而入,这些汽车的轮胎沾上了雪,白燎燎的;他来回几趟的脚印被无数交叉的车辙印辗没了。
那些汽车停在他们家正前方的不远处,阳光刺在雪地上反弹,又刺中他的眼,一只喜鹊从他的头顶飞落在家门口的槐树上呱呱地叫着。他听到前面车门开启和浑厚的关门声嘭嘭地响着,阳光和雪地扭打在一起的眩光,令他只能看见一双双锃亮的皮鞋从黑色的车门踏到白色的雪地上。他听到其中有个人在雪地的反光中向几个人介绍着地域与地块。
“总共180亩地。目前已批复的容积率是2,做做工作可以多点。”
“哦,拆迁安置的比例是多少?”
他听到这人的问话是拖拖沓沓的。
“比例是65:35。按现行的行价应该不单是盈利过亿的问题,而且我讲的是税后。”
牛青生踩在车辙上的脚印往前走,身后的声音令他的耳朵落在他们杂乱的落脚处。他的影子在雪地上缓慢地移动着。
“起草个转让协议,把权力和责任明确了。”
牛青生听到了。他认为他听到了希望。
“先付定金。解决了钉子户我们开始正式打款。”
此时,牛青生认为自己是把耳朵放在他们口腔上结结实实听到这话的。他不光是听到了希望,他甚至还偷偷暗喜起来。他知道急于转让项目的开发商不会再拖延他的问题;不会再没事找事地和他这样的小钉子户浪费时间;也不会仅仅因为他而影响项目转让的进程与速度。
牛青生微微笑了。
接下来他认为不几天就会有人来接受他微薄的可以理解为卑微的要求了。他一路感到腿轻;他的门牙这会儿让冻嘴的风乱吹一通竟然也不痛了;他肿胀的嘴唇好像康复的结痂了。
他走到一座老楼房的住户家接水,受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好事的鼓噪,他感到体内的血液开始变暖,畅流;他开始热情地与住户的主人搭话聊天。
“还没到四九的严寒呢,你还打谱坚持下去?” 那老太太问他。
“当然。”他说,“人不能随便屈服。”
“别傻了!”老太太眯眼看着他,“人家有钱有势,你能斗过人家?”
“大娘!”他笑,“这叫命。”他说。他甚至像成功者往自身撒彩纸一样地说,“别人斗不过,不代表我斗不过。”
他开始沾沾自喜了。
牛青生那天的眼神奇好。他提水时脖子都是挺的,直的。他甚至举目眺望。他望着白雪遮盖下的废墟;他望着自家那冒出炊烟的铁皮烟囱;他望着喜鹊搭窝的那棵孕育生命的老槐树,仿佛空气都过滤了生的阴霾;他认为自己可以轻松一下,甚至认为可以慰劳一下自己了。
他已经算过几遍细账。他把拆迁安置费、搬家补偿费、搬迁一次性补偿费等能拿到手的费用充分算足。他们再在外面租个小房,他们还能剩下一笔足够他们八个月的生活费用。这笔钱可以用来买床,买桌椅板凳,还可以添置一台电脑。他觉得生活中可预见的安适像迎风飘扬的红旗,抖着旗帜啪啪地向他招手了。
(五)
当牛青生仅仅被预见的尚摸不着边的那点幸福折腾的思绪飘扬的时候,他们家的户外电线又被人掐断了。
此时,他们居住的房屋黑漆一团,仿佛是一个撒风漏光的纸盒子;他们的眼珠和鼻息借着窗外那点微弱的光亮,彼此认证着并驱赶着惊异。他们沉默了一会,听听四下无声,仿佛验证是一场虚惊;他的妻子又沉下了脸;他正在写作业的女儿把手中的铅笔也摔了;牛青生正喝着酒,他举到半截的筷子也找不到碟子里的花生米了;他眼前只有闪烁的烟头和夜下反光的酒杯及空空的酒瓶子;他感到这点酒兴无疑是既不适意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才将他把发现秘密的暗喜透露给妻子的时候,他们将要面临拆迁的喜幸;他们精打细算中的志满意得;他们对新房子、新生活的憧憬,让突如其来的黑暗,把恐惧像疑心的肿瘤或心灵的暗影又拽回来了;他与妻子说话的热度也打了折扣;他对借着酒兴夸大的未来,在女儿由刚才竖起耳朵细听变成晦气的甚至摔铅笔,摔铅笔盒的时候,他自己说话的兴致已唯恐闪了舌头,像合上的井盖只好密闭下来了;可是他还有点负气,可这负气是无语的,只能转化成吐出的香烟;他让妻子给女儿点上蜡烛。他将剩下的半口白酒喝干,然后他穿上外套走出家门。
冷风飕飕,一些雪粒子飞进牛青生的后脖子,牛青生哆嗦了一下,突然想尿尿。
牛青生抹了把脸,定了定神。
院门外的雪依旧下着,夜下的雪片披光带银,像萤火虫又像是没头的苍蝇乱飘乱舞。他走出院门,身骨略微摇晃,雪夜下的路面,隐约还露出一条狭窄的从他家里来回进出的脚印;他踏在这条小道上走着,那二两酒一见风让他的负气加重;他嘴上甚至为这种低贱的打搅还骂骂咧咧的;他正要拐弯查看那根从屋檐扯向那棵槐树的电线时,几个明晃晃的手电刺向了他;他抬起手臂遮挡着刺目的光源,还没等他辨析出什么,他的头就被不明的硬物嗵嗵敲响了。他眼前一黑,听觉上他只知道声音发闷,像敲在胶皮上一样,却又很疼。
他蒙了,开始止不住地吆喝,可吆喝的声音刚刚挤出嗓子,他腹部被莫名的硬物一阵乱捣,他的声音随着身子本能的弯曲也哑了声。他被人架起,拖入一辆汽车。
牛青生不知自己被拖上汽车时,他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是长长的,双脚没离开地面的;他也不知自己怎样被塞进车厢;他只是感觉车在东西摇晃时,他头上有股液体在颠簸中冒出来了。车上的人用一块抹布抹着他流出的血,然后用抹布按住他的头顶。当他懵懵懂懂,神智且又尚未脱离恍惚,他只是意识到自己流血了,他的头顶开始痛;他知道头顶肯定有个开口;他认为他喝下的白酒在加速血液的流通并令自己头顶冒出的血仿佛泉眼一样的暗涌着。
“你……你们是……?”
他问的时候腹腔在痛。
他的嘴因为多话而被人迎面一巴掌打住了。
他鼻子发酸;他眼前开始模糊;他意识到鼻子像透开的水渠并令他双手有意识的接捧住暗红的液体时,他试图动动胳膊,可是两个陌生人左右的夹持,他的胳膊也动弹不动了。他放弃了挣扎。
影子在左右晃动中移动。一个微胖的身躯从前座上转过身子,仪表盘上的灯光泛在他脸的右侧,那些泛着红色的弱光从他的脸侧映现出几块松弛的横肉。
“小子!”那人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牛青生咳嗽着。眼睛在车里冒着金星。
“你自不量力,阻挡了不该你阻挡的事情。”
他感觉又有温热的血阻挡了他的视线。他想看清回头跟他说话者的面孔,可是他的手指够不到自己的脸;他只能听任头顶上的血像蚯蚓一样在脸上爬行着。
“你能阻挡住吗?你靠什么?就凭你吗?”
他看着那个说话的影子在摇头。他开始喘着粗气;他腹腔的疼痛让他弯曲着腰身;他知道他的心脏也在加速地跳着。血弯曲着走进他的脖子,爬进了他的内衣;他的裤子上是指缝流淌出的鼻血。
“老老实实搬吧!”说话的人开始用黑黑的手指指向他。“明天,而且限你明天上午。这是最后期限。”
牛青生听进去了。他甚至听得很清晰。
“不然的话,你会玩完的。”那人说,“他妈的,你知道吗?”
“我,”牛青生哑着嗓子说,“为什么?我……”
他咳嗽着,“想知道……”
“完了!”那人摆摆手说,“一个潮巴!”
他看到那人又用黑黑的手指指向他说:“告诉你,明天是强迁,如若再找麻烦,彪子,我会让你缺胳膊少腿的!”
牛青生两眼怔怔地看着那只黑黑的手指,他认为自己已经木了;他看到那根手指又晃了晃,那人说:“走!跑远点,然后把他扔下去!”
牛青生在听到那人说“走”,听觉上他仿佛熟悉;他甚至由于疑虑这种曾经听过的话音而打断了他想再追问什么;直到车子停下时,他通过车前面两盏大灯的照射,隐约知道这是一处僻静的离他家挺远的荒坡。
他看到那人头一晃,车灯灭了。车前面的荒坡只剩下黑漆漆的一团。他想张嘴说两句,可是头顶流下来的黏糊糊的东西,把他的嘴糊住了,他只好闭上眼,稍微歇歇。
车又颠簸了一下,牛青生觉得浑身散了架,不知道身上哪个地方疼,他不敢动弹。
刹车的声音,牛青生听到有人拉开了车门,然后他左侧的人拽着他的胳膊,他右侧有人用手粗暴地推他,他稀里糊涂被人拽出了车厢。
牛青生身后是一只猛力踹他的脚,那鞋底很硬,牛青生像只麻袋一样,“扑通”栽了下去,面包车呼啸而去。
(六)
“牛青生!……青生,青生!……”
牛青生的妻子满黑夜里望眼欲穿,却连一丝丈夫的身影也没发现,她只好对着拆迁后推平的场地,漫无边际东喊西叫了。
此时拆迁后的场地仿佛是一片无人的旷野,远处是一些高低不一的房子的轮廓,房子有坡屋顶的房子,也有简易的多层板楼,几扇窗户在黑压压的楼群里倦怠地泛着光;刚开口的两声她还迟疑地叫着,声音收敛,疑惑,但当扯开嗓子听见回声是风,是雪夜里卷起的扑鼻的冷雪,她又赶紧跑回家用手机打牛青生的电话。
她风风火火地进门扯动着屋内的烛光跳跃着,她的女儿在晃动的烛光中也停下手中的笔侧头看着她。叶子按完号码,号码在拨出去的同时,她脚下一只正在充电的手机荧屏亮闪了——那是牛青生吃饭前放在马扎子上充电的手机。
她听了两声,预感到不妙,那不妙像心的暗影,又像相机放在慢门上,按下了,却要等待快门闭合的咔嚓,于是为了这快门回落的响声,她要涂抹掉这心的暗影。
她放下电话再次披衣出门。
他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这是牛青生妻子的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尽管有点神经质且不合时宜但念头仍像手机的按键,按下了自然就拨了出去。这狗东西不会是偷偷去找他的相好吧?她这样想着。
她在空旷的雪地里寻找牛青生的影子,眼睛落到院墙外无数个杂乱的脚印和车辙印时,她开始认为牛青生是真被人叫走了,或硬被人拽走了。她没认为这是绑架,因为她坚信她叫丈夫的牛青生浑身上下即便砸碎了也没值得让人绑架的东西。或许是被谁拖去哈酒了?有可能,刚才他灌了几口,可能不过瘾,加上又吵了几句。叶子还在脑海里搜索可疑的女性,有没有老牛的噶胡。
雪夜没有给她答案。
可是报案的念头她还在频闪。她在不妙与疑惑牛青生其他的作为里犹豫,她不想让牛青生因为她大惊小怪的报错案情而横遭呵斥,她认为还是要坚持等,别大惊小怪,先回家吧,等到早晨再说。
(七)
牛青生是在第二天的黎明时分,用肩膀和身体的重量把门撞开的。那时他衣服、衣领以及裤子上的血迹已经浸入衣服的里层;他脸上、头顶以及鼻子上血迹也变得发黑、生硬,仿佛是冻住的血块黏稠在血液经过的地方。
他躺在床上的妻子此时大惊失色;她的女儿也惊恐地喊叫起来,爸!女儿在惊叫的同时,两只手被牙齿咬住,眼泪像下雨似的往下掉。
牛青生傻了一样,看着朦朦胧胧的家里,他手足无措的老婆,此时已不知该干些什么,两只奶子从被子里蹿出的表情错愕,像那张蜡黄的脸一样。
牛青生在一种身心俱疲的衰败中已无力顾及她们娘俩了。牛青生的外形是打蔫了的,有气无力的。他的两条疲软的小腿如果没有两臂的支撑,他不知会踉跄到哪,他屁股坐在那张沙发上时,好像全身瘫下了。他感到自己像一只水壶,余热顺着手心正在慢慢消失。他的余光感到一个身影正在他身前身后晃动着。他抬抬手臂,伸手指指炉子边上的暖瓶,然后那只手又无力地垂下了。
室内冰冷。人影的晃动仿佛能拖沓出个影子。他的妻子用手在暖瓶口上试试水温,水温只是残热。她倒满一大杯,然后回身递给他。然而在她眼睛凑近牛青生却仍旧无法把牛青生那张脸看得清晰,看得完整时,叶子开始破静地哭。
“牛青生啊!牛青生,你上哪去了?到处找不到你,急死俺们了……”
叶子声音嘶哑,有些披头散发。
牛青生喝着水。
他累了,已经累到极致。他既无心也没有多余的能力再顾及他人。他喘气的声音粗重,鼻息和嘴呼出的热气像烟囱一样,喷着眼前的杯子,继而又消失。
喝下这一大杯水令他感到有些松快了。他感到饮下的温水就像灌溉的流水在沟渠里东拐西走——在慢慢地走向四肢。他的身体也在这游走中慢慢地苏醒。可是苏醒的同时,他的心却在紊乱又扭曲地跳着。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就是一个运转循环的水泵,血由心脏收拢再分配到五脏六腑,分配到头颅与四肢,令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像打鸡蛋羹一样,打起了无数的气泡。这些气泡在肺部有块空隙的地方得以喘息,像吹起的泡泡糖,在破与不破收缩并鼓胀着。
他咳嗽了两声,腹腔却拐带得生痛,眼前也闪烁着星星。他甚至看也没看站在对面的老婆说:“今天……你们都走吧!”
“什么?”他正在哭泣的老婆眉毛都拧了,叶子问:“你让我们上哪?”
“回你妈家,或愿上哪上哪!”他开始不讲理,也不想讲理了。
“你……”叶子哭着说,“你想干什么?”
“我……”他眼睛碰到泪眼模糊的女儿,嘴巴不由缓软了下来,说:“男人的事,除了听话……别瞎问。”
“是拆迁的事?”
他沉默着。他没看叶子的脸。
“我们一块,咱,就是死,也在一块,青生啊,青生……”叶子抽抽搭搭,手在脸上抹拉着。
牛青生的脸开始扭曲并耷拉了,不屑和厌弃仿佛从晃动的门牙就要扭曲着挤出。他的妻子看到这已是熟悉的丈夫所能容忍的极限快要迸出,她选择了沉默。只是她的身体是根本没打算走的站在那儿。
他从牙缝低低地迸出:“快滚!”
叶子眼睛大了,她用泪眼看着自己的丈夫。
“你要是懂事的话……马上……给我走!”牛青生又用凶狠的口吻驱逐着。
叶子迟疑地看着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牛青生,你可以告诉我准备干什么吗?”
牛青生低着头手又无力地做做驱逐的手势。
他已经懒得说话,懒得动弹了。但他还是用嘴挤出一句话宽慰他的老婆:“放心,没事。”
看到尚未缓过神儿的女儿依旧看着他,他艰难地咧咧嘴冲女儿挥挥手说,“嫚儿,懂事,带你妈走。”
然后身子一歪,仅仅就这么一会儿,牛青生躺在沙发上睡了。
(八)
当牛青生身子陷进塌陷的沙发,梦却把他托起来了。
梦就像个捏造事实的法庭,把一些相关的甚至不相关的内容往一个案卷里凑。
牛青生起先梦到的是一个女人把被子给他盖上了,但这个女人像是焦点渐渐合焦的脸——对准了,清晰了,却发现不是自己熟悉的叶子。是另外一个女人。
这女人陌生且熟悉。陌生是因为这段记忆他自己挂上了铅封,熟悉是因为他与她曾有过灵肉纠葛的肌肤之痛。他们由一番暧昧而发展到相互迷恋,甚至因床事的沉迷而发展到难以割舍,却在因误会而形成的僵持中错过了。他熟悉她的身体,却永不熟悉她鬼魔一样飘忽不定的心。他梦见自己的门牙掉了。一张满脸横肉的男人在冷冷地嘲笑他。他甚至准确地记住他的面孔和他说话的语气。他说话时嘴唇没有张合,声音仿佛是从嘴唇后面的牙缝挤出来的。他梦见自己的彩票中了大奖,奖金是他认为一辈子吃不完也花不完的一大笔钱;他得到了他应有的房子;他用中彩票的奖金雇人把自己的屈辱报复回来了;他有了钱;他的气质和气节因为有了钱而不同于以往让人刮目相看了。那些打手在告饶的时候已没有往昔的阴冷和趾高气扬的跋扈。他是冷眼看待他们的;他仅仅用嗤之以鼻的神情,冷漠地看着他们满脸血污,看着他们哭嚎着乞求他的宽恕。他那是甚至蔑视轻视他们了。他认为蔑视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他转身便与自己的妻子开着汽车扬长而去。
“青生!青生……”
牛青生隐约听到有人仿佛是用喜极而泣的声音在叫着他。梦里他渐渐听出是妻子——叶子。当他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他试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眼前的妻子分明不是喜极而泣,而是紧张、错乱地在摇晃拖拽他的身体,他身体立马警觉地坐起来了。
“青生啊!外面在喊话呢!”叶子说,一面双手紧掐着他的衣袖,惊恐失色地摇动他。
“我们怎么办啊?”
牛青生蒙了。他的心脏突突地跳着。他起身的时候关节僵硬,肌肉酸痛。当他摇晃着站起来时,眼睛透过门缝他还怀疑,在这微微透亮的天色里怎么会有拆迁强迁的可能?
可是,当牛青生撇开惊惶失措的叶子,独自走出屋门,走向院门,抬头就被院墙上方一个黄色的铲车的车顶捋直了眼睛。他甚至看到铲车司机头顶上的毛发和铲车烟囱喷出的一缕缕浓烟;他听到发动机在院墙的后面低沉地响着;他正疑心自己是否看错了。随即是轰隆一声,院墙突然坍塌,一道院墙被豁开了口子,铲车宽大的身躯大摇大摆地迈进了院子。
他家的狗突然叫了起来,好像以前被轰隆隆的铲车吓畏了,汪汪汪几声过后,狗的叫声被堵在了嗓子里,呜呜啦啦,呜呜啦啦,是在告饶吗?牛青生照狗肚子上踢了一脚。
抬起头,牛青生看到一些深蓝色的大盖帽和穿迷彩服的人影晃动在铲车的后面。他知道他们此时是动真格的了。面前的大铲车面无表情,像撕扯着布匹一样,继续豁开着院墙;院墙里的碎砖仿佛被捅破的肚子哗哗地倾倒出来并掀起了尘土。
随着铲车对院墙的豁开、撕扯,牛青生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看到了几盏车顶上亮闪的红灯和几个穿西装的手拿对讲机的人。一些辨不清身份的人影随着哗哗倒下的墙砖,乌鸦鸦的又裸露出一片。高大的铲车冷漠又狰狞地推进,铲车的翻斗像一张吞咽砖瓦石块的大嘴,在吞吐着院墙,走近他身后的房屋。
牛青生随着裸露出全身的铲车后退着。
他看到院内种植的枣树,杏树,还有地上种植的大葱,青椒,被铲车刚硬的翻斗和宽大的轮胎无声地推倒碾压时,他知道这已是毋庸置疑的强行拆迁了。他知道他商量的余地已被人没收;他两次无由的挨打只能按自己倒霉处理了;他对家庭利益的苦斗与坚持,即将随着铲车的推进而变成惨埋在地上的瓦砾。他认为他已经被剥得干干净净;既然屈辱已没有了退路,那么活下去已没什么改善的价值了。他只能在这目睹的扒家、拆房中显示绝望中最后一搏。
那些帽檐和迷彩服在推倒院墙而掀起的尘土中隐现着。
牛青生回身用手拨开堵在门口跺脚大哭的妻子、女儿,两眼很快瞄上案板上的菜刀。他在抄起这把菜刀时,他的大脑、心脏仿佛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一搏而捋成了直线。他那时没有利益也没有了条件。他回身冲出屋门时,他的身子因叶子和女儿恐惧而生拉硬拽让他踉跄了几步。
他两步攀上挖掘机的踏板,一股即将喷射的怒火令他一手抓住驾驶室的把手,一手挥舞着菜刀并叫嚣着用菜刀砍碎了玻璃。牛青生甚至不知自己声嘶力竭的叫嚣了什么。当他知道身后有人试图用拽他的裤腿阻止他时,牛青生挥舞的刀锋在刺破云层的晨光中闪耀着骇人的光亮。于是没有人再尝试阻止,铲车司机也停下车子以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神情从另一扇车门仓皇逃窜。
拆迁的现场开始慌乱了。从铲车上跳车的司机惊魂未定地看着牛青生。诸多警察、城管和穿迷彩服的人选择了观望。
针对一场由政府督导的极具震慑力的拆迁行动来说,牛青生用这种绝非虚张声势阻止了铲车的强行拆除。当阳光穿透云层将光投射在米黄色的铲车上时,牛青生站立在铲车上的身躯也沐浴了阳光。
此时,站在铲车上的牛青生,他抓住车门的手和握住菜刀的手依然在抖动着。当他因为铲车的高度眼睛可以毫无阻拦地扫视人群时,牛青生的心脏突然在一张脸上停滞了。在他认准那张横肉松弛的脸下竟然身着一身肩章上反射银光的制服时,牛青生的脸开始抽搐并扭曲。他甚至感到一股云烟卷滚的绝望。他看一眼女儿,妻子。在他关上车门铲车开始吼着嗓子驶向人群的时候,人们惊骇了。
警察、城管,穿迷彩服的人,在冲向他们的铲车面前纷纷四逃。
东摇西挪的铲车开始冲向警灯亮闪着的警车。
那时的牛青生已从密闭的车门听不到什么了。他只看到一辆辆警车在翻斗和车胎下面惨叫、后退、扭曲。当铲车宽大的轮胎跨上并碾下这些警车导致牛青生身子在车内倾斜时,牛青生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舒心与酣畅。
车身下面警灯破碎,警车碾压下的塌陷和警车玻璃破碎的爆响声让他兴奋,几辆警车还有高出警车车身的面包车,在他脚下甘愿受辱,俯首称臣。然而在他碾压这些车辆,兜一圈又掉头用另一只大脚开始从面包车碾压时,牛青生的身子随着铲车车身的倾斜、侧翻,从而笨重地倒下了。
作者简介:王海波,网名蚂蚱眼,1963年出生于青岛。现青岛市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摄影学会理事。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散文百家》《青岛文学》《青岛日报》等发表过若干作品,中篇小说《大茶壶》获首届齐鲁文学奖。出版过摄影集《青岛屋檐下》,策划主编过青岛散文集《老城回声》等。
原载 杜帝语丝
2025年01月17日 13:43 青岛
蚂蚱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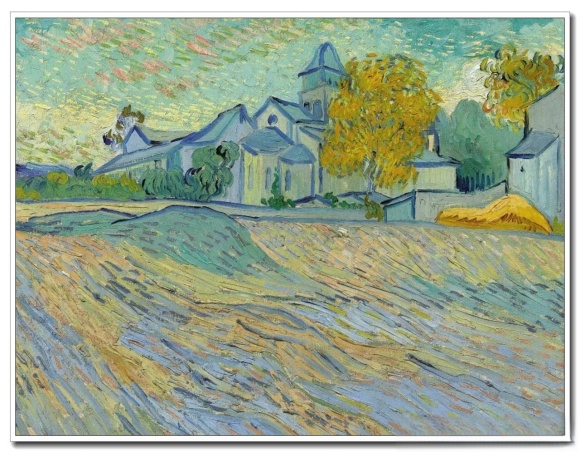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