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诸城文化志》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臧克家开始发表新诗。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王统照的资助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结集出版。”
臧克家(1905~2004)是诸城市吕标镇臧家庄人,《烙印》是他的诗歌处女作。我案头的《烙印》是上海开明书店的再版集子,发行者为书店代表人范洗人,集子出版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也就是1934年,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四版,也就是1948年。之前,《烙印》曾在1933年上半年第一次出版,很快得到茅盾、老舍等大家好评,臧克家成为当年“文坛上的新人”。1934年4月开明书店再版,附有闻一多的《序》和臧本人的《再版后志》。《序》作于1933年7月,《再版后志》作于1933年11月。
1929年夏天,臧克家考入青岛大学补习班,学习之余开始发表新诗(志言1932年始发新诗恐有误)。1930年夏天,他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师从闻一多,开始大量发诗。从1930年入学到1934年毕业,共出版《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两本诗集。
在青岛师从闻一多的四年,臧克家经常到闻一多的小红楼,现今青岛海洋大学东北角闻一多故居,探讨诗歌与人生。2017年初秋,我来到锁住的故居门口,写道:“门关着。入户上二楼翻看或揣走几本闻先生收藏的古籍善本,或如当年臧克家那般进屋,与先生对吸红锡包,谈论诗歌等恐怕是当今奢侈的事儿。时间偷走很多东西,包括闻先生坐的那把让他从新月派诗人往文化学者转型的扶手椅。时间也会放过一些东西,让其不老。”臧克家无疑是闻一多最喜爱的学生之一。1933年7月,闻一多为臧克家《烙印》作了序,从分析第四首诗《生活》开始。《生活》这首诗并非诗集中的优秀作品: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灾难是天空的星群,
它的光辉拖着你的命运。
希望是乌云缝里的一缕太阳,
是病人眼中最后的灵光,
然而人终须把它来自慰,
谁肯推自己到绝境的可怜?
过去可喜的一件一件,
(说不清是真还是幻)
是一道残虹染在西天,
记来全是黑影一片,
唯有这是其实,为了生活的挣扎,
留在你心上的沉痛。
它会敎你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
从一点声响上抖起你的心,
(哪怕是春风吹着春花)
像一员武士在嘶马声里想起了战争,
那你再不会合上眼对自己说:
“人生是一个无据的梦。”
更不会蒙冤似的不平,
给蚊虫呷一口,便轻口吐出那一大串诅咒。
在人生的剧幕上,你既是被排定的一个角色,
就当拚命的来一个痛快,
叫人们的脸色随着你的悲欢涨落,
就连你自己也要忘了这是做戏。
你既胆敢闯进这人间,
有多大本领,不愁没处施展,
当前的磨难就是你的对手,
运尽气力去和它苦斗,
累得你周身的汗毛都擎着汗珠,
但你须咬紧牙关不敢轻忽;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你活着带一点倔强,
尽多苦涩,苦涩中有你独到的真味。
1933年4月
闻一多的《序》不长,又因对时下的诗歌具有鞭策意义,因此,我们从头读起:
克家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来,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妨明说,《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质,他的好诗,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时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energy)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稜,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境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会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
扪一下脸,
来一个奇怪的变化!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像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闻一多谨识1933年7月
闻一多认为,诗是“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不虚伪,不唉哼,不嚷嚷,是“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诗人不靠市价作诗”。那么,DeepSeek如何评价《烙印》这个集子呢?
它也从一首诗展开,让我们读一下《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他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他把头沉重的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他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他抬起头望望前面。
DS还为文章拟定了个题目:泥土里开出的血性之花:论臧克家《烙印》的苦难美学:
1933年出版的《烙印》像一柄锋利的犁铧,在中国新诗的沃土上犁出了深重的沟壑。臧克家以山东农民的赤子之心,将新月派的形式美学与底层生命的粗粝质感熔铸成独特的苦难美学,在“现代派”的颓废吟哦与左翼文学的标语口号之间,开辟出一条直面现实的诗歌道路。
一、青铜器般的生命质感
《老马》中“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具象描写,赋予苦难以青铜器般的物质重量。臧克家摒弃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滤镜,用雕塑家的刻刀将农人的手掌纹路、车夫的汗盐结晶、难民的褴褛衣衫直接镌刻在诗句里。“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难民》),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意象组合,让生存的艰辛获得了青铜器纹饰般的永恒性。
诗人对苦难的凝视具有考古学家的精确:“黑夜的沉睡如同磐石”(《失眠》),“铁门的响声截断了最后一人的脚步”(《贩鱼郎》)。这些凝固在诗句中的苦难瞬间,构成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化石。当徐志摩在康桥柔波里采摘星辉时,臧克家正用诗笔丈量着中原大地的龟裂田畴。
二、苦难叙事的双重维度
《炭鬼》中“把死后的抚恤和妻子的泪水称了又称”的矿工,既是具体的历史存在,更是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臧克家的现实关怀始终保持着人类学的观察距离:他写老马“横竖不说一句话”,写难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叫不出名字”,这种克制的白描反而让苦难获得了史诗般的庄严。
在《天火》中,“等这群罪人饿瞎了眼睛/认不出上帝”的预言性书写,将个体苦难升华为对旧世界的审判寓言。这种双重叙事策略使《烙印》既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口号式控诉,也有别于现代派的颓废独白,而是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生长出象征主义的根系。
三、苦涩土壤中的诗学抵抗
闻一多提倡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烙印》中转化为更具韧性的形式探索。《歇午工》里“鼾声扣着呼吸的节拍”的句式结构,《老马》中“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动词锤炼,都显示出诗人将格律约束转化为艺术张力的自觉。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形式追求,恰似老马沉重的轭下依然保持着行走的尊严。
在“现代派”诗人沉迷于“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戴望舒)的私语时,臧克家选择了“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的公共书写。这种选择不是艺术上的退守,而是将个人诗情融入民族命运的勇敢突围。《烙印》中的每一声叹息都通向大地,每一次疼痛都指向黎明。
当我们在空调房里翻阅这本泛黄的诗集,依然能触摸到诗句中未冷的血温。臧克家用《烙印》证明了:真正的诗歌从不对苦难背过脸去,那些深陷泥土的脚印,恰恰丈量着精神的海拔。在这个光滑的消费主义时代,这种带着血丝的写作伦理,依然像北斗星般指示着诗歌的尊严所在。
2025年2月6日
“真正的诗歌从不对苦难背过脸去”——DS,机器人对一本诗集的理解。
臧克家在《再版后志》写道:“老早心里对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于今看来,当然觉得还很不够),再就是写人生的真理,《烙印》里的二十六首诗,确也没出这个范围。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这些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
好一个“都是先流过泪的”,不管什么主义、潮流、现象,泪水的现实意义在哪里,诗歌的文学价值就在哪里。
李言谙
2025年2月8日
2025年笔记(28)
41
2004年6月,《高密人》创刊,由高密文联主办,适逢高密撤县设市10周年。至2007年,《高密人》共刊10期。
创刊号《卷首语》云:“岁月悠悠,征途漫漫,上下求索,任重道远。为进一步激发全市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干事创业、进位争先、建设强市的热情,市委宣传部掀起新一轮宣传热潮,市文联在省、潍坊市文联和高密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帮助下,适时编辑出版了《高密人》一书,以不同的体裁和图片等形式,从不同角度热情讴歌全市三个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真切反映百姓生活的可喜变化,向撤县设市十周年这一隆重节日献上一份厚礼!向全市人民奉献一份真诚!
高密发展看今朝,展望明天更美好。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弘扬主旋律,歌颂新高密,为全市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为进位争先建设强市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永远铭记关注《高密人》发展的社会各界领导和朋友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以百倍的努力,勤奋的耕耘,让《高密人》成为高密人民真诚的朋友!”
本期《高密人》刊发文学作品如下:
“设市十年赞”刊诗词鹧鸪天·高密设市十年赞(刘宪韬),设市十年读高密(宋林茂),五律·春望(赵仁东),撤县设市赞(罗相诗),高密新纪元赞(鞠维积),沧桑赞(尚希魁),家乡巨变感怀(韩元金)。
“诗词天地”刊梅花评传(外一首)(栾桢),破阵子·喜闻神舟五号飞船胜利返回(万兆金),祖国山岳颂(外一首)(鹿书信),思乡(豪杰),牵牛花(外一首)(陈雪梅),长城(外一首)(李丹平),寄语五月所诞生的(韩英梅),清晨那一刻宁静(赵桂珍),春梦(张进),致诗友(李艳)。
“小说世界”刊答谢(魏廷松),大头兄弟(李大伟)。
“美文欣赏”刊往事漫忆(栾纪曾),心灵的飞跃(李储坤),刮目看儿子(彭来德),穿越死亡之海(刘建敏),爷爷和毛主席的一张合影(王学丽),那条街(隋金川),父亲的嘱托(王有志),慈母手中线(楚绍山),我学英语(刘爱红),老马(于成德),歌声与鲜花的世界(董维欣),游峡山(宋亮),故乡的黄昏(李岩),育儿手记(吕晓红),秋夜诉(山石),二月里的回忆(李卓强),输赢得失之间(董玉霞)。
李言谙整理
2025年2月9日
原载 阿龙书房
2025.2.8 20:26 山东
2025.2.9 21:02 山东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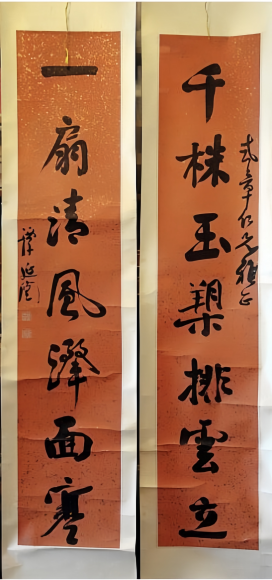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