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处地坛公园,很早很早就知道了,但我曾经很久没去过地坛。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十四岁,是奔着天安门广场那血红色的城楼去的。那是个狂热且无知的年代。以后又去了多次,十几次或上百次,十八九个景地儿都去了,以致再去时工作之余暇常常站在街头迷惘四顾,这京城还有非去不可的地儿吗?可是我就是没去过地坛。
十多年前,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便萌生了要去地坛走走的念头。去地坛看什么,不知道,也许会碰见史铁生,为了见史铁生一面?也不是。史铁生的照片我也见过,一个普通相貌的中年男人,照片的边角可以看到轮椅的扶手。只是那双眼睛,似乎透出一股深邃的光芒,触动我最多的是史铁生的文字,那字里行间仿佛有一股气场,透出他的精气神儿,那是一种说不清楚,写不明白的博大与坚韧。为了捕捉这一刻灵魂的感知,我对我自己说:我要去地坛,可是我又去了北京许多次,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急急促促。有一次坐在回青岛的班机客舱里,浏览一张报纸,突然看到史铁生的名字,心里咯一下,自言自语了一句,唉呀,忘了去地坛了。事实是以后又去了北京多次,终究没有去地坛。又有一次晚上从青岛飞北京,工作结束到深夜二点多,就在人家的办公室睡下了。接近中午时醒来吃了个便餐,接待的朋友问:今天回去还是在北京走走再待一天?我挥挥手说:马上订票,北京没什么走的地方了,直到飞机落地,夕阳正在落山。突然想起,为什么这么匆匆促促,怎没想到去地坛呢?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去世了,我的懊恼一下子涌上来了。那几天青岛的风特别刺骨,风穿过树林,在楼洞间呼呼哀嚎,阴沉沉的天空似乎咧开了那张难看的嘴巴,在嘲笑我什么……我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行字。史铁生,值得尊敬的一个人。他走了,我还去地坛吗?
又是一年过去了,忙忙碌碌的竟没有一个机会和理由去北京了,唉。
壬辰四月上旬,青岛还有点冷,大庙山下街头花园的迎春花的枝头刚刚绽开鲜嫩的花骨朵儿,而在北京的上午已是燥热燥热的了。我把春衫绒裤都脱了,沿雍和宫大街往北走,十几分钟远远就看见了地坛那鲜鲜翠眼的大牌坊,身上已经汗流浃背了。
此时,地坛于我仿佛是一个圣地,我的脚步怯怯地停了下来,站在牌坊下向东望去,那甬道笔直笔直竟然那么长,有三百米或四百米,似乎看不到尽头。我在想这笔直悠长的祭地之道就是史铁生的救赎之路吗?除了《我与地坛》,史铁生在好几篇小说散文中都写到了地坛,这座荒芜废弃的古园子。那“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而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他在写《我与地坛》时,用了十五年的思绪,也就是十五年间他在地坛的甬道上树林间,草丛里慢慢地读书,思考,救赎自己,当他使自己得到救赎后,他的德行和文字又救赎了很多人。我记得在哀悼他去世的网络文字中有一句特别深刻。“他的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他的作品展现了他那高尚坚强的灵魂与命运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他的精神魅力像一朵永不凋谢的生命之花,在这个冬天得到了永存。”深刻打动了我的也是他的文字中散发出来的那些平实、宽厚、坚强和乐观那这一切,都与地坛有关。他的很多文字都是从地坛的道与墙,树与草,影与气中悟出来的。
现在我站在地坛那朱红的城门口,那石路笔直,那行道树也笔直。周六的上午,甬道上没有几个游人。牌坊高高大大竖立在那儿,竟将马路上的喧嚣挡住了,一边车水马龙,人流攘攘,一边沉静无声,微风轻荡。地坛果然给人一种肃穆的悠然。
那甬道上还有史铁生的车印,那林草间还有史铁生的气息吗?
二
我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有好多遍了,史铁生的文集我有好几个出版社的版本,每一本都有这篇《我与地坛》。地坛早已种在我的脑子里,有时一闭眼,地坛就在一辆轮椅的车辙痕中摇来摇去。那古园的生机,历史的苍凉总有许多画面闪过。
现在我已踏入地坛,我站在西门城垛入口,前行和左右的甬道都是那么笔直,石砌的甬道,没有一丝杂物,临近中午的阳光映得石面上闪着光亮,使得我的眼睛微睁着不能全部张开。那几排四百多年的老柏树在哪?那石门的祭坛在哪个方向?那几棵在春天会开一簇细小而稠密黄花的栾树呢?斋宫是右手边上这一幢灰色的房屋吗?
史铁生说,因为地坛,“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他在二十多岁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陷入了人生的不幸与苦难。他在生与死的纠结中进入了邻近的地坛,这荒芜却并不衰败的古园子。一朵如小雾的蜂儿,捋着胡须的蚂蚁,爬得不耐烦的瓢虫,一只蝉脱,甚至一滴露水都在经历着生命的自然法则。在地坛四季的风物顽强的表现中,他悟透了生命的活力,摆脱了一件件残疾后必然去死的理由。没有理由的死并不能解决怎样活得好,他还是将轮椅摇进地坛,顺着颓废的城墙慢慢地边摇边想,窥察自己的心魂。史铁生在文中说: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又没了你的时候……迷惘和惆怅中他在园子里观察、聆听和思索,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与时间、历史,与自然和生命进行缠绵不尽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战胜了旧我,获得了新生。
我沿着地坛的石板道在走,石板道平滑整齐,拐弯的地方棱角分明。地坛里大多地方都是方方正正,“天圆地方”哦,这是地坛这园子的特征。祭坛的大红石门关着,我撞了两下,大门纹丝不动。史铁生在他的文字中说:祭坛有点高,轮椅上去不方便。除了祭坛,地坛里每一处地角儿他都逗留过许多遍。我再往前走,几排条木座椅,我坐了一会儿,树下两个石凳,我又坐了一会儿,这些椅凳史铁生不会坐过,但肯定会抚摸过许多遍。我在想象他坐在轮椅上陷入沉思的样子。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使他一举成名,三年后《我与地坛》一文发表,使他在文学界备受瞩目。但随即人与文学关系的低潮汹涌而来,逼迫史铁生再次将轮椅摇进地坛,陷入更痛苦的思考。社会的势利性,人与人关系的庸俗性,时事面前的犬儒和猥琐,对于史铁生这样一个实诚而纯粹的人越明白就越痛苦,越难以言述。云南的《大家》杂志主编在他去世后说:八十年代末期,他的长小说《务虚笔记》写完,被《大家》看中,《大家》明确许愿,这篇小说只要在《大家》发表,当年的“大家文学奖”肯定给他。十万元啊,等于现在的一百万元还多,但最终《务虚笔记》在《收获》发表。据了解,《收获》的稿酬不及《大家》的十分之一。还有一位著名作家在悼念他的仪式上说:“史铁生不像一些人,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中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他的人格完全和写作融为一体,他不是一个演员。”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47岁又患上尿毒症,直至59岁因脑溢血去世,他与病魔抗争了38年。我读他的文字更多感触的是太多的悲悯性思考,一些有关死亡的哲思话题令人震撼。在他患病后的前十五年,他从地坛里的生物及人的活动悟出了自己的心性。地坛的思考使他成了当今作家群里人格与作品最值得尊敬的人。
我已经顺着地坛的石板道走了一圈,高大的柏树林抛下的阴影带给人些许清凉,一簇簇不知名的灌木丛中竞相开着黄色和白色的花。在东北角一棵粗壮的栾树下有两大抱银白色玻璃纸缠绑的鲜花,花瓣有点枯萎,但颜色仍然鲜艳。我围绕着树干转了两圈,没有缎带和一纸文字。我突然想起史铁生去世前曾要求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地坛。这些鲜花莫不是崇敬他的人们对他的祭扫。前两天是清明寒食啊,地坛正是史铁生自己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地。我蹲下身子,用手里的纯净水洒滴在花瓣上,双手合十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在地坛里慢慢走着,走得很慢。前面是一辆轮椅,坐着一位白发的老人,轮椅摇得很慢,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史铁生,是他摇着轮椅在园子里慢慢走,慢慢地思考。他的地坛文字呈现了他的意志和毅力,表达了一种不苟且,有分寸的慈悲与怜悯,抗争生活的男女,弱智的女孩以及地坛里的草木和尘土,那草叶上的一滴溜儿圆圆的露水,他都给予生命的问候,给予宽容和爱怜,给予上帝般的关切和微笑。在地坛,他获得了初始的智慧,悟透生死,洞悉人生,在病痛中的思考,进一步升华了对真理的追求。我所在的省作协的主席作家张炜说过:“网络时代繁衍出多少文字,纵横交织的声音震耳欲聋,却难以掩从北京一隅的轮椅上发出的低吟。”我感觉史铁生简洁、通透,深邃且独树一帜的地坛文字和思考当会更深远地嵌入一代人们恒久的记忆中去。
“死是一件无法急着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能完全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地坛文字中的重要一句话,他有诗句作响: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我拍稳
躲开哀悼
挽联、黑纱和花篮
最后的路程
是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
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
我已跳出喧嚣
谣言,谜语和幻影
最后的祈祷
是爱地重逢
地坛的平板石路有点长,空气中的雾霭在跳跳闪闪,那密密的老柏树林发出沉闷的呻吟。史铁生的爱地不就是这片园子吗?斯人已逝,空余人们不尽的叹忧与怅惘……
三
自从在北京南站下车伊始,撞入眼帘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是人,人挤人的肤色、模样,南腔北调不同的人。
走进地坛后,明显的是人少多了,少得甬道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背影。园子里大多木椅石凳没有人坐,走了一圈,有点累乏了,我找了片树荫的草地躺了下来,眯着眼在想史铁生。
周围寂静得很,没有鸟叫虫啾,空气似乎也飘荡着一股惆怅。
史铁生年长我一岁零十个月,十七岁插队去了遥远的清平湾。21岁时因双腿疼痛返城看病,当时他的父亲搀扶着他走进医院,治疗未果,他是被担架抬回家的,下肢高位性瘫痪,行走从此成了他的梦想。最初他家住在前永康胡同,后来搬到雍和宫大街26号。这两处地方都邻近地坛,在街道工厂打工的时候是他最苦闷的时期,七八年时间闲余无奈之际只好摇着轮椅走进地坛,那时地坛荒芜得很,除了偶尔几个穿园而过的行人,很少游人。风声,雨影,枝曳,草鸣,伴随着他苦苦思索。正是地坛这特殊的灵性,启了他的人生顿觉,大自然的永恒敲开了他的心扉。在学外语未果后又尝试文学写作,五六年时间大量的练笔,终于于一九八四年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并获全国奖,给了他人生追求一个肯定的回答。又三四年过去了,一九八八年《我与地坛》这篇15000字的散文发表震撼了中国文坛,揪住了千千万万颗善良的心。地坛的灵性罩住了文坛。此后他还是经常漫走地坛,既是轮椅的不便不能使他外出做客,休闲,主要是躲避社会的喧嚣。地坛给了他新的生命和新的人生以及非常人的思考。他在地坛留下的痕迹,估计在一两代人中间不会湮没。我曾上网搜索过许多有关地坛的帖子,不少网民到北京不去八达岭,也没去故宫,却到地坛走了走。地坛没有高大巍峨的建筑和景观物,除了红墙圈住的树草,没有纪念物,甚至带字的碑石。但很多人就是来走一走,感受一下史铁生。现在我就趴在地坛的草地上,放松着四肢,使劲嗅着草地的清气,感受着精神上的史铁生。
1998年春天,史铁生他47岁,截瘫26年后患上尿毒症,每天的定时血液透析,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抗争。他自己说有不少在透析室相熟的面孔,在某一天见不到了,而且不是偶尔几个人的问题。残弱的病体,使他极易受到病魔的摧残,住院治疗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家医院只有12间病房,他住过10间。2009年冬天,他患了重度肺炎,他亲眼看见透析自己身上血液的管子静止不动了,那红红的血一点一点变暗了,很快成了黑色,不少媒体发了史铁生病危的消息。疾病使史铁生悟透了生死,身体加倍的磨难,使他精神上的思考越发成熟和深刻。史铁生与死神可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用成熟睿智的文字与死神调侃笑谈。读他的文字从早期残疾人的肉身感受的悲悯情感到中后期关于人与自然,存在与死亡,相对与绝对的哲理思考,几乎每一篇都成了经典。我手里现在正在读的一篇,是发表在今年第一期《收获》上史铁生最新的遗作,题目叫《昼信基督夜信佛》,文尾的写就时间是2010年11月4日,距他辞世还有五十多天。“人的迷茫,根本在两件事上:一曰生,或生的意义:二曰死,或死的后果。基督教诲的初衷是如何面对生,而佛家智慧的侧重是怎样看待死。”“乐观若是一种鼓励,困苦必属常态:坚强若是一种赞誉,好运必定稀缺;如果清官总是被表彰呢,则贪腐势力必一向强大。”这就是史铁生留给我们的另一类悟透了的人生启迪。说实话,史铁生这等境界的禅言,我一时还读不懂,悟不透,思不清。我在想他的文字在那一种极端困境中是怎样一个字一个字思考成熟写下来的。后几年,由于频繁的透析,他那粗壮的双臂也失去撑挪的力气,以至不能自已调整轮椅里的身体。而他的精细文字却是一篇又一篇。他的《病隙碎笔》和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都是尿毒症时期写作完成的,似我这等悠悠常人真难以体会他那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
“道路的无限即是距离的无限,即是差别的无限,即是困苦的无限,幸而人之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也可以无限——唯其如此,无始无终的存在才不至于荒诞。”读到这儿,闭上眼睛,仿佛每个人影,每个情与物都沉寂在这地坛,耳边传来像史铁生写出的那个地坛园神说的话:“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那语音轻轻淡淡,在南边那一片密密的树林中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春日的地坛早已不是史铁生那些年漫游的荒芜的园子了,黄刺刺瓦下的厚重红墙,看不出斑驳的过往。行道两旁的柏树枝整齐有序,地面干净,草地清洁,几乎看不到小生物的蠢蠢欲动。风似乎也慵懒了,空气中显出祭地的宁静端庄,肃穆悄然……我拣起几片飘落的花瓣,小心翼翼地夹进手里的一本《史铁生文集》。
四
自史铁生去世后,我常常梦见他,梦见他坐在轮椅上在地坛树荫间缓缓而行。白昼读史铁生的文字,晚间很容易催生几多清晰难以忘记的梦,只有史铁生的文字才有健梦的魔力。
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一坐就坐了三十八年,可以说是大半生与轮椅为伴。他像贝多芬发生耳聋时一样,哭泣悲伤绝望,甚至轻生过,但他也像贝多芬一样:“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让他毁灭我!”以他的文字站到了中国文坛的一个制高点。他的肉身湮灭了,但他的超常思考通过他的文字扎实耸立在许许多多的人们心中。
坐在轮椅上的铁生,其一生过得落寞也过得沉重,患病后一二十年,经济拮据,生活困苦,居住条件也差。去世前一二十年,因文学创作改变了境遇,但因他的正直与操守,人品与文字的坚贞,只是稍微有所好转。但随后再患花钱如流水的尿毒症治疗,如没有他人帮扶,那困境几近无法言说。他的病不但制约了他个人的奋争也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母亲49岁就去世了,不能不说是史铁生病后的困顿对母亲的思虑极度压抑有关。但史铁生通过坚忍不拔的抗争随后也活得很“精神”,活得很有尊严。史铁生在他的文字中曾自陈:人生的价值在于超越那种低层次的生物欲望,升华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事实也正是,残疾的史铁生未免庸常,思想的史铁生却神采飞扬!俗身的史铁生没有站起来,精神的史铁生却用他的文字站得雄伟,站得高尚!站得别具一格,让许多人钦佩并且仰望。
地坛真的没有什么风景,除了墙和树,就是那平直的石道。史铁生常来地坛的时候,地坛是荒芜不堪的,却是各种野草杂枝散乱竞生的时候,看不到人生的前途,又严重拖累家人,使“母亲日渐憔悴”,坐在轮椅上徘徊在地坛甬道上的史铁生犹如行走在无望的地狱,他在地坛行走,在思考,在读书。他可能读过尼采,知道尼采的那句名言: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但是,熬过严冬的人并不一定都会感恩太阳的温暖;经历过地狱磨难的史铁生,因为超凡脱俗的思想,才“自地狱深处”发出如卡夫卡描绘的那种“最美妙的歌声”。
这也是一名普通作家渐行渐远,却令整个文坛扼腕叹息的原因。中国不缺作家,从北京到各省、市县养了一大帮体制内的所谓专业作家,有的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写不了几个潦草塞责的应景垃圾文字,却月月拿着足以醉生梦死的高额工资,享受无与伦比的高档福利。在史铁生逝前几年,多个作家为其谏言,寻求作家协会编制,为的是争取缓解史铁生患尿毒症需要大额治疗费的困境,却至死而无果。有一位知名老作家就此事在一次所谓大牌领导看望艺术家的座谈会上大骂:什么他妈的世道和体制,竟引起众多人共鸣。我望着地坛南隅那一片柏树林,那树枝密切,枝条摇曳,风呼呼窜过,仿佛那共鸣仍在轰响……我在读史铁生在一篇散文中记述:他的母亲去世十年后,他和父亲、妹妹去找母亲的墓地祭奠竟然没有找到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这意味着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删减为零了?”读到这儿谁人不潸然泪下。
我认识一个所谓作家,一生就写了一部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所谓小说,因攀缘官场混了个x级作家的头衔。碰见作家自谓自己是流氓,碰见流氓又自称自己是作家。实在混不下去,用官场黑钱出自费书。因为其心思全在利用官权上,捞了许多不义之财花不了,就天天摆席请客,前几年人不少,这几年只剩几个吃客陪着,打了十个请客电话,八个半全回绝。人还在世,文字早无路可走了,人缘也绝了,形同行尸走肉。而轮椅上的史铁生,形体去世了,但其思想却在许多人心里激荡。他的文字在时间空间中耸立如山。我走在地坛的甬道上,仿佛看到他的身影在前方疾行,他的语音在耳边喃喃娓娓。在这个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世界上,在人们日渐物欲化的心地里,唯有史铁生如铮铮骨气与地坛共生共存。我与很多京华人谈到地坛,对那几年的地坛庙会和这几年的地坛书市无不皱紧眉头,只有提到史铁生,才使地坛有了话头,是史铁生给这个四百年的祭地赋予了内涵。
写于2009年5月中旬于大庙山下
原载作者原创《无奈的思绪》(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
李鸿春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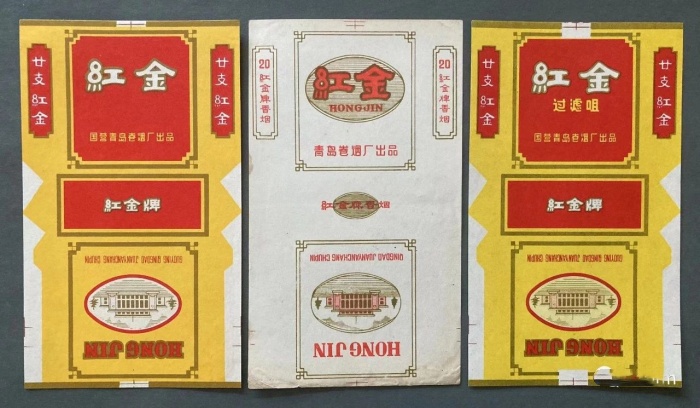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