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笔记(31)
44
“我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经过几十年的戏剧创作实践,水平逐渐提高,成果日益积累,现在,在学术上被评为相当于教授的一级编剧。回想起从写个十言八句的快板段子,连韵辙平仄都不懂,到写出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剧本,对所走过的40多年的创作之路,真是感慨万千!
1957年,我进入高密茂腔剧团拉二胡、弹三弦。1958年“大跃进”,我也解放思想,开始尝试写剧本,稀里糊涂地写出了剧本《妯娌俩》,没想到打响了,引起了县和地区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省里连办三年戏曲编导讲习班,都派我去学习。自此我开始博读群书,从现代剧本到古代元杂剧,从外国的莎士比亚到莫里哀,广泛阅读。白天上班,晚上演出,便在夜间读书,直至深夜两三点,一直坚持了三年,我这才像刚满周岁的孩子从学着挪步开始,一步步艰难地迈进编剧这道门槛。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的作品几乎全是农村题材的。因为我出生在农村,血管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农村的事总爱装在心里,只要闭上眼睛一想,就能知道此刻乡亲们在干什么想什么。当然,光靠这个不行。作为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剧作者,没有什么比改革大潮中的农村新的变化,农村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更能牵动自己的神经,吸引自己的目光了。尤其近几年,农村的变化很快,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变,一年不下去就感到陌生了。因此我经常往下跑,直到退休后还到昌乐县城关镇挂职副镇长一年。有的专家说我的戏所以“火”,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扎实的生活基础。这话不错。我体会到,写戏把握好“思想+生活+技巧”这三大要素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和百姓的心贴在一起。只有做到这一点,即是写配合形势的“宣传戏”、“行业戏”,也能写出剧场效果和艺术生命力,阐释出新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唱响时代的主旋律。我创作的大戏《盼儿记》之所以能够连续上演近千场,不少观众连看多遍,与剧中人物一起畅怀大笑,一起潸然泪下,就是因为这个戏通向了农民的心灵深处。
然而,在我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并不全是“柳暗花明”,也有“山重水复”。所经历的磨难和艰辛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3年,我写的《娶女婿》,开始演红了山东,又北至辽宁南到广西,许多剧种移植演出,连周恩来总理都陪日本客人看过这个戏。可没想到,不到一年,上头竟点名要对该戏进行批判。这使我彻夜难眠,心都有碎了的感觉,曾发誓搁笔不再写戏。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重新操笔写戏,创作进人盛产期时,却又赶上了戏剧普遍滑坡,一年忙到头,稿纸用上一大摞,写出的戏却成了嫁不出去的闺女。找家刊物社发表,全国有几个戏剧刊物?找剧团吧,多数又不景气,你陪着笑脸送上本子,人家却一脸难为情,只说研究研究,就没有了下文。往后路怎么走!真是苦恼极了!在极度苦恼中,自己也渐渐咂摸出了味道。人家剧团对你一个“大”编剧的本子为什么不热情?关键是你写的和人家所要求的,接不上茬儿。这使我体会到,在剧本选择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常年在基层为群众演出的剧团,观众需求什么,他们最了解。于是,我把两眼盯在刊物上,转为积极为基层剧团的需求写戏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如配合农村青少年教育的《为了明天》、宣传计划生育的《盼儿记》、歌颂基层干部反腐倡廉的《碧水长流》等多出所谓的“宣传戏”、“行业戏”,不但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上级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赞扬与支持。演出到处包场,剧团盛演不衰,大大增加了经济效益。这样,我面临的窘境就变了,过去是我求剧团演我的戏,现在是剧团求我为他们写戏,我写的戏成了抢手货。也就在这段时间,我写出了多部戏剧和影视作品,连连在省和全国获奖。
在戏剧创作上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点成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共潍坊市委副书记郑金兰和市文化局局长王振民同志。我的多部重点作品都是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从我深入生活的安排到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的加工修改,直至戏的排练演出、影视拍摄,他们都关照得非常周到。我的多部作品的成功,都倾注了两位领导的心血。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艺创作室对我的全力支持,我也永记在心。另外,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剧协住会主席张云凤老师为我的创作付出甚多,我写的《盼儿记》,是她亲手指点操作,请国家著名专家帮助加工提高,直至亲自带队晋京演出打响。从此,使我的创作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原《戏剧丛刊》主编宋云峰老师曾手把手教我写戏多年,有一部获奖作品是他同我合作而成。在此,我对二位老师深表谢意。
这个集子是我获奖作品中的一部分,是潍坊市文化局帮助策划出版的。文化局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我十分感激。另外,出这本书,我的朋友鲁鸿恩、王汝凯、刘成湘、曹云明、吴超凡等都关心备至,竭尽付出,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牟家明
2005年9月10日”
以上是高密籍戏剧作家牟家明为自己的著作《牟家明获奖剧作选》写的《后记》。我在某个圈子询问牟家明是高密哪儿人时,王建亭说:“律家村东的大周阳。”毛志华直接发来了牟家明的简历,我问毛志华是否了解牟家明去世的具体时间,他说:
“目前没有确切资料显示剧作家牟家明具体的去世时间,但据相关资料推测可能已去世多年。据记载,牟家明曾生过大病,做过两次手术。”
《牟家明获奖剧作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2006年2月出版,印数1000册,342千字,山东省水文仪器研制中心印刷厂印刷,书籍包装十分业余,开胶脱页严重。
牟家明的书由王振民作序。除了《序》和《后记》,全书由8个剧本组成,分别是:碧水长流(大型现代地方戏)、根的呼唤(大型现代地方戏)、盼儿记(大型现代地方戏)、盛世硝烟(大型现代京剧)、陈少敏三请徐公(大型现代京剧)、出嫁(大型现代地方戏)、瓜果飘香(大型现代地方戏)、财神女婿(大型现代地方戏)。
查证得知,牟家明是高密市密水街办大周阳村人,具体为周阳三村。大周阳村庄大,由四个村子组成,分别为周阳一村、周阳二村、周阳三村和周阳四村。周阳三村在村庄西南角,牟姓是三村的第一大姓。由张家骥主编的《高密村庄大典》记载:大周阳曾是古代驻兵屯粮之地。村后曾有平安寺,住有习武和尚,村东有烽火台,村南建有驿站和尼姑庵,住有尼姑。后有“南站(兵站)北庵(尼姑庵)”之说。村西南角有古井一口和舂米用的石臼一个,此井久旱不干,井水伸手可取,味道甘甜,被称为“龙湾井”,历史古老,无人考究。1964年在北庵地段出土过南宋年间韩世忠元帅的印章,南站地段挖出过陶土、瓦砾和灶灰等。
据田绍义主编的《高密古树名木》记载:大周阳村现有古槐5棵,树龄在280-500岁不等。其中周阳一村一棵,周阳二村一棵,周阳三村一棵,周阳四村两棵,不知这些“古物”是否安好,抽空得去一睹为证。
说起古树名木的保护,在高密不能不提一个人的鼓与呼和他由爱而生的著作。
李言谙
2025年2月13日
原载 阿龙书房
2025.2.13 14:06 山东
45
李章合在“笔记44”留言:“说起古树名木的保护,在高密不能不提一个人的鼓与呼和他由爱而生的著作。李储坤,一位有故事的文化人,他为保护高密的古树名木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其事迹应被后人铭记。”
是的,古树名木是组成故乡风景的重要元素,有和没有不一样,多和少不一样,它们是故乡情怀的延展和守望者身影的回顾。李储坤,高密古树名木保护的首倡者,虽然去世多年,人们依然记得他。翻开《李储坤高密古树名木速写》大型画册,当看到第75幅周阳三村国槐速写画时,我心里想,假如李储坤和牟家明在路上相遇,哪怕不曾认识,也当在这古槐下会心一笑,仿佛见过。
周阳三村300多年树龄的国槐立于岁月之中,永不凋残的身姿得益于一张钢笔速写画页。它在我面前大度16开的画册中风雨无虞,忧喜无伤,不再被时间、空间困扰,尽享艺术的筋骨之美。从1991年开始,李储坤走遍高密的29处乡镇,考察古树名木,找到它们,画出它们,写下它们,为所遇古树名木建立档案,呼吁保护这份珍贵的自然遗产,直至去世。
2016年6月,《李储坤高密古树名木速写》大型画册出版,高密市美术家协会《李储坤高密古树名木》编委会策划编制,宋利华主编,从200多幅速写中选取了108幅,涉及国槐、毛白杨、板栗、楸树、银杏、黑檀、皂荚、麦松、赤松、圆柏、龙爪槐、柳树、胡桃、麻栎、流苏等树木品种。宋利华在画册的《序》中说:“先生留下的速写作品,多为单色,以钢笔写就,参以石刻、版画以及中国画的写意技法。作品形式多样,无重复枯燥之感,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真情流露。正是这种自然,让我们看到了这批速写作品的价值所在以及透过作品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
古树名木速写作品大型画册的出版是在李储坤去世六年后(册中将李储坤去世标记为2006年7月疑有误,应为2010年7月)高密市美术家协会的义行,亦如李储坤呼吁的保护古树名木,乃情怀之举。高密美协《李储坤古树名木》编委会在《后记》中说:“这是一部厚重的无字史书。今天,我们整理出版,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后世的启迪。名园易建,古木难求。时间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真诚地传承是后辈人的责任,无谓地损坏将是历史的罪人。感谢李储坤先生用心血幻化成的绿色之歌。”
2007年4月,李储坤散文集《心灵的飞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孙惠斌作序,刘扬、黄赞友、张志孝、刘炳文、荆兆强、徐风波、荆全来、张爱华、魏修良、王金满、王有志、王怀民、马吉平等撰文祝贺。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为李储坤站台、搭架子?就因为他那份执着的精神,一种历史情怀,一种文化情怀,一种通过保护家乡古树名木寄托乡愁的大爱而非机心。
那么,这份饱含大爱的情怀来自何处?自有心迹,他在《心灵的飞跃》“后记”中写道:“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最耀眼的闪光点,是那一纸上书政府保护高密古树名木的提案。在为古树名木画像、树碑立传参加挂牌的日子里,透过古树的肢体语言,穿过时空的神秘隧道,人魂与树魂交往,我写了发生在古树形体之外的若干动人故事。有唐宋元明清的,有抗日解放战争的,有树神显灵消灾祛病的,有惩恶扬善保安赐福的。我忘记了患脑溢血头部手术留下的后遗症,我的灵魂和肉体命我创作了180余篇故事散文,绘制了200余株古树名木图像……”
李储坤对古树名木的大爱也并非无源之水无迹可寻,散文集《心灵的飞跃》一篇题为《树下呼唤》的短文,从文字的真情流露中可略见一斑。文章回忆他小时候早晨上学的一件小事,从老家胡家村到袁家村只有一里多路,但要过一条沟和一片坟地,李储坤写道:
“有天清晨,大雾漫天,太阳迟迟不肯露脸,独自走在小道上,周围笼罩在一片白雾里,比任何时候都使我胆怯,脚步迈得又急又快。倏地蹦出个黄茸茸的东西,刷地一下从面前蹿过,我被吓懵了,调头往家跑去。母亲听罢我诉说,牵起我的手要去送我,想着她的心脏病,看看她细细的腿,尖尖的脚,心里清楚,宁肯不去上学,也不能让她去送,可学校毕竟是要去的,怎么办呢?还是母亲有了办法。她站在屋后苦楝子大树下,让我往前走,吃力地呼唤我,在呼唤的声音听清的时候,就用木棍打大树给我助威、壮胆,让我感到她就在我的身后,跟着我,陪着我,我大胆地向前走去。在离学校不远时,还听见母亲在呼唤我的名字:'你——在走着吗?'我边走边回答:'我一—走着哩!'就这样,母亲问一声,我应一声,在她不间断的催促声中,还夹带着'梆——梆——'的木声。我知道,那是母亲在敲打着大树,似钟鼓之间的声音,在大雾中回荡。
'我到学校啦!'我最后朝着母亲大声、兴奋地回答。这是遥远的一幕。”
李言谙
2025年2月14日
原载 阿龙书房
2025.2.14 15:36 山东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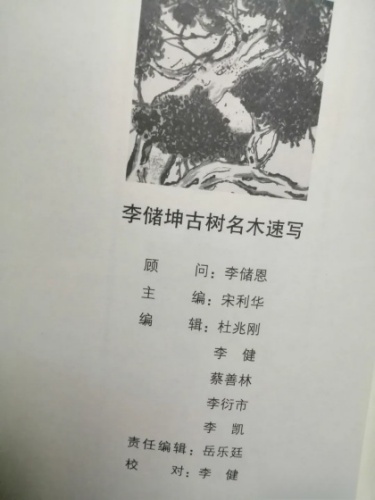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