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笔记(35)
48
“站在最上边远望,吓得腿肚子打颤,哪还顾得看风景。”
怎么办?“壮着胆子爬进渡槽”。这也是我想做的,到渡槽里去看个究竟。但我是严重恐高症患者,实在没勇气尝试。单连花看到了,并且“对着扬水站内两根抽水管喊话,重音特厉害,吓得我们撒腿就跑”。我想可能是很粗的黑色钢管,胶州提水站毕竟安装了396大马力的抽水机,管子粗到足以放大声音,把自己的“喊话”扩展回旋到极度空旷,像恐怖片中一样颤抖着散开,仿佛一层一层幽魂。
她们沿着渡槽跑远了,跑到南边水塔的位置,这里是摩天岭的最高点,自此渡槽不再用桥墩支撑,离地面不到一米,很安全的了——我怎么没想到从这里沿渡槽往北走到渠首呢?可能是那条南北沟的问题,到达渡槽隔着一条大沟,宽而深,除了深秋枯黄的杂草,还有密集的刺槐和楮树丛,另外,虫蛇之类尚未冬眠,不够安全。当然,主要还是渠首的吸引力还没大过不安全感。
“安全了之后,同行的小伙伴说他亲戚村一个女孩因为逃婚跳进抽水管自杀了,”单连花写道,“吓得我们头也不回,一刻不停地逃走了,就再也没有去过。”
留言到这里就结束了。她说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事实。
49
王吴水库是山东省最早建成的一座中型水库,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一个结果。过程是实用主义的,与文化和道德关联不大。
水是水库的最大资源。1958年,王吴水库建成后,一切附属设施的建成,都是出于对水资源的善用。水库北岸建设有东方红水轮泵站、王吴电站、褚家王吴扬水站,西岸建设有空冲水村扬水站,东岸建设有杨家栏子村扬水站,南岸建设有王十字庄村扬水站和胶州市提水站。
目前,除王十字庄扬水站踪迹难寻外,都还保留着原建筑物,但原设计功能都基本作废了。
水景已是旅游资源,四面有着一定历史的建筑物逐渐也演化为旅游资源之一。例如褚家王吴扬水站渠首和一部分渡槽被划入临库公园,经过精心包装而成为公园的重要景观。胶州提水站被开发者命名为“水上古堡”。开发者看中的无非水库南岸开阔的水面和提水站宏伟的建筑物。“古堡”当然指提水站水渠,尤其全部巴山彩石砌筑的渠首,时间上已经接近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是王吴水库的景观之最。水库周围这些建筑物身上,已经显示出文明的艰辛,质朴的苍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可视的景观与不可视的历史融合为一种文化和道德。
无疑,旅游开发是水库价值的再挖掘。
景观学家约翰·杰克逊告诉我们:“乡土景观的形象是普通人的形象:艰苦、渴望、互让、互爱,它是美的景观。”所谓乡土,是本地的、乡村的、寻常的,而非外地的、城市的、非凡的。乡土景观是城市漂泊者想找到的归宿,不安的心灵渴望获得的安宁,是不同身份的集合归一,是贫贱与富贵的共振。
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分析,中国大地上的景观无外乎三种:一是传统的,包括村落、农田、菜园、树林、道路、桥梁、庙宇、墓园等,是普通人的景观,农业文明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草根文化的载体,安全、丰产且美丽。二是政治景观,古代的例如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远古都城、帝王陵墓等,当代的例如城市景观大道、纪念性广场、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会议中心、大学城等,尺度恢宏而呆板,服务于政治,彰显大一统民族的身份,但与普通人不甚相干,与草根文化和信仰格格不入。三是出现了许多传统景观中所没有的新的景观要素:社区公园、加油站、街头小吃摊、城中村繁华的街道、杂乱的农贸市场、并不整齐划一的都市菜园等,这些景观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都符合普通人的要求,适应环境并不断变化,是孕育中的新乡土景观。
那么,景物和人追求的幸福一致吗?
这或许引进了一个道德问题。《河南程氏遗书》云:“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内持敬肃,外守道义,径直向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由此开始。朱熹讲评云:“最是他下得夹持两字好。敬主乎中,义防于外,二者相夹持。要放下霎时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达天德。”
天德,最高的精神境界,是也。
李言谙
2025年2月25日
50
《东武诗存》共计收录诗歌三千五百七十首,行世距今二百年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诸城人王庚言编纂了这部诗集,汇集了元代到嘉庆年间已故诸城人写的和外籍人写诸城的诗歌,一共十卷。卷十又分上下,卷十下又分为闺秀、流寓和方外三部分。“闺秀”收录了唯一一位女诗人的七首诗歌。这位女诗人是高密人。
她叫单为娟,字茝楼,号纫香,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初九,终于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初一,享年二十四岁。十九岁那一年,单为娟嫁到了诸城巴山王家,丈夫是王玮庆。与王玮庆的六年夫妻生活中,她先后孕有三子,都不幸夭折了,自己也在二十四岁时因病去世。单为娟去世四年后,王玮庆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王玮庆深刻怀念和单为娟在一起的日子,搜集整理妻子的遗作,共得五十八首,结为《碧香阁遗稿》,付之枣梨而行世。
单为娟的父亲单可玉,字师亭,号莱鸥。单可玉的母亲乃高密望族老木田李家李元直的闺女。李元直还有四个儿子:李高、李怀民、李叔白、李少鹤。其中,怀民、叔白、少鹤是高密诗派的主要代表人,李怀民则为首倡者。单可玉从小跟怀民、叔白、少鹤三位舅舅学习诗法,颇得真传,著有《荣安斋诗抄》《莱鸥诗抄》,诗作入《山左诗后抄》。
李叔白1782年在广西岑溪去世,李怀民1793年在高密去世,李少鹤1797年去世于岑溪知县任上。三李去世时单为娟尚年幼,诗艺自小从学于父亲单可玉,诗风直承高密诗派。一块学习的还有胞弟单为鏓,字伯平,号芙秋。单为鏓是高密著名理学家和诗人,书法精妙,著述丰硕。
单为娟以日常入诗,冷色中诗意淡远,也有些忧郁。如《月夜病中偶成》:
半窗新月明,皎皎光无缺。
照我窗前帷,通身疑是雪。
又《忆家》:
独对寒灯百感生,霜天嘹唳雁魂惊。
夜来时有归乡梦,犹听双亲唤小名。
巴山下,王家还有一栋老宅,应是岁月无心的遗留,偶有凭吊者走近,用陌生的目光搜寻熟悉的旧痕,报以迥异的怀思。
老宅面阔五间,正中开堂屋门,左右各两间。三层石为房基,石基表层被整饬过,与之上的青砖墙新旧不协调。墙上开窗四间,以年代算,原初应为木槅窗,后改为木框玻璃窗,窗下青砖已风化。斜坡屋顶铺小青瓦,正面因增出屋檐脱落,修葺时更换为红楞瓦。按照小青瓦的铺设规范,屋檐原本可能设有瓦当和滴水,之下为增出木椽,如今都已不可见。屋山也是青砖到顶,硬山式,坡檐青砖叠涩,屋顶直脊,端吻螳螂肚支撑雌毛脊,勾头瓦上翘于天。
久不住人,房屋已废,每年,屋顶上长出茂草,经霜后再度枯萎,如此一年年循环往复,仿佛在唱一支挽歌,可惜人听不懂,而那听得懂却不善言辞的砖石,如今也愈加沉默了罢。
李言谙
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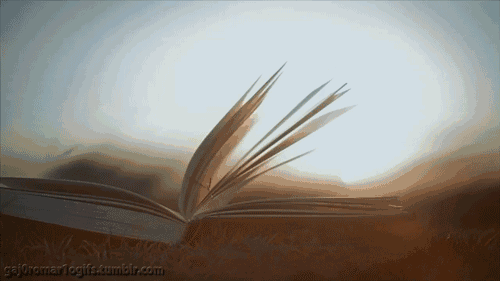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