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师爷赏饭吃”
王惠娟与京剧冥冥中有着奇缘,这得益于“祖师爷赏饭”,给了她姣好的面容和一条好嗓子,她说:“我小的时候嗓子非常好,是青岛市少年宫的一名领唱演员,经常参加市里举行的接待外宾的演出,记得当时接待西哈努克时,从各市区选拔的各个方面的优秀演员、演奏员,在这个年代,能被选上,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我被选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还参加过接待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像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领导人的演出,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
能够结缘京剧,纯属机缘巧合,她说:“1973年,中国戏曲学校和山东戏校同时在青岛招生,我和班里另一个男同学被选中了。最后,尚长麟老师(尚小云之子当时任教山东戏校)对我说,你是山东人,应该优先考虑家乡,就留在我们山东吧,就这样把我们俩都留到了山东。”从此,王惠娟走进了梨园,不离不弃五十余载。
“砍的永远没有镟的圆”
在戏校六年,王惠娟吃了苦、遭了罪,打下了基础,也收获了京剧带给她的荣耀。回忆过往,历历在目:“上学的那个时候,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比较匮乏,学习、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还好,当时大家的幸福指数特别高,那个时候也很单纯,就是想好好学戏。”刚到学戏的第一年,王惠娟学的是《红灯记》,教他们的是穆静娴老师,穆老师是上海人,梅(兰芳)先生的徒弟。王惠娟说:“穆老师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大家都很害怕他,他唱得特别好,嗓子特别棒。我现在能在唱腔上有一个良好的基础,真的很感谢穆老师。”她至今记得:“当时学‘听罢奶奶说红灯’一段唱,一个星期就抠一个字儿。一开始唱不对,让我们一遍遍地听,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掌握一个字儿,然后再掌握一个字儿的,我现在还记得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砍的永远没有镟的圆’,他强调学戏就要一点一滴地抠,这就是学院派、科班儿的功夫。”现在王惠娟自己课业授徒,她真正理解了老师之前说的,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一个演员演唱的时候一定要一板一眼,表演做到一招一式到位,没有几年科班训练是很难做到的。
在戏校,文戏是穆老师教的,武功课是教,都是名师。高明华老师是新中国戏校第一批学员,跟中国京剧院的刘琪是班上最优秀的两个武旦,刘琪曾陪杜近芳演过白蛇传里的小青。王惠娟跟高明华学的是《打焦赞》,“平时基功课,是高老师教我们。‘把子课’是荣春社科班毕业的翟永俊老师教。另外我们山东的优秀的武旦李文娟老师,也在我们学校,我跟她学的‘穆柯寨’。在学校里我学的武戏比较多,打下了厚实的武功基础。”
在济南上学期间,赶上薛亚萍刚恢复演出,每逢周日,王惠娟都去薛亚萍家学戏,张派代表性的传统戏,像《秦香莲》《状元媒》,都是薛亚萍给她说的。有时候薛亚萍演出忙,就由薛亚萍的母亲李婉云教她,尽管王惠娟没有拜入张派门下,可她的张派戏算是得到了真传。
1979年毕业的时候,王惠娟学会了全部的白蛇传,这出戏有文有武,前面“游湖”“结亲”是文戏,中间“盗草”和金山寺“水斗”是武戏,是好几个老师教给她的。王惠娟记忆最深的是这出戏的“打出手”“我每次演出就特‘保’,我们老师说王惠娟这出手特保,就是特别保险,从来没掉过。”很多年后,王惠娟回忆起这段经历,依旧充满深情,“你知道吗?能做到万无一失,这都是我在私底下练的,一次踢200多下。每天我就是不停地用脚去踢呀,踢呀!一次就是200多下儿,200多下没有掉地下的,踢打出手就是为了保坑。哎呀,等我夏天放暑假回家,我妈妈一看我的腿啊,上下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抱着我就流眼泪,说,咱不干了,太艰苦了。我说这就是梨园行说的‘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遭罪’,你遭了罪,你的动作才保险,才能让你的观众看到精彩的表演,才能给你掌声。”
回到青岛 机缘巧合成为年轻主演
六年戏校,无论是戏剧业务,还是学习成绩,王惠娟在班里都非常优秀,她还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是众人瞩目的“校花儿”。六年科班,打下坚实基础,练就一身功夫,毕业演出,凭《白蛇传》一出大戏,引起省内名家的青睐,方荣翔、殷宝忠和宋玉庆诸位名家对她倍加赞赏,说一定要让她留在省里,留在山东省京剧院。可是“当时因为我不太喜欢济南,济南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还特别‘土’,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我说我一定要回到青岛,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就回到了青岛。”当然,青岛是她生长的地方,而青岛京剧院也曾经名家辈出,这也是王惠娟渴望回来的因素。
回到青岛的第一年,青岛京剧院排现代戏《救救他》,王惠娟在B组,因为剧本等各个方面不是特别成熟,这个戏就没有演出。后来,青岛京剧院排《卖油郎与花魁》,尽管那个时候,她是以优异成绩分配到青岛京剧院,并作为年轻的培养对象,“因为京剧院的旦角太多,号称‘一窝旦’,按说论资排辈儿都排不上我。”可这毕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院里安排她参与其中,“就给我排了一个三组啊,第一组是欧阳娴老师,那时候她是‘大姐大’,在院里很有根基。还有是一个王老师,比我大二十几岁,在第二组。后来,欧阳娴老师有点儿耍大牌,和院里的头儿不怎么对付,晚上就要演出了,上午她却回了北京,我的天啊,团里头着急得火烧火燎,这怎么办?只好,下午让我排练,就排练了一遍,晚上就让我上,所有的人都在疑问,能行吗?刚毕业的学生从来也没排过练就能上舞台了?”面对各种疑问,王惠娟自己却显得相当自信。尽管她在第三组,没有人逼着她去学,但在前面两组排练的时候,她一直用心地去看、记、学、练。“一整出戏,我就一直在用心地去看,用心地去记,没想到一彩排,导演说真的是严丝合缝,特别准确,就这样,晚上我就上台演出了,那个当时所有的剧院的同事都捏了一把汗,当时我才十八九岁,确实也紧张,结果演出之后大获成功,从此以后呢,我就是京剧院的主演之一了,当时我是最年轻的主演。”
感恩田宝诚 拜师吴素秋 结识翁思再
说到艺术之路上遇到的贵人,王惠娟首先想到的是田宝诚,她说,“在我的艺术道路上,田宝诚老师是我的恩师,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舞台上,他引导、教导、示范于我,陪我演出,使我终生难忘。”在《玉堂春》里,王惠娟的苏三,田宝诚演王金龙,在《花田错》里,王惠娟的小花旦春兰,田宝诚演莫姬,作为老一代的田宝诚捧着年轻的王惠娟一路呵护她成长。“最难忘的就是1987年我们共同演出的《潇湘夜雨》,获了奖,这也是我在全国第一次获奖,这是中国首届电视大奖赛获奖的这个剧目。”
拜在吴素秋门下,让王惠娟在艺术之路上获得质的飞跃。1985年,王惠娟拜师吴素秋先生,拜师仪式由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刘镇主持,足见市里对这件艺坛盛事之重视。王惠娟说:“能够拜吴素秋先生,我得感谢我们青岛剧院的导演田宝成老师,他对我真的是在我的艺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厚爱,是我的恩师,我所有的现代戏,都是他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教出来的。”吴素秋先生是一个特别通透的人,她对田宝成导演赞赏有加,当时她来青岛给王惠娟排“苏小妹”,同时在青岛演《红楼二尤》,除了吴素秋先生,小生、丑角是从北京带来的,其他的配角都是青岛京剧院的,导演就是田宝诚老师,田宝诚的艺术素养赢得吴素秋老师的夸赞。后来王惠娟演红京城,吴素秋先生并没有贪天之功,她对王惠娟说:“小慧子,没有田老师的点点滴滴的教导,你不会走到今天,所以永远不要忘记恩师。我只是在你有了成绩的基础之上,给你锦上添花,你要更多感谢的是为你辛勤付出的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园丁老师。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铭刻在心,那么我现在我同样我也是老师,我也会这样教育我的孩子们。”
缘于拜师吴素秋,王惠娟得遇名票翁思再。她说:“翁思再老师是我拜师的时候举办的演唱会上认识的,他是新闻记者,是名票,懂戏还能唱,余派唱得很有味,他对我非常欣赏,在那次演唱会上,我们俩合作唱了《四郎探母·坐宫》。后来我去上海演出,他非常热情接待了我,而且还给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我在演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时候,他看了之后说:‘我真的没想到王慧娟文武俱佳!’那是九十年代初,当时我30几岁刚刚生完孩子,我的搭档,演我妹妹那个演员比我还大十几岁,他说:‘你们俩在舞台上根本看不出来那么大岁数。’因为草原小姐妹角色是十一二岁、十三四岁。我们都是年龄跨越了很大,这让翁老师赞不绝口,专门写文章揄扬。”后来翁思再给梅葆玖写了《大唐贵妃》,他到青岛来开会,专门找王惠娟见面,教她唱《梨花颂》,“从细节上,从他的编排意图上,给我讲了很多,我唱罢,他说:‘你唱的这个《梨花颂》,有深度有味道。’我说:‘这得益你的指导。’”
遍学“吴三出” 演火阿庆嫂
拜了名师,让王惠娟在艺术之路上更上层楼,吴素秋专门来青岛,传授排练她三出代表戏之一的《苏小妹》,吴素秋另外两出代表作是《孔雀东南飞》和《人面桃花》,王惠娟除学过全部的“苏小妹”,还跟吴老师学过“孔雀东南飞”和“游龙戏凤”。王惠娟回忆,自己跟吴素秋学《游龙戏凤》的时候,刚好刘长瑜老师和张学津老师要去香港演出这出戏。刘老师找吴素秋上门讨教,“那个年代摄像机很稀罕,刘长瑜老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带着摄像机拍摄了吴老师的表演,所以她的学习进度就特别快,几天的工夫,就学到精髓,之后就去香港演出去了。现在想,当时的资料留到现在很珍贵了。而我则是完全凭着记忆,用脑子去记,所以学得慢,却记得深。吴老师的《游龙戏凤》,从细节上,从人物上,有自己的风格。作为专业演员,我看过很多的名家的《游龙戏凤》,越看越觉得吴老师在刻画人物上有自己的理解,把握人物非常准确。另外,《红娘》这出戏,吴老师也有独到之处,她演的小红娘和其他人演的尺度拿捏得不一样,在跟我说戏时,她说,小红娘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热心的小姑娘,一定不要把这个人物演偏了,演得过于老成,或者过于世故,这个人物感觉就不高级了,不美了。这一点我很赞同老师的说法。”吴素秋要求王惠娟要从自己的修养上理解、刻画和表现人物,“再比如老师教我《苏小妹》,因为她是女扮男装,其中有一个抖袖的动作,需要表现出人物的精神抖擞,和潇洒倜傥,要体现人物的‘帅’劲。这一切都让我至今难忘。”吴素秋有三出代表剧目:就是《苏小妹》《人面桃花》和《孔雀东南飞》,别人真的是来不了的,王惠娟都从老师那里学了,她说:“老师传授我《孔雀东南飞》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我演出这出戏,获誉很多。”
王惠娟艺术之路上,最为得意的是当年自己演阿庆嫂获得老师的赞扬。当时青岛京剧院在全国率先恢复演出“杜鹃山”和“沙家浜”,2000年,青岛京剧院演出的“沙家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很高,好评如潮。“我到北京演出的时候,剧场外面就打着横幅‘欢迎青岛京剧院,王慧娟全国第一嫂’。说起来有点儿夸张,可当时我们这个‘沙家浜’还是很轰动的。”吴素秋老师,通过电视全部看完了,晚上十点多钟了,高兴地给她打电话,说:“小慧子(吴老师都叫我小慧子),祝贺你演出成功,这戏演得真棒,真地道。”第二天又给她打来电话,说:“小慧子,你这会儿可红了,你这出戏呀,真的是真棒,我一早就接到电话,一个是赵燕侠老师,一个是刘秀荣老师,都给我打电话,(赵燕侠直呼她素秋,刘秀荣称她素秋姐)都说,你这学生真不赖,真棒,地道、规矩、到位。”听到老师说到赵、刘两位艺术家都表扬自己,王惠娟打内心高兴,这二位前辈都曾经演过阿庆嫂,赵燕侠还是最早演阿庆嫂的,“前辈给我那么高的评价,我都觉得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入吴门窥高艺 得识名家无数人
拜吴素秋为师,王惠娟自己说跟着老师就像跟包一样,当时就因为老师特别喜欢她,在她家里面学戏,王惠娟跟随她见过许多的名家,还有机会跟很多名家合作演出过,像张学津,刘长瑜老师,再比如尚长荣老师,赵荣琛先生、梅葆玖先生,还有冯志孝老师等等。有一次,王惠娟和名票翁思再唱过一次“坐宫”,唱完后,他对王惠娟说,“你的嗓子这么好,特别适合拜杜金芳老师。”并表示要给她引荐,“我当时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已经拜了吴素秋老师了,就婉言谢绝了。”王惠娟事后说。后来吴素秋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她很豁达,说:“小惠子,你不用有什么顾虑,你表演跟我学一定没问题的,至于唱,要结合自身的条件,你应该学各个名家的长处,要博采众长,这样才能发挥你的优势,让自己更加丰富、更加出彩。”尚慧敏在纪念吴素秋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素秋师姑在20世纪30年代十几岁时,就拜在尚小云先生的名下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感觉她学花旦比较合适,这样她又投奔到荀慧生先生名下。荀先生也是高风亮节:既然你拜了尚先生,我就不能收你当徒弟了,这样我收你当干女儿吧。这样她就拜了荀先生为义父。”她自己的艺术之路就是这样走过的,她当然支持自己徒弟走好她的艺术之路。当王惠娟表示想唱张派,吴素秋当即同意,说唱张派就一定跟张(君秋)先生学。后来她带王惠娟见了张君秋先生,从此王惠娟在演唱上坚定了宗张的信心。
师恩如海,2003年的春节之前,王惠娟带着学生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参加少儿春晚,演出结束后,她专门抽出时间带着孩子们来到著名表演艺术家吴素秋老师的纪念馆参观。“老师生前的演出的海报啊、照片啊,还有平生的资料,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其中一个小朋友看到了有我的拜师照片,很惊讶,也很兴奋,我的学生纷纷围在照片前,指指点点,我看到纪念馆里只有这一张吴素秋收徒的照片,徒弟就是我,足见老师对我非常重视,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当然心里非常高兴。”在吴素秋纪念馆,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吴老师这个人真是德艺双馨,是京剧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在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我从老师身上不光是学了京剧艺术,还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做事的优良品质啊,所以你们也不光要学学戏,最重要的还是要学做人,因为优秀的传统京剧剧目,教的就是忠孝仁智信。”
“包幼蝶给我献过花”
王惠娟至今依旧保持着一个角儿的范儿,她要强、要好,通过努力让自己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也为此而自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青岛没有合适的演出舞台,青岛京剧团一度在“长三角”区域长期演出,在上海,王惠娟演出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得到媒体关注,翁思再在新民晚报刊文,赞扬王惠娟文武俱佳,这篇报道引起当时的上海文化局领导的注意,认为她条件好,特别想让她留在上海。王惠娟说:“当时史敏就是史依弘,还刚演‘虹桥赠珠’,只演下午场呢。而舞台晚场上演的是我们青岛团的传统戏。”在上海,有很多迷恋王惠娟的戏迷,她演《全部四郎探母》铁镜公主,一出场戏迷就用上海话喊:“王惠娟、王惠娟”,那份热烈气氛让她回忆起来,依旧兴奋不已。在上海时,还有一位谭阿姨(据说是谭嗣同的后代)老两口曾到舞台后面给她送吃的。
上海有一位名票包幼蝶先生,与梅兰芳先生谊在师友之间,专门请王惠娟到家里做客。包幼蝶先生出生于杭州,自幼对京剧艺术兴趣浓厚,少时曾亲身拜访艺术大师梅兰芳,此后开始醉心于梅派艺术,钻研梅派剧目的曲谱、念白和唱词。一九四○年,他应上海艺华公司之邀,拍摄《霸王别姬》京剧电影,又帮唱片公司灌录不少梅派唱腔唱片,因而声名大噪,名演员如童芷苓、李玉茹、王熙春等常向他请益。王惠娟记得当时的情形,“包先生亲自给我做了花儿,穿得特别靓丽,晚上就去给我送花儿,我们后台都惊讶得不得了。”当时王惠娟并不清楚这位儒雅的绅士何许人也,时隔多年之后,当她知道包幼蝶的身世和艺术造诣,很有一点未能请益于他的遗憾。
还有一件事,让王惠娟念念不忘:“在上海演出的时候,黄正勤老师,是创立‘黄派’的黄桂秋的儿子,就是在电影《红楼二尤》和童芷苓搭档演柳湘莲的那个著名的小生,把我请到他们家里头,请我吃饭,他的女儿跟我成了好朋友。然后又把我介绍给上海京剧院的许老师,我记得叫许美玲,是唱梅派的,他的先生叫纪玉良,也是著名老生,让我到她家里面,给我说戏。”王惠娟说:“这些前辈对我的关爱,和那种戏迷对演员的痴迷,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怎么说呢,哎呀就是感恩、感激、感动!就想在台上好好演,用自己的精彩演出回报他们的爱。”上世纪80年代没有什么太好的交通工具,青岛团在苏州杭州一带演出,有的戏迷一直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城市跑到这个城市,一路跟随,“我那个时候,今天演‘秦香莲’,明天演‘杜鹃山’,后天演‘沙家浜’,上海啊,南京啊,镇江啊,苏州、杭州,这一带,就是我的根据地一样啊,每年都来演出,那时候,这一带的戏迷对我还是很喜欢的。”
退而不休传薪火 梨园苍枝着新花
2016年,王惠娟从工作岗位退休,舞台上她的身影是难得一见了,可她却仿佛更加忙碌了。说起退休,王惠娟常常觉得很恍惚,“退休啊,我好像觉得更少了些空闲,反正,我是退而不休。”因为她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就是从事京剧艺术教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之前我是在舞台上为大家传播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国粹京剧。从退休之后呢,就从方寸舞台走向了广阔世界,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我现在每天非常充实,非常忙碌,非常艰辛,也非常欣慰,因为我从另一个侧面感受到,我倾心京剧艺术,为此流汗流泪付出心血没有白费,我通过自己的教学,为喜爱京剧的孩子打开了一扇窥探国粹奥妙的窗户,看到一颗颗禾苗茁壮成长,看到了国粹京剧传承的希望,我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信心为后辈的成长当好一块垫脚石,我感到了自己的另一种价值存在,这是拜京剧艺术所赐,我和京剧一时结缘,必将终生不悔。”刚刚退休时,王惠娟应深圳宝安教育局邀请,作为专家,参与京剧进校园活动,一待就是几年,她和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专家一起,为宝安打造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经过他们的辛勤培育,宝安的学生在全国拿到了许许多多大奖,“当时我的学生,他们现在都在中戏呀,上戏啊,已经成为京剧的后起之秀。”说到自己的有出息的弟子,王惠娟一往情深:“在深圳的时候啊,印象最深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叫黄雨欣,一个是戴景源,那个黄雨欣特别勤奋,特别认真。每次我教他一个唱段,他都会用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把唱腔的转弯,唱腔的长短,节奏的强弱,标记下来,九岁的时候,参加比赛,凭着一段‘诗文会·喜盈盈进画堂’唱拿了全国的金奖,这可是小梅花金奖啊,当时中国京剧院正要排《三国》,就准备要让他去演小乔,这是李胜素演的人物。他的演唱真是超越了九岁孩子的水平。”另一个学生戴景源,因为家庭原因,自信心不是很强,但她的天赋条件非常好,王惠娟因材施教:“我就动员他,说你一定要树立你自己的形象,你自己争气了,出息了,你们家里才能重视你,后来他的演唱的“霸王别姬”得了很多奖,像‘小梅花’呀、‘和平杯’呀等许许多多的奖。”从此,小景园树立起自信,人也变得开朗大方,学戏更专注,也得到了父母的宠爱,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王惠娟老师的付出和鼓励是自己成长的力量,时刻激励她勇攀艺术和人生高峰。
王惠娟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她说:“我在教学当中觉得是有一种责任,不光是要传承我们的京剧艺术,还有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孩子们通过学习京剧,学会自信、自强和自律。学会如何去面对社会,树立好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从深圳回到青岛后,为了传播京剧艺术,王惠娟依旧忙碌着,她有教无类,教老的和小的新学生。结缘一时,无悔一生,京剧艺术塑造了王惠娟,王惠娟加倍回报着这门国粹艺术。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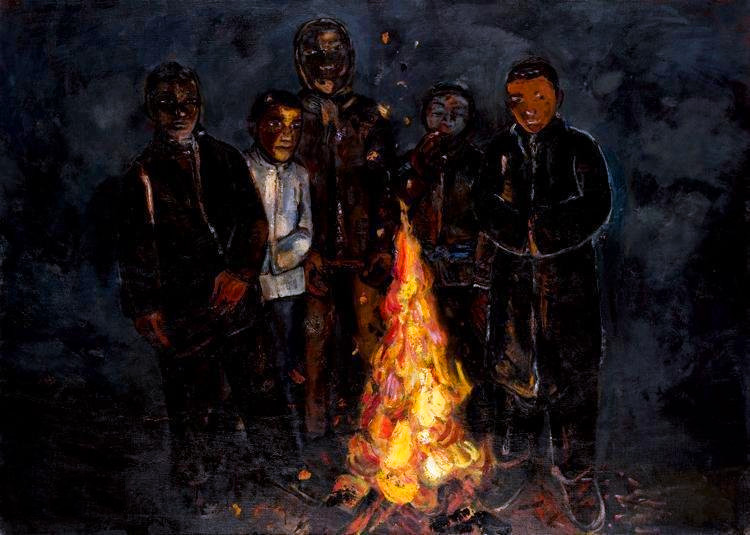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