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侵占了青岛的日本人,用一条鱼山路劈开了前海附近的一座无名小山,路的东面便是现在的小鱼山,绕山修建了一条福山路;路西面的山仍然无名,1930年代盖起了不少别墅,围绕着别墅修建了一条金口路。
青岛的路都是以中国地名命名,而且与实际地名所在地相对应。“金口”应该是即墨金口(清代的繁荣商港,南北货物进出口集散地),因为它与附近的福山路、莱阳路、龙口路、黄县路、掖县路、栖霞路、文登路所在的地方都属于胶东半岛。
金口路没有八大关名门望族的高贵,却也不失大家闺秀的典雅;没有东部新青岛的繁华,却浓缩了老青岛城区的宁静。在这里你看不到门头广告的鳞次栉比,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嘈杂;这里多的是一份慵懒和随意,一如它缓慢温适的生活。只有石墙小筑,红锈铁门,老式别墅,石阶长路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涂抹着历史的沧桑。
金口路因地势复杂,弯曲绵长,建路不久就分成金口一路、金口二路,后来又从金口二路分出了金口三路,不过现在人们仍然习惯地把这三条路统称作金口路。
1950年代虽然没有“学区”这个概念,但小学也是“就近入学,划片分班”。我当时住在金口二路,金口一、二路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全在文登路小学一个班里。每天上学放学我们就穿梭在金口路的大街小巷中,那里留下了我们童真的欢乐和纯洁的友谊。
时隔五十多年后,在一个海风轻拂、紫藤飘香的日子里,我推着一岁半的外孙重走金口路做“怀旧游”,老楼的建筑仍在,老街的味道仍在,院子里槐花依然盛开,院墙上蔷薇依然怒放,只是老同学、老邻居却踪影难觅了。
金口一路
金口一路西端连接着太平路,靠近老二中小操场曾经有几块高标准的网球场,围着一圈二三米高的铁丝网,这还是19世纪末德国人建的。1950年代,国家领导人陈毅、万里等在这里打过网球,60年代初,我们在二中上学时还见过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这里挥拍。“文革”中可能因为网球是“封、资、修”的东西吧,网球场被拆了,一块给了二中作篮球场,一块盖了财政局、体委办公楼。二中篮球场后来盖了几栋教师宿舍,不过门牌却是大学路1号。现在那里正在建地铁站。
网球场旁边在“青岛网球俱乐部”的旧址盖起的一座四层楼,是1999年4月23日正式挂牌的“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金口一路2号。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隶属于市委统战部,其主旨为组织帮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负责统战系统干部培训工作等。这个学校还有另一个名字“青岛中华文化学院”,主要针对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开展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是“青岛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中心”。

金口一路3号最初是一个日本人(朝鲜银行经理)的私宅,有资料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的家眷曾在此住过。建国后,这里曾经是金口路派出所,我的启蒙教师王佑明老师就住在派出所楼上。王老师从一年级教我们到三年级,后来因身体有病休了长假。当时的王老师年轻时尚,烫着发,衣服合体,爱穿列宁装、布拉吉,爱穿高跟鞋,喜欢跳舞,喜欢花。我的同学徐克澍院里有棵远近闻名的大玉兰树,徐克澍说,开花的季节,自己一犯错误就送花给王老师,老师便原谅了他(呵呵)。可惜王老师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便因病去世。
3号对面是一条通往金口二路、三路的胡同,胡同口有一个汽车屋改成的粮店。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粮食是按计划供应的,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购粮证”,上面记载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定量”及粗粮细粮的比例。如果不买粮食,可以换成粮票,因为姑姑一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我们家便经常换“全国通用粮票”。我记得“全国通用粮票”很难换,要单位开证明,还要按比例扣食油的供应量。小时候经常跟家长到粮店买粮,在那里接受了关于粮食的启蒙教育。我还记得,每年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到粮店买分配的地瓜。大人小人,大车小车,大筐小筐,一趟趟地往家搬弄,十分热闹。如今,那所粮店早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五六层的高楼。
7号曾经是铁路疗养院,后来成为铁路职工宿舍。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王德华住在这里,四年级时,她父亲调动工作,她跟着去了济南。王德华是第一个让我产生“好感”的女生。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早恋,而对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情窦初开”也还为时过早,只不过是刚开始有懵懵懂懂的“性意识”吧?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到中山公园爬山,我像个“小男子汉”似的帮王德华背着书包,她则略显羞涩地、感激地跟在我后面,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前些日子几个小学同学聚会,我让他们猜我的“心动女生”,他们没一个想到王德华,因为她在班上实在不起眼。我在几杯红酒的作用下,向大家袒露了藏在心中几十年的秘密。
金口一路不长,只有四十几个院,却住过七位将军。9号住过1955年授衔少将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忠学,1964年,黄忠学调任第六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后任部党组书记,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黄忠学重着戎装,相继担任海军东海舰队第一副政委,政委,海军顾问等职。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黄忠学楼下住过北舰政治部副主任赵昭大校(大军区级副军),建国后历任海军指挥学校政治委员,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现在其子赵金普还住在9号。
黄走后,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赵汇川入住9号,他是1961年授衔的少将,历任海军航空学校校长、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国的航母基地原胶南小口子军港曾融入他的诸多心血。
赵汇川搬走后北舰顾问康烈功搬入,他是老红军,1964年授衔少将。历任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旅顺基地副司令员,福建基地司令员,福建基地政治委员,烟台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顾问。
那天9号的门口一位环卫女工坐着休息,我问她:“这个院住着几户,可以进去吗?”她回答:“住着一户,随便进”。我推开微开的黑漆铁门进到院内,院里还套着一个小院。楼很新,但楼外挂着的铁制楼梯破坏了建筑的整体美感。院内空无一人,我照了张照片便退了出来。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琴南先生曾在10号住过,他翻译的《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是我们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世界名著。林先生长年寓居北京,10号便长租给外人居住。1940年代初,青岛最早的火柴厂创始人之一张仲三先生租下了10号整座楼。建国前夕,林琴南先生女儿曾来此住过近两年,现在的10号院已被违章房挤得插足难立了。
我的一位业大同学曾在12号住过,那个院的房东是一对巴西华侨,老两口不在青岛居住,委托女儿收取各家的房租。“文革”后这个院被一家公司以七十万元买断,现在门外墙上还依稀可见某某公司的标识,但不知产权归谁了。我的同学对几十年前院里的事记不太清了,倒是对斜对门赵昭赵伯伯每到夏天便领着她去洗海澡记忆犹新,时时想起。“文革”中同学一家搬到38号,与我的小学同学左元放、高继兰成了邻居。
13号曾经是银行宿舍,建国初成为67军招待所,现在是青岛警备区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院内停满了挂着军牌的小车,身穿军装的军人进进出出。
14号作为日伪敌产,抗战胜利后分给了当时来青的接收大员、中纺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元。王新元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纺织部副部长,王新元进京赴任后,14号则成为纺织局招待所。招待所所长是我同学周东平父亲的老乡,周东平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那时招待所院里长满了树,成群结队的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招待所平时没人住,所长便领着周东平到处用气枪打麻雀,周东平记得招待所里有小半缸盐水腌制的拔了毛的麻雀。
著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中国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研究的奠基人方宗熙曾在16号住过。方宗熙195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邀请回国的科学家之一,1953年应童第周的邀请来青岛担任山东大学教授,开启了学校的海洋生物遗传学研究,后筹建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并先后任海洋生物遗传教研室主任、海洋生物系主任和山东海洋学院副院长等职;他还任过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山东省侨联、科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中国遗传学会、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普通遗传学》《达尔文主义》等。
方宗熙1950年代初期搬到16号,后来把夫人妹妹弟弟及老母亲也接到16号,全家人住在了一起。内弟江乃强从这里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潍坊,为潍坊的环保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潍坊日报》曾做过专题报道。方宗熙在16号一直住到1985年去世,长达三十余年,如今他家的后人仍住在16号。
16号还住过海洋学院另一位教授陈修白。陈修白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1945年至1946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渔业学院进修。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水产公司鱼肝油厂厂长、青岛海洋渔业公司工程师、山东海洋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陈修白父亲陈陶遗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曾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于1946年4月27日病逝。
19号曾是比利时驻青领事馆,京剧名伶吴素秋建国前曾在19号生活了七年。当时外地京剧演员来青岛演出按惯例都要到她家“拜码头”。我的同学徐兆强也在这个院住过,那时门外挂的牌子是“新华社青岛疗养院”。小院不大,却鸟语花香,难得的是现在依然如此。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宋红旗也住在19号,她是四五年级从外地转来的,据说她父亲是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中层干部。
19号现在住着岛城文化名人赵宝山先生。赵先生是古董文物收藏家,是青岛文化街的首批入驻者之一,他本人也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仍在为岛城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例如龙江路赵太侔故居、金口路老建筑、馆陶路古树保护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买下了19号当年吴素秋的练功房,也算是“名花”有主,“屋”有所值了。19号二楼产权归文化局,前些年一直闲置,现在好像有人住了。
站在19号院外,想起了徐兆强幼时的一件往事:那天下大雨,上课铃早已响过,门外传来一声“报告”。打开门,徐兆强站在那里,头戴一顶苇笠,身披一件蓑衣,脚踏一双木屐,让从未见过这些“雨具”的城市孩子瞪大了眼。老师也发出了质问:“搞什么名堂?”徐兆强小声解释:“雨伞、雨衣被大人们用了,我只好找出这些东西,‘呱哒板’不跟脚,所以迟到了”,老师哭笑不得地说:“快放到教室后面,上位去吧”。那个“蓑衣郎”徐兆强我至今还记得。徐兆强中学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1990年已经在那边工作了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调回了青岛,在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21号最近因为院内拆建改造,施工单位的挖掘机铲断一棵百年老洋槐而被岛城百姓关注,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
1936年,俄国人基迭曼在此盖起一座两层别墅,小楼掩映在松柏洋槐的郁郁葱葱中。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没落贵族流亡到中国,被称为白俄,青岛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当时青岛的外国人除了日本人,就是俄国侨民,金口路是他们的集中居住地。他们甚至影响到青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我们小时候用的外来语有些就是来自俄语,比如水桶叫“米大罗”,拳击叫捣“鲍克斯”。
据资料记载,为俄国侨民子女建的俄国学校从最初的莱阳路后来搬到了金口一路21号。1940年代末,俄国人陆续回国,学校撤销。中国人、俄国人在龙口路13号联合开办的霍康医院搬到了这里,医院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小时候我还在这所医院看过病。
1951年,生如锋在金口一路21号前留影
二十世纪这座别墅的最后产权人是曾在霍康医院任妇科医士的生如锋(音)女士,我在金口一路上的同学都认识生大夫。1956年公私合营霍康医院改为市南区联合医院第一门诊部。
1966年,第一门诊部搬出21号,市南区在这里组建了青岛市南晶体管厂(后改为青岛科技材料厂)。“文革”混乱中,这里也遭受了浩劫,原址上扩建了办公室、食堂、招待所、车间、仓库、传达室,美轮美奂的欧式风情荡然无存。
1990年代,这座建筑被一家叫“麦克美高”的文具厂租赁。厂长姓淳于,加工一种花色笔杆的签字笔,号称韩国进口,销路很好。我有个亲戚认识厂长,还介绍人在那里干过活。现在网上介绍这里是“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可不知为什么铁门外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从外面看,院内虽然树木葱茏,建筑却尽显颓败,看得出好久没人居住办公了,不知是不是骗子在网上发的信息。
22号铁门斑驳,车库门还打着补丁,很不起眼的院子,当年这里可是住着一位将军——邓兆祥。邓兆祥1949年率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历任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北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邓兆祥也是个传奇人物,听金口一路的同学讲起过他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当年他率“重庆号”起义北上时,部下紧张地报告发现两艘舰艇在后面追赶。邓问清部下两艘舰名,毫不在意,哈哈一笑:“不用管他们,他们是在为我们送行”。果然“重庆号”与两艘舰越拉越远,不一会儿追舰就不见了踪影。另一个故事是1964年,我们打下美国无人侦察机,搜索部队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敌机残骸,向邓兆祥请示。邓调来当天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在海图上画了一个圈,“就在这里找”,很快便找到了。
有资料显示,金口一路22号不仅是邓兆祥故居,还是曾经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的一处故居。
孙科应该是金口一路上住过的最有名的人物了。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的别墅就在金口一路26号。1948年,他在这所别墅里召集幕僚们商议,决定以蒋介石的副总统身份参加竞选。尽管最终败给了李宗仁,却还是因“行政院长”的身份,被共产党列为国民党四十三名“战犯”之一。
我在一张照片上发现,26号还曾挂过“军事管理区”的牌子,那应该是北舰副司令员邓龙翔在此居住的时候。邓龙翔,1955年授衔少将,当时也是北舰副司令员,曾任海军长山水警区司、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现在26号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年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舰队司令部警卫连在这条路短短的二百米派驻了一个警卫班12人,9号、22号、26号三位将军家各一组四人。白天的警卫由舰队政治部保卫处派警卫员,持手枪贴身跟随首长,夜晚则由舰司警卫连战士持步枪在院内站岗放哨。
金口一路从一号开始,步步上坡,直到21号达到顶点;在这里拐了一个近九十度的弯,由南北走向变为东西走向。青岛的路牌有个规律:东西走向的是蓝底白字,南北走向的是绿底白字。当然,这里的“南北”“东西”都是大致的概念,这是青岛的一个特色:房屋沿山而筑,没有一座正南正北的,因此道路也是曲曲弯弯,且高低不平,红瓦掩盖在绿树中,错落有致。
金口一路双号拐弯处的28号,在这条路上明显地与众不同。它建在金口一路的最高点,进院后还要上一二十级石阶才到楼前。建筑年代比较晚,据说是美国人建的,与整条路上的德式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它如同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周边神态各异的“洋房”之间,当时很有些“高大上”的味道。现在的楼与我印象中的建筑完全不同了,问了同学才知道,原来老楼因房间少,被警备区拆了,又重新盖的。
28号院当年的“神秘”也是它“傲视群雄”的资本。门前经常停着一辆当时极少见的小轿车,平时几乎见不到有人进出。这里当年是67军的金口一路招待所(所部在13号)的一处别墅楼,用来接待济南军区和其他部队来青小住的首长。杨得志上将、杨勇上将、张仁初中将、范朝利中将、杨国夫中将、刘涌少将、况开田少将等都在此住过。这些将军与一墙之隔的邓龙翔副司令多为战友,所以经常在各自的阳台上打招呼聊天。
我们班一位叫张继勇的同学在这院里后院平房住过,他父亲是胶东人,抗战时期的老八路,因为没有文化,时任招待所所长。那个年代还不讲“拼爹”,我们对他父亲的职务并没多少兴趣,他也不觉得是炫耀的资本。小学毕业后,大家便与他失去了联系。
25号被称为“苗公馆”,旧时是一苗姓资本家的私宅。我的同学朱克家住在那个院,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在外贸工作,是因为他父亲是当年青岛市职工足球赛冠军外贸队的成员。上了年纪后,他父亲成为岛城有名的足球裁判之一。25号院内现在有一座后盖的两层小楼,听说是“文革”期间,院里一黄姓居民被强占了房屋,落实政策时无房可还,房管部门便在院内空地盖了两层小楼,另外几户邻居也跟着沾了光。这楼虽说鲜亮,却与老建筑的风格格格不入,让人很是无语。
27号在日占时期是青岛盐务局长(日本人)为他岳母买下的房产。徐兆强的父亲曾给这家人当厨师,一家人也在这院里住过一段时间。日本人投降后,房东回了日本,房产充了公,后来成为海洋所的职工宿舍,现在房改也都成了私房。
29号有一个占地极大的院落,南墙外是一条胡同,南大门改成几间平房,用来做“八大关街道帮到家社区服务中心”。院子里面种植着刺槐、红枫、梧桐、迎春等各种树木,从花岗岩的花墙看进去,红黄绿紫,五彩斑斓。
这里日占时期是一座日本的全科医院,名“崎巴达”(KIBADA)。建国年后曾经是山东大学(后来的海洋学院、海洋大学)教职工宿舍,现在据说房主是银河集团老总。院里的建筑修葺一新,仍保持着欧洲风格,看上去像一座贵族别墅。
31号曾经是市公安局的一处接待中心,我的同学蒋守卿一家曾在这里住过。蒋守卿的父亲建国前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建国后住在这个院里,白天工作,夜晚兼职守卫。蒋守卿小时候经常看到有客人神秘进出,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公安局的一个处,行使类似现在安全局的职责。这里建国前曾经是挪威驻青领事馆,蒋守卿还记得他们家刚搬进来时,房间里都有地毯,有一间屋还有一架钢琴嵌在墙壁中,他还曾淘气地胡乱弹奏过。公安局之后,这里曾归水族馆管过,现在据说也被个人买去,成了私宅。从外面看,花岗岩高墙耸立,黑漆大铁门紧闭,偶尔传出阵阵狗吠,不知里面住的什么人?
蒋守卿在小学就喜欢读课外书,多次被老师表扬。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沂机床厂,后来调回青岛,官至中石油青岛分公司副总。在石油匮乏的年代那可是手握实权的人物,批一张条子就可以捞不少钞票,但他显然清正廉洁,是从纪委书记任上退的休。
31号还住过一个“有趣的”人物。1940年代后期,这里是一位许姓土产资本家的私宅,被称为“许公馆”。许老板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小六”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什么也缺不了他的。但他有个怪癖:不愿穿鞋。小时候家里人外出总爱带着他,但不管去哪里,他寻死觅活就是不肯穿鞋。后来大了上学了,也知道美丑了,能穿鞋去上学了;但是出了家门就把鞋脱下来,放到书包里,到了学校再穿上。这段故事是徐兆强的二哥徐兆庆先生讲给我听的,他小时候住在27号,比“小六”大两岁,整天在“小六”家玩,许家人便托付他多关照“小六”。如今的“小六”也七八十岁了,徐先生提起他,眼前还会出现一个小油头梳得锃亮,西服马甲吊带裤,却赤着脚丫,一双小脚像老农民,脚底磨了厚厚的一层茧子的小少爷。
32号也曾是银行宿舍。我的同学王建国曾住在这里,他父亲在银行工作过。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街道在32号办起了托儿所,院里的住户都被迁到了别处。托儿所办了不到两年就散了,许多住户又搬了回去。
王建国小时候是班上最“野”(调皮)的孩子之一。四年级时,班主任刘老师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让他当了班长,果然束缚住他的“野性”。初中毕业后,王建国考入青岛城建技校,毕业分配在枣庄水泥厂,从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干到厂长,后任枣庄城建局副局长。1997年思乡心切的他,几经犹豫、纠结,还是毅然调回青岛,几年前从青岛建材总公司中层干部的位置上退休。
32号还住过我的另一个同学刘青海。1960年,担任街道干部的母亲为响应政府号召,带头领着四个幼小的儿女回到淄博老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村里的刘青海一家,忍饥挨饿,度日如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刘青海如今提起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仍然禁不住眼圈发红。坚持读完了初中高中的刘青海作为回乡知青回到农村,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凭着一股不怕流血流汗,不惜体力精力的狠劲拼劲,赢得了干部社员的认可,成为村里建国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当上了民办教师,团支部书记,1973年被大队公社推荐上了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周村农业局,后又调到泰安农科院,评上了研究员,担任了副院长,从农科院退了休。
33号是金口一路上有名的建筑之一。1930年,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在此开办了“万国疗养院”。宋春舫先生还是一名藏书家,他在青岛建的书房“褐木庐”,是国内首家私人戏剧图书馆;他还是中国海洋科学的先驱,曾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科长,倡导建立中国海洋研究所,青岛水族馆也是在他的努力下1932年建立的。当时的许多所谓“疗养院”,其实就是旅馆,宋春舫的好友胡适两次来青,都下榻在33号“万国疗养院”。
33号建国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美国海军俱乐部。建国后做过北舰幼儿园、干部家属楼,如今却破旧不堪,似乎无人居住。这么寸土寸金的地脚,也只有军产才会闲置,还是体制的问题。
34号当年有一座青岛唯一的东正教堂。因为居住集中,俄国人信奉的东正教教堂就建在金口一路,当地老百姓叫它“拉姆庙”。1950年代后期,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这批俄罗斯人陆续返回苏联。此后,这座东正教堂长期闲置,门户紧闭。只是每逢周末这里还经常放映电影,中山路上的电影院每场两毛钱,这里半价只要一毛。我在一路上的同学们经常在这里看电影,像《静静的顿河》这些片子他们至今都还记忆犹新。“文革”期间,“破四旧”的风暴将这座教堂夷为平地。
我的同学马宝林住在34号后院。当年34、35、42、44号都属于煤矿工人疗养院,马宝林的爷爷是院长,奶奶是书记,煤矿疗养院后来归属于全国总工会疗养院。
马宝林小时候长得很漂亮,性格又像个小女孩,大家便给他起外号“马大嫚”,男生女生都喜欢他。几十年后再见到他,依然很帅,依然很有“女生缘”。马宝林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港务局工作,我们无法想象他那个柔弱的身板怎么能扛得起二百斤重的大包。后来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养成了认真细致负责的好作风,现在班里的同学们有什么事务性工作都推给他,他保证能出色地完成。
俄国侨民多为贵族,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小提琴家谭抒真(这可是位堪比贺绿汀和傅聪的伟大音乐家),14岁时就师从住在金口一路上的俄国小提琴家霍洛舍夫斯基(不知住在几号院)。
俄国侨民的吃苦耐劳,给附近的邻居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建国还清楚地记得,34号院老王家的俄国媳妇,高高大大,白白净净。有一年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人们冻得伸不出手,老王家的下水道堵了,俄国媳妇挽起袖子,戴上胶皮手套,跳进马路上的古力中,一把一把地掏出堵塞的秽物。
36号院子不大,一座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这里曾住过67军童国贵副军长,童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历任志愿军师长,省军区司令,1967军副军长,1955年授衔少将。“文革”前住42号。
36号还住过一位副军长孔瑞云,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建国后任过济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副军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要塞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顾问。64年授衔少将。这个院后来住着警备区王副司令,九十多岁了,前些日子才去世。那天看到有军人进出,看来仍是军产。
金口一路上有十五六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横或纵的胡同。胡同里马牙石铺地,石条筑阶,两旁深深的庭院里老树杂草,青苔茂竹,为金口一路增添了一抹静谧和神秘。这些胡同从金口一路延伸到二路、三路,延伸到莱阳路、鱼山路,像一棵巨树的树根,吸收着四面八方的人气和活力。
37号乙就在这样的一条胡同里。 37号乙曾经是徐克澍家的私宅。徐克澍家在原籍掖县是名门望族,“徐家八大家”曾占据掖县城百货业的半壁河山。建国前夕,徐克澍父亲徐效古先生带着父母兄弟来青岛“闯世界”,当时他用四万八千块大洋从一国民党官员手中买下了37号乙。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中,徐先生把商铺和作坊都交了公,只留下了37号乙这处住宅。“文革”中,37号乙也不可幸免地遭了劫难。先是居委会的小脚大妈组长隔三岔五地来命令当时徐家掌门人徐奶奶:“徐大娘,倒两间房给***住!”徐奶奶便快麻溜地倒出来。三倒两倒,最后徐克澍一家被赶到了39号的汽车库。现在想想,这种事简直不可思议:街道小组长有什么权利剥夺私有财产?但那个年代就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1979年,徐克澍从青海建设兵团顶替父亲回青就业,他工作之余的“工作”,就是到处上访、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整整用了十年,37号乙终于“完璧归徐”。1990年代初,徐老先生考虑再三,决定将37号乙私宅卖掉。一位名王春明(音)的美籍华人用300万人民币买下,本来他想在青岛开公司,可几年过去,因种种原因没开成,他便委托政府拍卖。当时正是房地产低谷,第一次拍卖以180万的开拍价竟然流拍。第二次拍卖时,一位年轻的地产商独具慧眼,仍然以180万的开拍价将37号乙买下。几年前徐克澍故地重游,新房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徐克澍发现原建筑上天入地各加了一层,两层楼变成了四层楼,新房东“霸气”地说:“现在给我三千万我也不卖。”
38号是一座三层小楼,面海背山,一条“之”字形花岗岩石阶从院门通到楼前,这里曾是我同学左元放家的私宅。左元放外婆家曾是上海滩的大户人家,有一个舅舅任过上海工商联副主委。1930年代末,左元放几个舅舅从上海来青岛拓展家族生意,买下了38号整座楼和另外几处房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把房产都交了公,只留下38号三楼的两间屋和一个阳台,左元放一家自己住。因为这是家族的房产,现在暂时由左元放的姐姐代管。
38号后院连着一座无名小山,我们叫它后山,翻过山就是金口二路,38号便成了我们小伙伴从一路到二路,从二路到一路的便捷小道,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个院穿过。后院墙下有一个水泥垃圾箱,是我们翻墙上山的阶梯,这个垃圾箱如今还在,后山却早已成为一片住宅小区了。38号院内也是违章房乱建,从墙外看如同贫民窟。
左元放中学毕业后也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在兵团待了六年后,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青海格尔木发电厂的筹建,电厂建成后便留在了那里。在那里与也是兵团战友的一位重庆姑娘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为了女儿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1986年,左元放放弃了厂里的中层干部身份,放弃了到武汉水电干部管理学院深造的机会,历尽千辛万苦,调回了青岛,在黄岛发电厂干了四年普通的班组工人,进了厂基建处。电厂基建处工程量巨大,“油水”丰厚,但左元放却坚持自己“同流不合污”的道德底线,兢兢业业地干到了退休。退休后的左元放生活丰富多彩:每年出国旅游一次;在老年大学学摄影,到各地采风,作品还获得过市老干部摄影一等奖;重新拿起了小学就喜欢、初中放下几十年的乒乓球拍,每周到俱乐部活动几次,偶尔参加比赛,也得过好名次。
38号还住过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高继兰,她也是青海建设兵团军垦战士,也历经辛苦,调回了青岛,从青岛车辆厂退了休。
39号有我的两个女同学:宁慧妹、曲玛丽。宁家是一个大家族,当年宁慧妹爷爷宁文元是岛城大资本家,一直与德国人做生意。宁家的四公子宁推之,被称为“宁四少爷”,早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学院,1930年代,宁推之出资500大洋在广西路开办“荒岛书店”,成为青岛地下党和“左联”的活动地点,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老舍、王统照、洪琛、黄宗江、萧军、萧红都曾经常光顾这里。宁家其他几个儿子在社会上也混得风生水起,金口一路26号、37号、39号、41号,莱阳路5号都曾是宁家房产,甘肃路、保定路上也还有几处。
宁慧妹是我们班最矮的一位同学,排队总是在最前面。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忘记了,宁慧妹的模样我还依稀记得:圆圆的脸,扎着两条长辫子,说话很害羞的样子,活脱脱一个邻家小妹。
曲玛丽的姐姐曲露露是岛城有名的美女,当年她是青岛开放、时尚、浪漫的标志性人物。她的各种版本的传奇经历为她造就了一批帅哥靓妹粉丝,与别人说起“我和曲露露的妹妹是同班同学”时,似乎也能满足我们小小的虚荣心。曲玛丽顶替母亲在市立医院就业,几年前从急诊室总护士长位置上退休,又被一社区医院聘为负责人,今年才彻底退下来。她的姐姐也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40号曾经住过海洋学院生物系主任高哲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子高歌1963年二中毕业以山东高考第一名考入北航,“文革”后分配到青海工作,1985年北航首位博士生,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任国防科工委水动力学专家组副组长。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任国防科工委水动力学专家组副组长。高歌在湍流理论上有重大发明,曾受到赵紫阳、邓小平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过。其研究的沙丘驻涡(BD)火焰稳定器获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1986年被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0号前几年据说被一台湾人(也有说温州商人)以1700万元人民币买下,如今大门紧闭,从墙外看,院内亭台楼阁,绿树环绕,清新雅静,修建的像一处花园。
41号是宁家的祖宅,当年宁文元在这里开山劈石,建起一座三层别墅楼,全家四十余口人都住在这里。现在41号门牌在金口一路上,其实那是一个北门,正门在南面的胡同里。从南面看过去,41号楼端庄典雅,雍容高贵,宽敞的院子里一棵高大的榕树,一到夏天遮天蔽日,撑起一片阴凉。进南门有几级石头台阶,上去台阶是一个门洞,门洞两旁左右对称地盖着两间各约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那是当年宁家的私塾学堂,东边是两位老师的宿舍,西边是宁家子弟读书的教室。现在平房仍在,只是长年无人居住,房前长满野草,一派荒芜。
这次我路过41号,看到楼外挂的牌子是“青岛汇泉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门卫跟我讲里面还有“中外捷运公司”。我则看到中午有些身穿城管制服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似乎是在这里吃午饭。
43号是我的同学孙慧正家的私宅。孙慧正祖父孙柳溪先生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校长、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学长,七七事变后,因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辞职回乡,在金口一路盖房隐居,青岛伪政府曾多次登门恳请他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市立医院院长,皆被拒绝。
孙慧正记忆中的43号三层小楼背山面海,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果树,绿色草坪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文革”中,这里也难逃厄运,树被砍伐,花被清除,连草坪也被造反派掘走,违章房见缝插针地冒出来。现在43号虽落实政策归还了孙家,却风光不再,旧景难觅了。
孙慧正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工厂“青岛市无线电元件二厂”。报到那天,当她看到简陋破旧的厂房设备,单调繁杂的生产工序时,立刻产生了抵触情绪,找了“关系”,想要调动。“关系”批评了她的见异思迁,劝她安心工作。没想到小工厂一步步发展成青岛电视机厂、上市公司海信集团,孙慧正也一步步成长为集团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董事会董事。小学毕业后一直没见过她,几年前我们在市老年大学太极拳班又成为同学。现在她在老年大学学绘画,前些日子看她们的成果展,外行的我觉得她的水墨画已很有造诣了。
我生平第一次见识跳交谊舞是在44号。44号从外面看有一处半圆形建筑物,是门厅,是餐厅,还是舞厅?那道靓丽的弧线曾勾起许多人的遐想和猜测。我知道那是个综合厅,在里面可以打乒乓球、可以跳舞,因为马宝林带我们去打过乒乓球。有一天晚上带我们进入里面,几个小伙伴老老实实地坐在窗边,看大人们在悠扬的舞曲中翩翩起舞。那舞会的旖旎场景与那建筑的半圆弧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文革”时期,44号差点住进一位“大人物”:青岛市的“一把手”、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葆华。1967年1月22日,青岛市造反派夺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党政大权。因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卖花生米“一毛钱八粒”被对手起绰号“杨八粒”的杨葆华,由一名明胶厂工人、市轻工系统造反派负责人摇身一变,成为市革委主任。他看中了44号,进行了精心装修。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还没搬进去即下台,1979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缓,1982年改判有期徒刑20年。1989年出狱后从事过各种职业,最后穷困潦倒的他住进了麦岛福利院,1998年病逝,终身未婚。44号当年因杨葆华的准备入住,被称为“杨公馆”,杨宝华下台后,“革命群众”把对他的仇恨发泄到“杨公馆”身上,“杨公馆”从装修到家具被砸了个稀巴烂,为这个院又增添了一抹历史的痕迹。
那天,44号大门闪着条缝,我信步走入。几蹬台阶左手一间门房,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坐在里面听戏,他没发现我,我便径直进到院内拍了几张照片,出门回望了一下似乎无人办公、又有些神秘的院落,黑漆大铁门上方的紫藤萝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流逝。
48号是金口一路最东端的一个院,院子极大。我们上学时是北舰的一个幼儿园,后来改建为舰队干部公寓楼,现在则建成“金口花园”小区,据说里面的几栋楼都是正军级干部楼。那天我想在门口拍张照片,被从门房中出来的两个身穿迷彩服的青年赶走:“这里不能拍照!”当时虽有些疑惑:既不是军事重地,又不是私人宅邸,为何不能拍照?但怕败坏了好心情,便没与他们搭腔,收起相机离开了。后来路过这里又补拍了一张。
48号的楼因为是后来盖的,所以里面住着的几位将军不在金口一路七将军之列,其中有北舰参谋长、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徐世平中将,北舰副司令朱洪禧中将。巧的是这个院先后住过四位杨姓将军:北舰司令员杨立,1961年授衔少将;北舰副司令员杨继忠,1988年少将;北舰副司令员杨玺,1988年少将;北舰副参谋长杨苏,2015年少将。而且巧的是,后三位杨将军都曾任过海军潜艇基地司令员。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何小江也住在这个院,她的父亲是北舰顾问何明智。也许是从小生活在军人家庭的缘故,何小江性格豪爽大方,热情开朗。1960年代初,自行车还是奢侈品,我们班只有两位同学有,何小江的那辆则成为班上同学学骑车的“教练车”,我就是用那辆车学会骑自行车的。我们班女生体育成绩特好,初中三年六个学期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全被她们包了。何小江是其中的绝对主力,她的80米低栏在历届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没出前两名。何小江高中毕业后参军,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后来转业到市药检所,后又调到海慈医院,从那里退休。
48号对面的45号和47号,其实是鱼山路2号海底世界后院的建筑,在金口一路上开的门。45号门头是科海商务酒店,47号门外挂的两块牌子分别是青岛市科技咨询业协会、青岛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两个院。
徜徉在金口一路上,对照着脑海中翻腾的儿时记忆,感觉整条路变化不算大,一座座老建筑仍然在默默地坚守着对历史的忠实守望。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如果说老建筑是“静态的文物”,那么,生活在这些老建筑中的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就是“动态的文物”,也需要我们珍惜守护,代代相传,不要让它们随着岁月的风雨飘零而去。
(文中钢笔画写生作者王鹏先生现任青岛市钢笔画协会副会长,谨致谢)
原载 青岛城市档案论坛
2019.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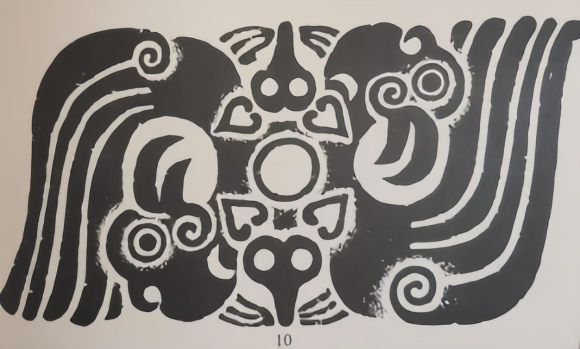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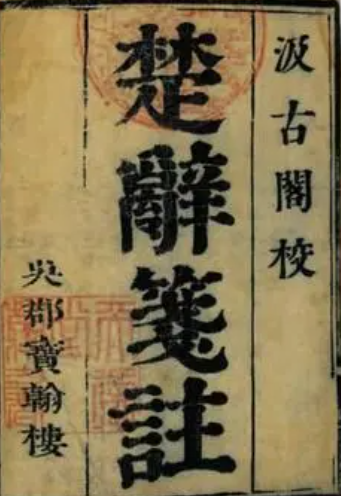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