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4.5)读到一首白居易的《咏史》,这首诗明确注明写作时间是“九年十一月”,诗是这样写的:
《咏史(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
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
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咏史》所咏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借助历史曾经的血腥来书写血淋淋的现实。为这现实,白居易还写了另外一首: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两首诗因同一件事而写,这件事即甘露之变——唐太和九年(835),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大臣李训、郑注、王涯等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欲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这对于大唐王朝是一件天大的事。当京城长安甘露事变的消息传到优游于东都洛阳的白居易耳中,他对于这场血腥事变,已经完全不像二十年前乍闻武元衡遇刺那般激奋,好像已经不那么吃惊了。这一天,白居易好整以暇,独自游了香山寺,写了一首即事诗,意犹未尽,又写了《咏史》,两首诗将血腥的政变作为背景,借丰富的历史典故将自己对甘露之变的所思写出来,他看透了、看淡了,现实的血腥已经无法袭扰他内心的安逸了。祸福无门,唯有自招,远离庙堂,即可免灾。
两首诗用典解诂
“秦磨利刀斩李斯”:典出《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腰斩于咸阳,临刑谓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齐烧沸鼎烹郦其”:指汉初郦食其说降齐国,韩信破齐后,齐王田广怒而烹杀郦生。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黄绮入商洛”:商山四皓中夏黄公、绮里季隐遁典故,源自《史记·留侯世家》。
“歌紫芝”:化用四皓《采芝操》“晔晔紫芝,可以疗饥”之句,见《古今乐录》。
“白首同归”:语出潘岳《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后石崇、潘岳同日赴刑场相视而笑:“可谓白首同所归矣。”(《晋书·潘岳传》)
“顾索素琴”:暗引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事(《晋书·嵇康传》)。
“忆牵黄犬”:李斯临终语,亦见《史记·李斯列传》。
“麒麟作脯龙为醢”:反用《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喻贤臣遭屠戮。
“泥中曳尾龟”:典出《庄子·秋水》楚神龟“宁生而曳尾涂中”寓言。
两首诗密集的死亡意象构成历史暴力图画。当白居易将李斯、郦食其的惨死与商山四皓的隐逸并置时,甘露之变的血腥现场被纳入“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的对照中。这种“去者逍遥来者死”的历史认知,颠覆了传统士人“致君尧舜”的使命,将政治参与的热情降格为生存策略的选择。
千年聚讼诗案公评
对《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历代诗评争议颇多:
《仇池笔记》的悲情说:
“内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苏轼透过“盖悲之也”的论断,洞察到“当君白首同归日”中隐藏的双重创伤——既是王涯等新贵陨落的集体悲剧,更是诗人对自身江州之贬(815年)的遥远回应。这种悲悯超越了私人恩怨,如盐溶于水般渗入历史循环的苦涩。
《蔡宽夫诗话》的互文对照:
“刘禹锡、柳子厚与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贬,元衡为相时也。禹锡为《靖共(安)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实盖快之。子厚《古东门行》云:“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虽不著所以,当亦与禹锡同意。《古东门》用袁盎事也。乐天江州之谪,王涯实为之,故甘露之祸,乐天亦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
蔡启(宽夫)将柳宗元《古东门行》“冯敬胸中函匕首”(用汉文帝时袁盎被刺事)与刘禹锡《靖安佳人怨》并置,揭示中唐诗人群体对政治暴力的集体记忆,那次血腥事件导致白居易被贬江州,而甘露事变的遇害者王涯当年是力主贬抑白居易的主角。白居易此时以“青山独往”的姿态,惹得蔡启猜测白居易“小肚鸡肠”。
《诗人玉屑》的道德审判:
“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仇可快,然朝廷当此不幸,臣子不当形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类。”
章惇(子厚)“几如幸灾”的苛责,与蔡启的看法一致,与苏轼的观点截然不同。实则是对诗歌讽喻功能的误读。“麒麟作脯龙为醢”的惨烈图景描写,哪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悲悯和同情的成分更多一些。苏轼的见识值得肯定。
《白香山诗集》的文本细读:
“按‘白首同所归’乃潘岳、石崇临刑时语。太和九年甘露事,李训、郑注、舒元舆、王涯、贾餗皆被害。味诗中‘同归’句,本就事而言,不专指王涯也。公自苏州召还,秩位渐崇,见机引退,宦官之祸,早计及者,何至追憾王涯?况公之迁谪,本由宦官恶之,附宦官者成之,岂反以中人诛夷士大夫为快?幸祸之说,盖出于章惇,谚所谓‘以小人心度君子腹’耳。”
清人汪立名指出“白首同归”非专指王涯,实乃对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五相齐陨”的整体观照。这种超越私仇的视野,与白居易宝历年间《禽虫十二章》“兽中刀枪多怒吼”的末世寓言一脉相承。
江州谪恨与白王恩怨
白居易与王涯的恩怨,可追溯到甘露事变二十年前的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元和十年(815)武元衡遇刺案。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寅时,长安城笼罩在破晓前的浓黑中。上朝路上的宰相武元衡刚出靖安坊东门,导引的灯笼便遭刺客箭矢击灭。黑暗中刀光闪过,这位力主削藩的宰相头颅被割下,尸身倒伏于大明宫丹凤门外。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遇刺,头部中刀坠入阴沟。这起血腥刺杀的起因是唐宪宗李纯继位后推行“元和中兴”计划,以武力镇压藩镇割据。武则天曾侄孙,进士状元出身的武元衡力主“强干弱枝”,是宪宗削藩政策的核心执行者。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武元衡主导平叛,其强硬态度使藩镇视其为最大威胁,从而引发河北王承宗、山东李师道等藩镇恐慌。
元和十年(815)正月,朝廷正式讨伐淮西,调集十六道兵力围攻。李师道等藩镇认为“唇亡齿寒”,企图通过刺杀瘫痪中枢指挥系统,瓦解平叛行动,元和十年六月初三凌晨,武元衡从靖安坊宅邸出发上朝,行至坊东门,刺客先射灭灯笼制造混乱,随后以箭、刀、锤等武器袭击,武元衡被斩首,首级被带走。此时白居易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他义愤填膺不顾唐代“非谏官不得言事”的铁律,在血案次日便向宪宗呈递《请捕贼书》,疾呼“国辱臣死,此其时也”。这份奏章如同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追凶的声浪,更得罪了政敌。而弹劾他的就是甘露事变的遇难者王涯,弹劾的罪名竟然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指斥他“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旧唐书·白居易传》)。这场道德构陷的背后,实为宦官集团对削藩派的清洗——王涯作为与俱文珍集团关系密切的官僚(参见《新唐书·王涯传》),其弹劾绝非个人私怨而是集团意志的延伸。当政敌以“不孝”罪名构陷时,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自辩:“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字里行间燃烧着儒家士人的赤诚。
然而这种赤诚很快被江州的寒雨浇灭。贬谪途中的《舟夜书怀》已显露裂痕:“暗虫声切切,落叶气凄凄。此夜愁人独,孤灯照客衣。”但真正标志其精神转折的,是浔阳江头的《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喟叹,不仅是对商妇的共情,更是对自身政治处境的隐喻。那个在朝堂上“不惧权豪怒”的白大夫,一经贬谪,意气顿消,“江州司马青衫湿” 活画出一幅失意文人落魄潦倒的形象,江州之贬(815-818)成为一道分水岭,从此他开始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其《琵琶行》流露出对时局的疏离感,为甘露之变期间的沉默埋下伏笔。二十年后的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发生,当年构陷白居易的王涯仓皇逃出中书,在永昌里茶肆被禁军抓获,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他的全家遭诛灭,家产被没收,田宅入官,而白居易反成“泥中曳尾龟”的幸存者。这种命运倒置的荒诞,白居易仅以两首七律发了一点个人的慨叹,而并没有更激烈的举动。
青山独往:白居易的精神蜕变
甘露之变爆发时,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长安城的血腥气为香山寺的炉烟掩盖,那个曾经“不惧权豪怒”(《寄唐生》)的白居易,面对宦官集团屠杀千余朝臣(包括宰相王涯等),白居易未公开发表政论,仅通过《感事而作》、《咏史》等诗作隐晦表达:“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从武元衡遇刺(815)至甘露之变(835)的二十年,是白居易精神蜕变的二十年。从元和年间的锐气(815):《论魏徵旧宅状》中“以直谏为心,以忠贞为事”的谏臣风骨,到长庆年间的彷徨(821-824):《杭州刺史谢上表》“察臣慎守官常,恕臣不逮”的守成心态,再到大和年间的超脱(829-835):《中隐》诗“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生存智慧,最终有了太和九年甘露事件中彻悟(835):《咏史》“去者逍遥来者死”的通透认识。
两首“甘露”诗展现了白居易的精神彻底蜕变到将政局看作虚妄的境界。此诗借助大量历史典故,暗讽卷入权力斗争者的悲剧结局,暗示自己通过退隐自保,终于在“泥中曳尾龟”的轨迹里寻找到生存的策略。当白居易对政治的热心冷下来时,而此时,唐王朝也进入了倒计时。
原载 读曰乐
2025.4.6 8:16 青岛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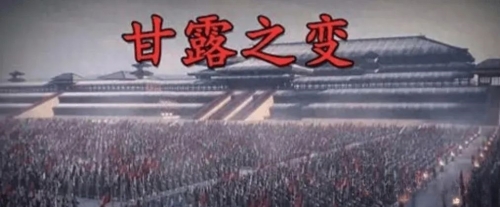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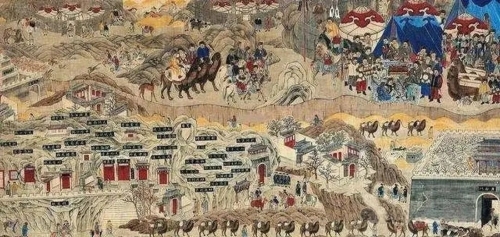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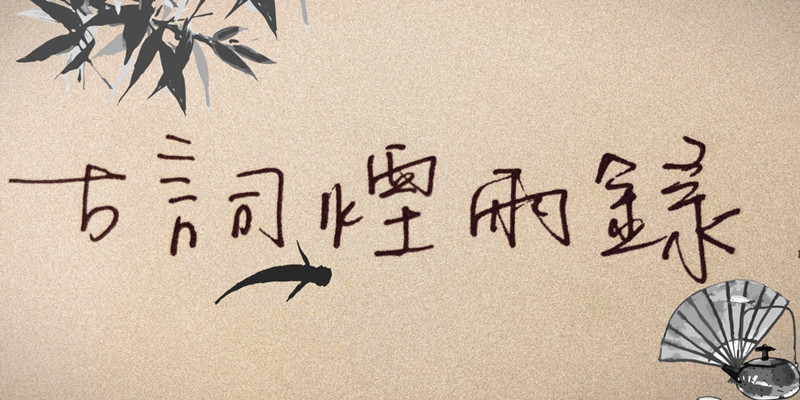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