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插图 周川
自行车
傍晚的铁中操场影影绰绰,不少是在学骑车子的,有从家里偷偷把自行车推出来的同学,颐指气使——“每人只能骑一会儿!排队!”
刚学骑车是“溜车”,推着车子跑,突然站上脚蹬,慢下来之后再推着跑,借惯性站上一边,车子越来越稳,恣晕晕的不想下来。
“溜”顺了就“骑”,腿不够长,把腿从横梁下面伸进去,我们叫“掏腿”,也叫“偏裆”或者“别大杠”。如今60岁以上的人恐怕都熟悉,侧着腿蹬,身子一歪一扭,显得右腿特别长。熟练了,可以蹬得飞快,感觉风驰电掣,神气极了。如果是女士的车没有横梁,那我们正好,身子悬空,重量放到了脚踏上,不讲舒服,要的就是一溜烟。
那时候没有拍照的条件,更没有无人机航拍,我记忆里的铁中操场,一众衣衫褴褛的孩子,三三两两围着自行车喧嚣,有人一手拿着苞米面饼子,一手拿着疙瘩头咸菜,边跑边喊,该我了,该我了,狂追一辆奔跑的自行车;前街邻居建国和他弟弟建军在坡道上挖防空洞,他们不时直起腰来,拄着铁锨和镢头,往操场上看;操场上一些孩子正“掏腿”骑着车子,与另一个“掏腿”你追我赶……
我很好奇,若是有视频拍下来,那些身材矮小的孩子晃晃悠悠骑自行车的情景,仿佛自行车自己在动,“无人驾驶”的场面会不会显得奇异并骇人,或许温馨,也未可知。
那时候我们喊自行车是“决扎车”,老辈人都这么叫,约定俗成,其实就是“脚踏车”嘛,青岛方言的变音。
当年自行车是最实用的交通工具,虽然价格不便宜,但过日子离不开啊,勒紧裤腰带也要置上一辆。
那个年代汽车少,到了晚上,铁路宿舍门前的温州路空空荡荡,路灯底下就是老百姓的活动广场,丝毫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人们对汽车只有仰望仰慕的份儿,公家单位才允许有汽车,除了运输单位,能买得起汽车的单位也不多。
老百姓出行载物,全靠自行车,再低的就是手推车、自制的钢铃车。我看到的自行车好像一出生就是旧的,估计是使用太频繁所致,有的就如相声里所说,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这也宝贝得不行,有的三角梁缠了塑料带,有的三天两头擦拭,有的怕失盗,把自行车悬挂到家里的墙壁上。
我曾经替二哥到邻居家借过一次车子,吞吞吐吐,好不容易说明白了,邻居犹犹豫豫,问了好几遍用车子拉什么,又千叮咛万嘱咐,别忘了锁车,更不要碰了磕了。我脸上一直火辣辣的,诚恐诚惶,推回家后跟二哥说,以后千万别让我去借车,臊死我了。二哥瞪眼剥皮:我去医院接咱爹,家里的事儿,少叨叨!
铁路宿舍东头的同学老苏,他三哥有一辆,是在李村集买的二手大国防,老苏给他哥哥跑腿干活,央求开恩到操场骑一会儿,我们几个同学围着老苏,点头哈腰,老苏骑一圈,我们骑半圈,接班的早早跑过去等着,经常有死皮赖脸的让人撵着拽下。
记得自行车链子会铰着裤腿,冷不丁把人拽倒。有时候骑着骑着失去平衡,好像经常挨摔,腿和膝盖少皮没毛,身上伤痕累累。家里条件好的就抹点药水,创可贴没听说过,更没有去医院一说。那时候孩子皮实,抗造。
自行车还经常掉链子,我们无师自通,把脱落的铁链子抬高,对准牙盘,拿着脚蹬慢慢倒转,链条复位再往前转。双手漆黑,在地上抹几把,在裤子上擦擦,继续骑,乐此不疲。
一次老苏又推出了他哥哥的大国防,我们正在操场上踢球,见状大喜,呼啦啦围过来,见面分一半,好几个人撕拉着轮流骑,不亦乐乎。
也是乐极生悲,大亮子仗着“掏腿”技术熟练,车子骑得飞快,不料与对面骑来的一辆自行车相撞,大亮子满脸是血,对面那个孩子也够呛,趴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
大亮子说我摁了车铃,使劲摁也不响,老苏,自行车铃铛盖呢?
老苏说,我三哥怕别人给拧了去,把盖藏起来了……
那时候社会上偷铃铛盖成风,不少车主经常把铃铛盖拧下来,骑在路上时再拧上。还有的把铃铛盖用电焊焊死,声音不清脆了,好歹防盗。
这时老苏他娘颠着小脚倔哒倔哒过来了,她不看受伤的人,先过去看自行车——哎哟哟,俺家的车子撞坏了没有?老三看见怎么办?谁拿修车子的钱?哎哟哟,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老太太声嘶力竭捶胸顿足。
人穷志短,过苦日子很容易被物质牵着走,设身处地,也许应该理解罢。
是啊,那时候家里称自行车得太少了,社会上流行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件是缝纫机、手表,简称“三转”,都有轮子和齿轮。
结婚能置齐三大件不容易,积毕生之积蓄,加上东拼西凑。老百姓即便有继承遗产的,也在一波波的运动里,家破人亡,遗产被扫荡殆尽。贫穷是一视同仁的社会底色,还越穷越光荣呢!
那时候能置办齐“三转”的,确实不容易,凤毛麟角。我们看到谁家有几件家具,例如饭桌衣橱什么的,或者平时穿了件新衣服,或者过年时布袋里多了两个“二踢脚”,甚至谁家里偶尔飘出了挺浓的香味儿,一帮孩子会异口同声地说“客”!“富人”的意思。“客”的发音是去声,从微弱处说,好像馋涎欲滴时咽下的口水,在力度上,是狠狠吐出的一口浓痰,掺杂着羡慕嫉妒恨。
我一直怀疑,所谓“客”就是“阔”的变音,“穷”的反义词。
铁路宿舍一个老爷子,单位发票买了辆上海的二八大杠,是凤凰还是飞鸽的我记不清了,老爷子喜欢到郊区村镇赶集,长途跋涉来回十分风光,得空就拾掇车,擦得铮明瓦亮,谁上门央求借车也不松口。那天他骑车子去小港的土产店买烟囱,出来后发现自行车不翼而飞,急火攻心,双眼冒火,四处寻找,只是不见车的踪影。
老爷子到派出所报了案,好多天也没见着什么线索,老爷子在家整日生气,心痛,突然就上吊自杀了。
老爷子是济南铁路局分过来的,家人都在农村,亲戚来奔丧时哭着嚎着要政府赔那辆自行车,说全家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其中一个亲戚为车子吵吵,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被抬到自行车上送到了医院。
据说铁路局和街道、派出所也挺为难,最后想方设法给买了辆大金鹿,老爷子的那些农村亲戚欢天喜地地走了。至于是哪个单位拿的买自行车的钱,我始终不得而知。
自行车贵重,总不如口粮重要吧?民以食为天。我听铁路宿舍的一些老人,感慨唏嘘,怎么就投井了,好生可怜。原来是铁路南公司宿舍的一位大婶,背着袋子去买粮,到了粮店才发现粮证和夹在里面的钱,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她差点张倒,哭得死去活来,蓬头散发,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嘴里嚷嚷着全家吃什么,日子没法过了。谁料当天晚上,大婶跑到附近的小村庄跳了井。
听说小村庄的人忿忿不平,一口好好的水井,淘起来好费劲。有人还指着南公司宿舍方向骂,你们那里出门就是铁路,怎么不躺倒铁轨上,还利索。
听到这些话,我觉得身上发冷,老苏他娘吆喝时,我也打过冷颤。
我觉着自行车是美妙绝伦的科学发明,速度好快啊,世界呼呼地往后闪,人动几下腿,把一切都甩在了身后。
羡慕那些家里有自行车的。我缠着大哥,说你上班好几年了,能不能攒钱买一辆?求求你了。
大哥苦笑,说我虽然出徒了,一个月能挣21块钱,可除去给咱家里的生活费,我能省下几个?就是不吃不喝使劲攒吧,一辆大金鹿一百多,攒个十年八年也够呛!就是攒了,或者借钱凑齐了,自行车票谁给?黑市买一张自行车票,没有几十块钱拿不下来。
是的,那个年代买什么也得凭票,都是供应,统购统销,一块豆腐一寸布一两花生油,没有票证寸步难行。
大哥叹气,我很憋气,心里被自行车痒痒的,说不出来的难受。
骑自行车绝对是肌肉记忆,学会了再也忘不掉,哪怕多少年没摸,上去就能骑,和游泳差不多吧,本能,潜意识,源代码。
也许,嵌进记忆里的那些动作和技能,已经与时间深处的快乐或苦难,都沉淀进了生命里。
图片插图 周川
弃婴
青蛙捡到了一个女婴。
我们一帮小伙伴非常吃惊,把一个小女孩捡回家?匪夷所思,反正我是绝对不敢想。
青蛙是我老邻居卫东的外号,卫东说话呱呱的,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外号“青蛙”,铁路宿舍的人就这么叫下来了,约定俗成,改口觉得很别扭,甚至觉得青蛙竟然还有个什么“卫东”的名字,很怪诞。
青蛙是在下半夜挖蛤蜊回来的路上,在路边捡到的,弃婴放在一个篮子里,里面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谢谢你好心人,老人自杀了,孩子没法养,但愿孩子以后不受什么牵连……
青蛙把纸条拿给我们看的时候,我发现纸条最后几行字模模糊糊,好像被水泡了,那几行字写的是:好心人啊,我给你磕头了,让这个无辜的孩子活下来吧,你就是她的再生父母……
后面的字我有些看不清了。
青蛙说当时篮子里还有一个银镯子,还有十几块钱,十几斤粮票。
女婴被青蛙捡回了家,不几天宿舍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很多老娘们去看,回来说小女孩长得真好,大眼睛,小嘴,皮肤那个白啊,她们真想亲她两口。
青蛙的爸爸妈妈也喜欢这个女婴,下班回来就带吃的,青蛙有空就抱着孩子,在街上闲逛。
我们问青蛙,女孩长大了怎么办?恐怕户口也落不上,弄不好派出所还来找麻烦。
青蛙咧着大嘴,说怕什么,大不了我将来娶了她,让她给我当老婆,也挺好。
我们都吃了一惊,你他妈的青蛙才多大啊?竟然想得那么复杂。
因为女婴没有奶吃,青蛙的爸爸就从农村买了一只奶羊,让青蛙挤羊奶喂女婴。
我们一帮伙伴玩游戏,有一个游戏是踢白菜疙瘩,把白菜疙瘩放在地上的圆圈里,一脚踢出去,踢的人撒腿就跑,趁另一帮人把白菜疙瘩捡回圆圈里之前,藏起来。
我们经常玩这个游戏,等另一帮寻找我们的人跑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趁他们找人期间,回来踩住白菜疙瘩,那我们一方就胜利了。白菜疙瘩就像足球场的“球门”。
可是青蛙屡屡破坏我们的游戏,他总是偷走我们的“球门”。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在圆圈里找不到白菜疙瘩,无法表示胜负,后来才发现是青蛙把白菜疙瘩拿回家了。
有一次我踢开以后装作跑开,藏在附近。我看到青蛙拿着白菜疙瘩,鬼鬼祟祟看了看,好像确认没人了,他拿起白菜疙瘩就往家里跑,我从胡同里窜出来,一个扫堂腿,把青蛙扫倒在地。
我气呼呼地问,你为什么偷大伙的“球门”?拿回家你还能吃?
青蛙哭咧咧地,说我是喂羊,奶羊的奶水不够,我的雪儿挨饿。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女婴叫“雪儿”。
我怔怔地站在那儿,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大眼睛白脸蛋的婴儿,我说,青蛙,你拿着白菜疙瘩走吧,我再回家找找,有就给你送去。
青蛙在地上抹着眼泪,拿着白菜疙瘩走了。
那个叫“雪儿”的女孩慢慢长大了,背着书包上学了。我们宿舍里的人都叫她“冷面人”,她好像不会笑,鼻子高耸着,脸上总是冷若冰霜。
我见过宿舍里的一些小孩子骂她:什么雪儿,捡来的孩子!野种!杂种!
女孩站在那里,眉头紧皱,她弯腰从地上捡起石头,恶狠狠地扔向对方,嘴里是骂人的粗话。
不久青蛙一家搬走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雪儿”。
后来我当兵离开了铁路宿舍,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雪儿”的任何消息。
哎呀,掐指算算,现在的“雪儿”已经老大不小了,青蛙捡到她的时候,已经50多年过去了。
那时候的弃婴,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妈或者老太太了。
图片插图 周川
邻里告状
我妈在街道上担任了干部,来找她的人多了起来,他们说些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邻居们之间的七长八短,有时他们还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以示亲近和重要。
我有些糊涂。
不过这些来我家的人,基本上不回避我,在他们眼里,我毕竟是个只知道疯玩的孩子,对那些“大人话”不感兴趣。
其实我听过无数次的话,我还在一边偷偷笑过,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喜欢看书,难道知道什么是“差啦舌头”吗?书面语叫“飞短流长”,背后说人坏话,面和心不和,各种拍案惊奇笔记小说闲书杂书,半懂不懂,连蒙带猜,让我见识了更多的社会世面。
可能老百姓愿意找领导诉苦,或者愿意向上级告状,“媚权”是人的天性吧,妈妈担任的那个所谓街道干部,恐怕连十八品芝麻官都够不上,竟然也颇受邻居们重视。
我不大明白,多少年的老邻居了,怎么就那么多龃龉和矛盾吗?有时候你来反映他的问题,转眼他就过来说你的什么事儿,例如参加街道学习不积极啦,或者帮着农村亲戚卖地瓜花生芋头什么的,上纲上线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
还有说别人小偷小摸的,或者在家里看反动书或者听黄色歌的。
骇人听闻的,那个谁谁,竟然有台湾亲戚,万一是蒋匪帮反攻大陆的内线接应怎么办?
还有说某某乱搞的,某某惯孩子放纵过头的,谁谁在单位挨批判了……
我在旁边听得头昏脑涨稀里糊涂,有时牵涉到男女作风问题,说到破鞋什么的,我的听力骤然灵敏,好像还在聚精会神地写作业,其实那些内容基本上都落进我支楞起来的耳朵里。
唉,是对男女情事不正当的好奇心,在作祟,厚此薄彼。
这次邻居孙大娘一进门,扯着嗓子大声说:“他五娘,咱院里有些人不正经,老王家那个三闺女,像个什么话!竟然把对象领来家,晚上还不走,没登记,没结婚,老天爷唉,年纪轻轻的,晚上住一块了!”
在孙大娘的声音里,我想象着王家三姐和那个大青年在被窝里卿卿我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孙大娘瞅了我一眼,压低声音:“他五娘唉,你是街道干部,这些伤风败俗的,你可不能不管!老王头也不是个好东西,我说恁家老三还没出嫁,对象在家里住不太合适吧?你知道老王头说什么?”
我妈手里缝补着我们的衣服,好像对孙大娘的告状并不太感兴趣,她有些冷淡、应付,对此我很清楚,妈妈对那些鸡零狗碎,一贯的能不管就不管。
我妈说:“她孙大娘,别卖关子了,老王头说什么?”
孙大娘声音又高了起来:“哎吆吆!老王头竟然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说俺家的事儿,与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俺家小三跟她姐姐一块睡的,小三对象走得晚了,没有末班车,是跟俺儿子一个铺,哪有你们想的那些事儿!你望望,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望望,贼喊捉贼嘛!”
我真想不到孙大娘还能顺口说出什么“此地无银”的成语来,想当初黄鼠狼“浮”住你,疼得嗷嗷叫,你那些文绉绉的成语哪去了?
孙大娘喋喋不休:“那天晚上我悄悄趴在他家门上听了,三嫚她对象确实没走,就宿在老王头家里了,一晚上,青年男女,还有什么好事?你望望,娘来!受不了啦!”
经孙大娘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三姐有些不地道,谁知道男的是不是真的没撵上末班车,也许是找理由,特别是半夜里都睡了,蹑手蹑脚爬起来,干柴遇烈火,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没出声,我妈妈也没出声。
孙大娘坐了一会儿,小声向我妈妈说:“他五娘,你不去跟派出所汇报汇报?那些穿制服的听你的,你让路段民警来查查,老王头也太嚣张了,平时不跟我们来往,也就算了,弄个狐狸精三嫚,穿得花里胡哨,见面也不跟我打招呼,作风败坏,偷汉子,不尊重老人,不懂礼教,雾银!”
我妈说,人家三嫚也不小了,按说早该结婚了,听说男的家里没房子,再说这个事儿,确实是人家老王自己家里的事儿,咱不大好干涉啊。
孙大娘有些不高兴,说咱们是老姊妹,你又是干部,要不和你说些那个干什么!
孙大娘说着,从炕上跳下来,扑拉扑拉腚,撅达撅达走了。
孙大娘前脚刚走,后脚又有人推门进来了,是宿舍东头的冯大爷,手里拿着几个无花果,进门就说俺门口树上摘的,这几个熟了,拿来给他五娘尝尝。
我站起来,说,妈,我要出去玩了。
我妈瞪我一眼,说把作业写完,你还当班长,光知道出去疯玩,坐下!
冯大爷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这是小三还是小四?长这么高了。
我妈让我去给冯大爷倒水,我坐那儿没挪窝。
孙大娘那杯白开水,放在炕头还没动呢!
冯大爷笑了笑,说我马上走,来给领导反映个情况。
我妈说什么领导,我是赶鸭子上架,本来在区办化工厂挺好的,让孩子拖了后腿,干这个街道小组长,也是给大伙跑跑腿,咱就是知道了什么情况,也不一定有用。
冯大爷说:“哪里,我听说你还管着治安,我这个事就是治安的,俺院里有偷听外国电台的,戏匣子吱吱啦啦响,我昨天晚上经过他家后窗,听见里面在说外国话,是不是敌台?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我妈放下手里的衣服,站起来说:“他冯大爷,你别急,也许人家是胡乱调台,你看俺对门的爱国家,家里也有收音机,孩子说短波能听见音乐,有时候找不着,就能听见外国人广播,叽里咕噜咱也听不懂,这不算什么事吧?”
“哎哟,他家不一样!”冯大爷非常认真,说:“我是个老党员了,咱的阶级斗争,那根弦,坚决不能松!好几次了,我都听见外国人在戏匣子里说话,昨天晚上我就留了心,趴在他家后窗上,仔细听了好大一会儿,他哪是听什么音乐,全是呜里哇啦的外国话!”
“唉!”我妈叹了口气,“前街龙龙他爹,因为收听敌台被抓进监狱,龙龙去踢球,人家不敢要,去当兵也不行,他家的孩子,全耽误了。”
冯大爷不吱声了,闷闷地坐在炕沿上,呼哧呼哧喘粗气。
我妈小声说:“是不是他家里有人学外语?俺老大厂里,修军舰都学些苏联话,什么俄语单词,咱一句也听不懂。”
冯大爷也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是没事找事,更不是要害谁,咱就是保持警惕,派出所三天两头来开会,让我们检举揭发,党员必须带头,哪有那么多事儿来揭发?是不是?”
冯大爷站起来要走,妈妈说,小四,你赶快去送送。
冯大爷说不用不用,他五娘啊,我说的事儿,咱先不提了,万一弄错了,不大好看。
我妈说你放心,都是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不是来送无花果嘛,没别的什么事儿。
冯大爷往外走着,我高兴坏了,把作业本一推,跳起来,说冯大爷我去送你,正好出去上趟茅房,憋死我了!
我妈和冯大爷都笑了,我心想,可跑出来了,是去踢球还是赢杏胡,抓人?抓土渣?不玩到黑天绝不回家!
2024.7.4
原载 杜帝语丝
2024.7.5 11:58 青岛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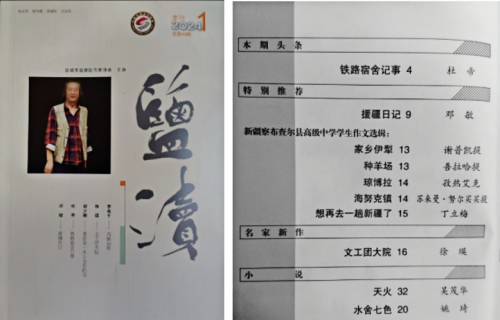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