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天主教的影响力时,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发表文章“教皇有几个师?”,其中谈道:西班牙威权领袖佛朗哥曾提醒庇隆,不要和天主教激烈对抗,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胡安·多明戈(编者注:即庇隆),冷静一点,试着跟他们达成一项协议。记住,教会是永恒的,而我们的政权是短暂的。”
就此冯克利老师评论说:佛朗哥的母亲和夫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今天看这个人,他才堪称卓越的“右派”领袖,其重大历史功绩至少可以列出四项:一是成功阻止共产势力以“共和”名义在西班牙夺权,二是未让西班牙法西斯化,在二战中维持中立立场,使人民免于战争灾祸,也使盟军最后获胜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采取了更加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创造了所谓的“西班牙奇迹”,四是保护了西班牙的法定王位继承人,使后佛朗哥时代十分顺利地完成君主立宪的民主转型。
社会运动是复杂的综合体,里面充满了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思想观念的博弈和角力,前面谈到的是宗教和威权政治的影响力,据说教宗本人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他曾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甚至用“市场暴政”来形容资本主义。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他以他的思想,凭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奥地利一战后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人就是米塞斯。
现代奥地利的版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固定下来的。一战后,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残余的国土不过630万人口,日耳曼民族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甚至不能为这片残存的国土命名,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疆域已不复存在,国民只能自发地把他们的国家命名为“德意志奥地利”。
20世纪90年代,当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鲜花盛开的国度时,仍然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雄伟的皇宫和古老的歌剧院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穿行于具有历史意味的街巷,一不小心可能就被某个伟大的天才人物撞了腰。这里是精神分析法、逻辑实证主义、奥地利经济学的诞生地,不仅仅如此,这里还是一个观念的自由市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学……观念迭出、精彩纷呈,从任何一个方面看,维也纳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的中心。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差点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昔日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上与大师激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一跃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头号人物。尽管时任外交部长鲍尔的权势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总理伦纳。有证据表明,1918年至1919年之交,米塞斯阻止了鲍尔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努力。后来米塞斯回忆说:“完全由于我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主义才没有在维也纳大行其道……我只身一人,单枪匹马地说服了鲍尔放弃与莫斯科结盟的想法。”
米塞斯清楚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布尔什维克化将在短短几天内造成维也纳的饥荒和恐惧,成群结队的暴徒很快就会遍布维也纳的街头,暴力和杀戮将摧毁维也纳的文化与文明。
幸运的是,最终鲍尔的克制拯救了维也纳的文明。米塞斯与鲍尔私交甚好,“他本可以成为政治家,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在米塞斯看来,最终腐蚀了鲍尔智慧、道德操守和个人诚信的,是他的所学和后来所行的那些先验的主义信条。
后来,米塞斯把这些思考写进了他那500页的《社会主义》专著。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总是把人类行为假设为某种经济算式,而米塞斯坚称,这一可能性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市场,就只剩下了个人的价值判断,而绝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
米塞斯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过去,人们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批评过集权式计划经济,但是都没有想过中央计划经济的功效问题。米塞斯优雅而彻底的一击撼动了极权主义大厦的根基,阻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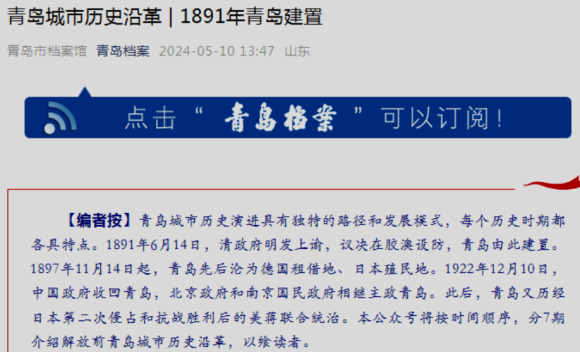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