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历朝历代都说修桥铺路是功德,被当作地方上的大事,方志、人文书籍、民间传说多有记载和演绎,出钱出工的众乡亲也被勒石纪念,可谓桥有名,人有迹。
孙家口石桥如果是孙家口村跨南胶莱河平板石梁桥的名字,它应该是孙家口立村之后修建的,如果是孙家口立村之前修建的,便没人知道它的名字。当然,它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饱含时代特色的名字——青纱桥。
《高密村庄大典》记载:“明洪武年间,孙姓先人首迁此地立村,因地处运粮河岸,为河口地带,故名孙家口,村名沿用至今。”明洪武年间孙家口立村,青纱桥志石背面文字介绍此桥“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假设孙家口立村于洪武末年即1398年,建桥于嘉靖初年即1522年,立村与建桥至少隔着124年,中间经过了建文、永乐、洪熙等10个朝代。
嘉靖朝共行世45年,1522至1566年,青纱桥修建于嘉靖朝哪一年或哪一年之后呢?
一般认为,胶莱河开挖于元至元年间,通航的时间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将淮河中下游屯田所获之粮运往元大都北京。至元二十六年由于会通河建成,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畅通,胶莱河的漕运被废止。
明初,胶莱运河时用时废。疏浚、攒运之事屡议屡罢。嘉靖十七年(1538年)山东巡抚胡缵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惟马颊濠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余里。”嘉靖十九年(1540年),派遣副使王献主管开凿工程。是年正月二十三日破土动工。因“顽石如铁”,“河工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见《明史·河渠志五》),苦战三月,终于开通了“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明史·河渠志》)的人工河段,从而使江淮之舟避薛家岛石牙林立的险滩,直达塔埠头于胶莱。继马颊濠工程之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王献又致力于胶莱运河的全面疏浚工程,引张鲁河、白河、现河、五龙河诸水,以增加胶莱河的水势。同时,建起了“海仓口、新河、杨家圈、玉皇庙、周家、亭口、窝铺、吴家口、陈村”九闸,以调节河道水位。并“置浮梁,建官署以守”(《明史·河渠志》)。尽管分水岭处三十里因工程浩繁,未得疏浚。“船底拖沙而行”。但分水岭“五里下可张帆畅行至海口无阻”(李秀洁著《胶莱运河》1937年版)。后来,由于倭寇为患,明朝实行海禁,着力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胶莱河再次陷入萧条冷落,乃至堙废。嘉靖二十一年,已不能通行。
因此,可以断定,青纱桥建于嘉靖二十一年之后,即1542年之后。为什么呢?因为青纱桥的桥洞跨度不足两米,高度太矮也不够通行漕运船,在这条以完成漕运为使命的河流上建造小石桥阻碍航行是不会被朝廷允许的。
69
青纱桥是一座连通平度、高密、胶州三地的重要桥梁,志书等是否有记?
康熙《高密县志》记载桥梁16座:通济桥、永安桥、大吕桥、王党桥、张鲁桥、里仁桥(县西四十里)、张洛桥、流沙桥(县北八里)、龙湾桥、阳沟桥、亭口桥(县北四十里)、柳沟桥、碾头桥、白衣阁桥、官庄桥、两岔桥。
亭口桥跨北胶莱河,通平度崔家集亭口村,明嘉靖朝设漕运闸,为胶莱河上的九闸之一。未见青纱桥的记载。
民国《高密县志》记载桥梁58座,涉及县北域的桥梁有:夏庄桥、朱家村桥、河崖桥、大石桥(县治东北三十里)、大石桥东北桥(县治东北三十二里)、大栏桥、胶莱河石桥(县治北四十里)。
县治北四十里“胶莱河石桥”条目记为:“与平度县合修,长约七十尺,需款一万余元,由高、平两县第四科各补助洋六百元余,由附近庄村募集。该河跨越两县,工程最大,凡经其地者莫不称便云。”从文中所涉时间看是对民国年间的建桥记载。“大石桥”和“大石桥东北桥”从距离县治所距离看,也非指青纱桥。孙家口距高密城五十里。
平度志书对胶莱河桥梁的统计显示,截至1987年平度境现存胶莱河上的各种桥梁共17座,其中平板石梁桥10座,分别为:崔家集闸口石桥、大迟家石桥、大孙家石桥、大沟头石桥、孙家庄石桥、六七里庄东石桥、刘家口石桥、宅科河北石桥、宅科河东石桥和宅科姚家石桥,亦未见对青纱桥的记载。
青纱桥,仿佛被史书遗落的一颗明珠。
李言谙
2025年4月5日星期六
青纱桥,阿龙摄于2014年12月
2025 年笔记(51)
70
那年冬天,2014年12月,我第一次去孙家口村,直接到刻“青纱桥”的志石下,知道了专门来看的石桥叫青纱桥,之前以为叫“孙家口桥”。我比较仔细地观察了这座平板石梁桥,比之后再来的七八次都仔细。忘了哪一年哪一次,突然发现青纱桥变新了,重新铺设过,那就没观察的必要了,因为它古老的特征被“新”盖住了,连它用的原来的石头还是新的石头也失去了了解的兴趣。
2014年12月南胶莱河剩一点小水,结了冰,人不能上去,冰太薄。2015年冬天没水了,太旱了。2015年11 月我去了离青纱桥不远的南胶莱河上的另一座石桥——平度市万家镇的六七里村石桥,高密市这边叫它王干坝石桥,它躺在傅家口子村北的胶莱河上,我从桥上眺望了青纱桥,想必青纱桥也眺望了我,因为我们都是风景,于是知道南胶莱河彻底干涸了,满沟芦苇和荒草,还有几个王干坝的小女孩,从沟南走到沟北,就是说从高密走到青岛,又从青岛走回高密,我也走着试试,口袋里手机信号来回切换,一会儿漫游,一会儿又不漫游了。
但我还是踩到了冰上,没敢踩实,一只脚在冰上,另一只在岸上,身子的力量停在岸坡上,这是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桥洞,石头也看得更明白。干嘛要明白石头?石桥用石头做的,当然要看石头,难不成看鸟?我找弹孔,没有弹孔。花岗岩可真硬,像驴的性格,子弹叭勾一声射到上面,一溜火星子,连刮痕都不见,落进河水起一阵烟。我想这么硬的石头,这么大个,一块石条少说五六百斤,明朝嘉靖年间,全是人工,采石要人工,石料从山上采下来,那时候用炸药吗?光靠打眼我觉得够呛,放炮炸的话采到这么大的石料可不容易,都碎了,再说古人知道怎样保护生态,绝不放炮。有炮也不放。我也就说说,一百个我一百天采不来一块石头,建一座石桥得八辈子。这还不算,弄下山,还得运到河边,怎么运?要我就用嘴,因为我不会用别的,而且亲自用嘴,或者请几个网红,网红擅长用嘴。用嘴运是智慧。弄到河边,然后找来一百单八个石匠,有天罡,有地煞,来加工石料,必须手工操作,一锤一凿,一斧一斩,经过成百上千次的捶打錾凿——一遍剁斧、二遍剁斧、三遍剁斧……面找平,棱找直,卯一下榫一下,都得事先想好,想不好要命,毁一块石料比毁个人都心疼。
我看青纱桥是先在河底铺一根石梁做基础,然后石梁两头分别立同样的石梁做桥墩,然后顶上又横一根石梁做上梁,条石板竖着铺到上梁上,并列三块,然后一座石桥就成了,非常简单。一只小小鸟从胶莱河飞过,冲我拉屎,还大叫一声:蠢!
我脸一红,高潮来了,像熟了的高粱,垂了垂穗子,怪不好意思的,又斜眼看石头,还是没看出什么,还那个样——蠢!不过有一个桥洞底下的水没冻住,还哗哗哗哗地淌,这个声音吸引我,镜头推上去,吓我一跳,脚下的冰咯嘣一声,吓我一跳:基石悬空着,河水穿过石梁底下朝外流。这怎么可能?又稍微往河里挪一点,大概两三个厘米,冰继续咯嘣,再把头歪厉害一点,吓我一跳,我看到石梁被几根立柱支撑着,柱子还不粗。怪哉。
我善于学习。之后持续好几年我琢磨这事。我一直琢磨。琢磨是我的常态。我琢磨到今天。桥基底下流。不明白。我明白的事不多。多一件也无所谓。少一件不如多一件。立柱和智慧有关,或无关,我知道。
李言谙
2025年4月6日星期日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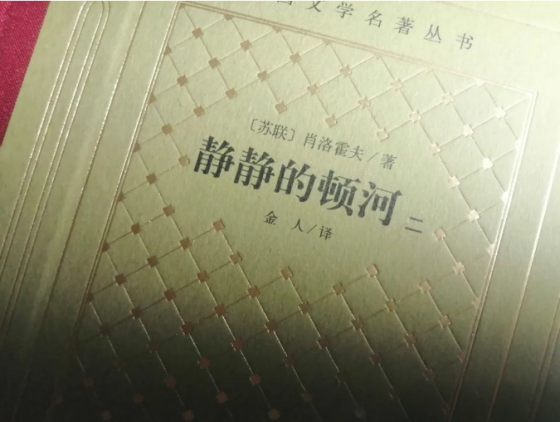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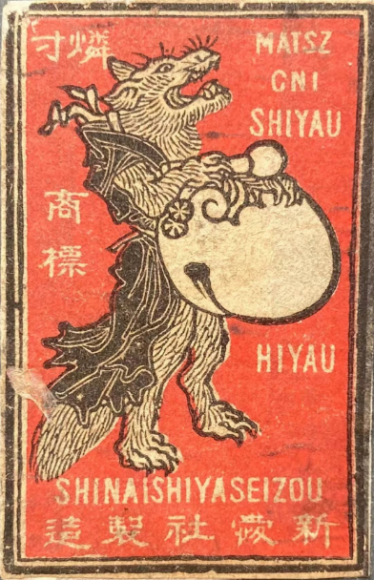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