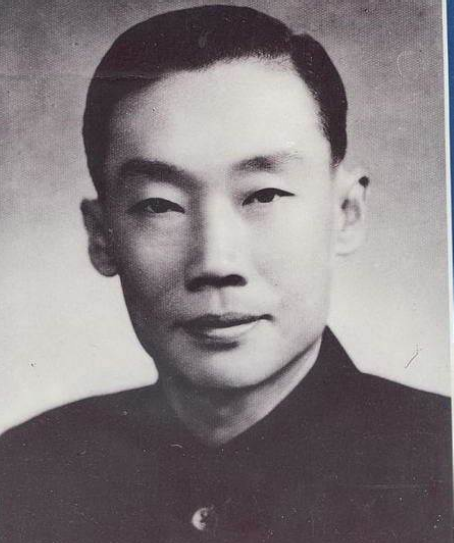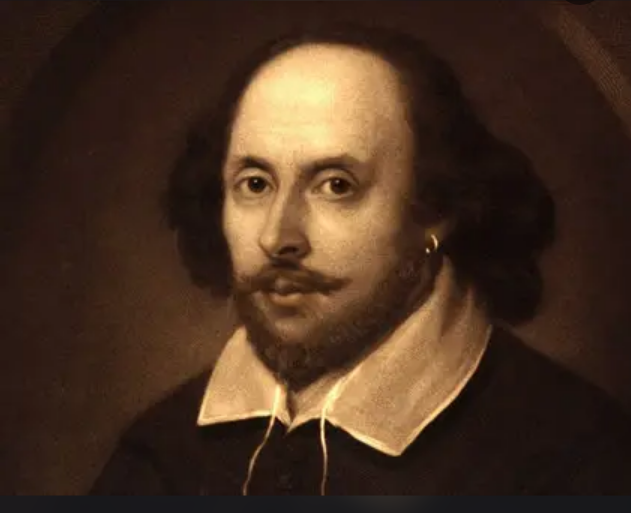什么是诗?一提这个问题,人们必定首先想到辞书上是怎样定义的,那是最信得过的标准答案。但是中国几部最权威的辞书很多定义却都存在问题。例如关于诗的定义,就不能恰到好处地说明“什么是诗?”
(一)
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现代汉语词典》与《辞海》是这样对诗定义的:“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①;“文学的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排列成行”②。
这样的定义看上去无可厚非,诗的语言确实“精炼而形象性强”,诗都是“有节奏、韵律的”。然而细细想来,两部权威工具书的解释,似乎忘记了:《古文观止》里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不都是“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能说《古文观止》里的那些经典散文是诗吗?
中国古代散文,大都有“有节奏、韵律”。且不说汉赋、骈文中的“节奏、韵律”是每个诵读者都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喻户晓的《论语》,稍有点古汉语知识的人,不都明显地感觉出《论语》中的“节奏、韵律”?
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古代散文里的语气助词特别多?原因就在于古代散文非常讲究“节奏、韵律”!这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突出特点!大部分今人有所不知:古人的散文不是用来读的,更不是默读。古人读散文都是吟诵,即散文都是发声唱出来的。这是古代散文之所以有“节奏、韵律”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古代散文有“节奏、韵律”而把它看做是诗吧?
至于说诗“反映生活,抒发情感”——难道还有不反映生活、不抒发情感的文学吗?这种说法类似于问“张三是什么?”有人回答“张三是人”。这个回答没有错。但谁听了都不会满意。因为这个回答仅仅指出了共性,没有说出特性。如果回答“张三是深圳家电公司负责国际销售业务的经理”。这个回答就有点抓住特性了,别人听后就明白了。所以下定义,仅道出共性,虽然没有错,但不能说明问题。只有抓住特性的定义才能说明问题。很显然,《现代汉语词典》与《辞海》关于诗的定义,仅概括了诗作为文学体裁的共性,没有抓住诗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特性。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与《辞海》关于诗的定义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两部辞书里的其它概念(定义),也存在这个毛病。这是权威工具书存在的一个严重失误!当然这个失误绝非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编撰人的水平问题,抓不住被定义者的特性。
于是看来,所谓定义仅仅指出“正确的”共性,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是没有必要的。定义必须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特性。不难看出,用共性定义虽然简单容易,却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废话。这样的定义给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让人奇怪的是,像《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这样权威的工具书,都是一流的专家编撰,又经过大师级的学者审阅定稿。在给诗定义时,怎么能避开诗的根本特性,不着肯綮地说了一堆“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废话”呢?
(二)
探讨诗的特性,需要撇开文学的共性,从诗与其它文学体裁的差异中认真辨析,才可能发现其它体裁文学所缺的、唯独诗才有的特征。这要从人类为什么写诗谈起。
众所周知,人人都有表达思想情感的欲望,这是人的天性。人之所以要写诗,主要原因是,。当平常的语言文字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时,便想到了用诗一吐为快,因为诗含有一种音乐性可以弥补语言文字的不足。其中的道理十分平常:
常言道“男愁唱,女愁哭”,其实都是人在特殊情况下,语言“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时,男女各自采取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实现尽情倾诉的目的。男人的“唱”,可能是一支歌曲;也可能是一段戏曲唱腔;更多的可能是,在愁绪中亨出的一种“曲不成曲,调不成调”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听起来大都是顺耳的。男人的愁绪在这种顺耳的“曲不成曲、调不成调”中变得明晰起来,于是心情顿时痛快了许多。女人易“哭”是天性。但“哭”毕竟是一种劳力的行为,即便是“天塌下来了”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哭”,由于受体力的限制,“哭”声不可能老是停留在强烈的高音区,它会不由自主地滑向低音区,以便继续“哭”。何况“哭”也是一种思想情感的倾诉,凡是倾诉都想打动人,所以“哭”的声音至少在“哭”者自己听起来是不能刺耳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哭”便在高低、强弱、快慢、长短中呈现出一种很有音乐感的声调,所以有人发现寡妇哭坟的声音有高低、长短、快慢的变化,很是顺耳,可以记谱。据说乐曲《寡妇哭坟》就是音乐家从民间寡妇哭坟时记谱后整理出来的。实际上“男愁唱,女愁哭”,是人在“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时,不自觉地采用了音乐的方式。因为音乐在表达人的思想情感上有着神奇的全能功用,人类千差万别的各种情感,都可以在音乐那里得到表达。听一首歌词的念白,与听这首歌的唱腔,给人的感受大不一样,其艺术效果有着天壤之别。所以音乐有着人类共同喜欢的情感魅力,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人说“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最远离人类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他们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会用唱歌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声调虽然很简单,毕竟是一种可以记谱的音乐形式。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本能。
据考证,诗在远古时期是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这种诗、乐、舞的“三位一体”是先人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例如远古人打猎有收获,大家因此饱餐一顿。饭后都很高兴地一边跳着(舞)一边哼唱(乐)再简单不过的词(诗)。随着人类的进化与文化的进步,舞、乐、词(诗)各自独立出来,出现了舞蹈、音乐、诗歌三种艺术形式。诗从“三位一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但仍保留着音乐的特性,于是人类文化便有了千百年进化出的最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字形式——含有音乐特性的诗。所以诗中的音乐特性,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特征!是构成诗的最重要元素。一首诗若无音乐性的声调营造的情调,那诗的文字再好也肯定没有了唯诗的乐感才有的诸多情意、情趣、情思及情不能已中引发读者的浮想联翩。诗缺了音乐性情调,诗味也就寡淡了许多。例如那些“白话文断句”的新诗,没有、也无法营造音乐性情调来。这样的诗类同短小的微型散文,已经不能称为诗了。所以谈诗,无论如何不能避开音乐。那么,音乐是什么呢?
(三)
生活中大部分人不识简谱,更不用说五线谱了,所以一般人以为音乐是什么高深玄妙的东西。如上所述,既然“哭”因其高低、强弱、快慢、长短而成为悦耳的声音可以记谱;那么人在欢乐时踏着高低、强弱、快慢、长短节奏形成的声音不是同样可以记谱吗?生活中这类随着高低、强弱、快慢、长短节奏出现的声音,经常可以听到;或因其好听,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细究起来,这种声音之所以听了舒服,一是有节奏,二是有起伏万状的变化,这便是音乐的全部奥秘。明白了音乐的这个“奥秘”,就会发现音乐是人类生活中的平常现象,只是平日里人们并不在意,以为音乐属于音乐家的“专利”,是供高贵阶层欣赏的“阳春白雪”。所以,被一般人视为高深莫测的旋律,其实并不高深莫测,不过是声音的一种特殊运动,是变化中的声调,只是这种声调让人听起来有种快感罢了。只要抓住节奏与旋律这个音乐的基本要素,“音乐是什么”便成了一个明白易晓的问题——音乐就是旋律,旋律是声音伴随着节奏在高低、强弱、快慢、长短的变化中出现的声调。旋律是一种和谐悦耳的声音,是人类共同喜欢的声音。
既然诗必须带有音乐性,那么作诗就要首先考虑用相关手段营造出既能传情达意,又能让人听了有快感的声调,这是作诗与写文章的根本不同。诗的这种不可或缺的音乐性情调,都是在出声的吟唱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认为,诗词不能朗诵只能吟唱,因为朗诵念不出诗中的音乐声调,反而是对诗味的一种损害。通常见到的古典诗词表演会上,演员那或抑扬顿挫、或低回婉转的吟唱,类似歌唱家的歌声,也有着绝妙的听觉艺术效果。吟唱与朗诵的区别是明显的:朗诵是一种高声念白,并无音乐感;吟唱则不同,吟唱中所有的字词都要随着高低起伏的调子出现,从而使诗的语义融化在旋律中,合成为一种美妙动听的“交响曲”,吟唱者在这一“交响曲”中全神贯注、声情并茂,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听者也在闻其声的心领神会中渐入佳境。古典诗词吟唱中的这种妙入神的现象,犹如音乐会上的听众——会在声调中很快地进入角色,跟着乐曲的旋律不由自主地任凭情感的幽灵,游荡在乐曲声飘逸出的神奇美妙的天地里,尽情其间、流连忘返。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没人先去琢磨乐曲的文字意义后才进入乐乡,都是不由自主地被旋律的声浪激起情感的波澜,忘我其中。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自古就有“听诗”一说。实际上,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审美意义上的听觉艺术有着妙不可言的神奇魅力——这是古人所以能历经千百年的不懈探索,终于发现格律(五言、七言、对仗、黏连、平仄音律、押韵)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汉语写诗只有格律才能既游刃有余、又恰到好处地营造出音乐性情调来。从而实现诗不仅是文字意义上的文学,更是听觉艺术上的文学。
其实不仅诗是“听觉艺术上的文学”;京剧也有着同样的道理:例如京剧在明清以后二百年间风靡大江南北,是深植于庙堂之上、江湖之远中雅俗共赏的艺术,但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坊间百姓,人们都说听戏,不说看戏。戏迷们都深有体会,只有“听戏”才能领略戏曲旋律的万种风情。
有听诗经验的人都知道,诗的声调与纯音乐的声调大不一样,诗的声调因融有语义的灵魂而更加浑厚多情、妙趣横生,弥漫出一种出神入化的氛围,洋溢着令人神魂迷醉、心魄震荡的情调。唯其这种情调,才是诗在文学园地里最动人的妙处所在。毋宁说,这种情调对读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于是看来,诗的特点,是一种涵有音乐性的情调,这是诗之所以在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在文学天地里,只有诗才能——用语义、韵律、节奏、句式、字数等不可或缺的相关元素与手段,营造出一种声乐中的美感情调,这是语义与音乐共同造化的结果,是只有诗人才能实现的文字与音乐的浑然天成。关于诗的定义,只要抓住这个特性,诗在文学中便有了与众不同的清晰面目;诗的独特魅力,也会愈发光彩起来;所谓诗词欣赏,在诗性的烛光映照下,可能入木三分了。
(四)
通常所说的古典诗词欣赏,主要是体会其中的情调给人带来的审美享受,即人在诗词涵有的情调中产生的美感体会。毋宁说,这种情调美非同人体美、风景美那样直观,而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含蓄美,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美,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这种美因其处于朦胧中而愈发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吸引力。古典诗词吟唱中出现的“曲终情未已”,是普遍现象,说明这些诗词都有着令人回味无穷的神奇魔力。诚然,诗词情调给人的审美享受,是在欣赏者的感觉中出现的,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由于人在感觉时的心情、兴趣及审美水平不可能一样,所以诗词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见仁见智,不会有统一的看法与结论。越是优秀的诗词,其情调越是有一种扑朔迷离中的魅力,越是散发出类似“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万般风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诗词是不可以讲解的,通常的诗词讲解,不过是讲解人表达个人的审美体验与情感体会,万万不可作为统一“答案”,听者只能作为参考自行感觉。常见语文考卷上有古典诗词让学生翻译,既是强人所难,也是批卷教师自找难看——哪来的统一答案!这样的考试,最终是让学生都有教师个人的那种诗词情调感觉,这怎么可能呢?何况古典诗词不是用来默读的,而是应该出声吟唱的,不吟唱怎么感觉诗词的情调?可以看出,这样的考试很不科学,不但用教师感觉出的“统一答案”扼杀了学生独立感觉的能力,而且容易造成学生僵化的思维习惯。何况在一定意义上说,翻译古典诗词,就是翻译情调——情调都是该文化才有的格律营造出来的!所以古典诗词的情调是其它文化无法翻译的!
实际上,以音乐性情调“一枝独秀”于文学园地里的中国古典诗词不仅“不可以讲解”,甚至是难以再造的文学绝唱!众所周知,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天才,一个是阅历(社会土壤)。道理很简单:
没有亡国之君的苦难经历,不会有震铄古今的李煜词;同是亡国之君的宋徽宗赵佶,也是写词的高手。但赵佶的词与李煜的词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个文坛共知的案例说明,伟大作品的作者都是天才,但天才的阅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都说中国古典诗词是世界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却鲜有人看到,这朵奇葩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这里无法展开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生长了古典诗词这朵奇葩?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诗词:
那是中国人在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唯一可以畅通无阻的心灵桥梁;是历代文人用单音节的古汉语,遵循着千百年摸索出的格律规则创造的艺术精品;是只有单音节的古汉语才能创造出来的东方艺术瑰宝;是大千世界里一道五彩缤纷、气象万千的艺术风景。漫步在这道风景里,会为山河的壮丽骄傲;会为古人的智慧惊叹;会为历史的沧桑感怀;会为爱情的悲剧落泪;会为人生的苦难怆然;会为历代文人的怀才不遇感慨万千……。在这道风景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凡有见识的历史学者,都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看古典诗词,里边有着证实、证伪的实证力量,这是世界史学中独一无二的奇观——不过这已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
(五)
有人可能不同意“诗的主要特征是音乐性情调”这个说法。例如新诗,既无铿锵有力的节奏,也无音律(平仄)与韵律(不押韵)。能说新诗不是诗吗?
新文化运动以降,写新诗的人如过江之鲫。新诗也垄断了现代诗坛一百多年。但,什么是新诗?——如果说概念中的定义必须抓住被定义者与众不同的特征。那么,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除了“白话文断句”这个“特征”外,新诗与古典诗词、与散文、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较,还有什么独有的特征呢?但是“白话文断句”,这是连小学生都会的把戏!谁不会把白话文句子断开、排列成行?也就是说,谁不会写新诗?但是,诗在任何民族文化里都属于“阳春白雪”。常识告诉我们,凡是“阳春白雪”的文学艺术,在创作上都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不是谁都可以涉足的。白话文断句的新诗虽然谁都会写,新诗大众化了。但新诗没有“音乐性情调”这个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特征,在诗的本源意义上说,还能叫诗吗?何况新诗虽然垄断诗坛一百年了,却至今没有形成新诗成熟的、定型的表现形式。要知道,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一定的内容都是由相应的形式予以表现的。离开形式,内容则不复存在,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没有价值的空壳。正是在这个道理上说,格律是单音节的汉语写诗不可替代的形式——唯有格律才能体现出诗之所以为诗的音乐性情调来!但是新诗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这样说并非是否定新诗的价值。本文不讨论新诗。这里所以谈到新诗,仅是突出一个看法:汉语离开了格律,是很难营造出音乐性情调来的。或者说格律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胡适那代人提倡新诗,只看到了古典诗词格律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人在创作天地里自由驰骋;限制了作者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浮想联翩”。
殊不知,古典诗词所以成为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都是古汉语利用格律这种形式才能营造出的艺术品性的使然。胡适一代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是没有看到:隋唐时期格律诗的成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这座里程碑隐含着:古代文人历经千百年的探索,终于发现格律既能心应手、又能淋漓尽致地创作出汉语诗的音乐性情调。从而使作者思想情感在“一吐为快”的爽然中完成了一件文学艺术精品。
看过胡适写的那些寡淡如水的新诗就知道,胡适不是诗人,也不谙写诗之道。抛弃格律诗的胡适有所不知:被誉为“中国文学大厦上的皇冠”的古典诗词,不是像他写新诗那么简单易行——正因为太简单了,所以胡适的新诗都是速朽的文字。而古典诗词创作不仅有着格律的“循规蹈矩”,还有着完稿后的反复“推敲”。优秀的古典诗词不可能像新诗那样“一气呵成”,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出来的。北宋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是名篇。其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更是脍炙人口。但这首词写出来后,晏殊一直不满意,一年后才在别人的帮助下完稿,终成传世不朽的优秀作品。
实际上中外诗家都认为写诗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因为诗要表达出音乐性情调来,必须用这种文化特有的相应形式才能实现。这种唯该文化才有的特殊形式,便是写诗的“镣铐”,其实就是诗的格律。只是东西方文化中写诗的格律不一样罢了。离开了这种该文化固有的格律(“镣铐”),写不出有音乐性情调的诗来。这个道理本来是写诗的常识,这个常识却被胡适那代人忽视了。诚然,发现这个常识(格律)——中国古代文人经过一千多年的的探索,才在隋唐时期定型下来。鼓吹新诗的那代人,怎么可以轻易地抛弃先人留给我们多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
新诗在“火红的年代”曾经一度领中国文坛的风骚。随着理性的回归,“火红的年代”寿终正寝后,新诗便没有了昔日的风光。社会上出现了“写诗的人比读者还多”的尴尬局面。新世纪以来,古典诗词沉寂了一百多年,又“重见天日”。古典诗词虽然是“阳春白雪”,却深受大众欢迎。有人在沿海地区做了一个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有古典诗词读本!特别是少儿阶层,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都能背诵几首古典诗词!但是少儿中几乎没有人喜欢新诗,也没有人背诵新诗。古典诗词“进万家”这个现象,与新诗的尴尬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普通大众读古典诗词是有阅读障碍的,但大家喜欢。特别是少年儿童对古典诗词有更多的“隔膜”。少儿背诵古典诗词却有点“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绝非是专家谈古典诗词所讲的那些“旷远的意境”“苍凉的情调”“万千的气象”“豪迈的气度”“精妙的语言”等这些审美意义上的艺术特色所吸引。主要原因是普通读者与少儿在诵读古典诗词中,都会很快地进入诗词含有的音乐性情调中。这便是音乐的神奇魔力。现代人大都不会吟诵,但是,即便一般的诵读时,格律诗在五言、七言固有的铿锵节奏与诗句的韵律(押韵)声调,汇成了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都说音乐没有民族文化上的国界,音乐也没有年龄的“国界”。这是古典诗词“老少咸宜”的根本原因。
古典诗词在今日中国出现的新气象,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诗词走了一百多年的弯路后,出现了“正本清源”的希望!
注: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