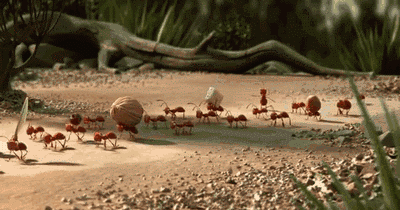历史的主体总是把他的意志和他意志的粉饰强加给公众,个体被时代的政治话语符号所覆盖和定义,在这种被定义历史中,注定了其命运和话语方式的被动性。个体在历史主体的概念化的话语下是缺少个性的,他们的命运也被历史锁定。个体不一定是历史的洞察者,但个体对自由与个性的出自本然的热爱让他想跳出这种历史命运的强迫和被动,但命运的结局往往是悲剧。这种历史主体的整一性与个体对个性的狂热的表达构成了话语的对立与差异。如《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他对那个世界充满怀疑与悲绝,最后以遁入空门作为结局。我想在结局的处理上高鹗是个创作的高手,我想他对曹雪芹的创作初衷是感同身受的。文学家不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他们关注的正是在历史的征途中,那些早已被定义的个体在历史幽微的隧洞中命运的呻吟和无力。其实贾宝玉只有做个活死人——遁入空门,我想这种命运的安排比让他去跟李黛玉一样死去还要耐人寻味。
我一直把贾平凹的作品《废都》看做当代文学作品的扛鼎之作,所立论的基点正是他对历史个体的关注与把握,在贾平凹的作品《废都》中庄之蝶的命运与贾宝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是对社会充满怀疑的历史中的个体,但他无法对社会改变什么,在这种迷茫的围剿之中,他选择的是一条堕落之路,他一方面对社会厌倦与疲惫,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拯救。他是矛盾重重的人,他堕落在肉体的享乐当中不能自拔,在结局部分他的泪流满面正是把他的矛盾心情推向极致的一个高潮,他的对自己的命运的不可预料充满悲凄。他难以跟“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相比。黛玉是宁要碎玉、不求瓦全的外表柔弱内心刚烈的奇女子,她的死可以看做跟那个浊世的最后一搏,她用死表达了自己的高洁情怀,以及不甘受辱的个体生命的尊严。我想,迷茫个体的种种行为方式和命运结局窥见了在历史主体话语下个体的现状与微弱的生息。他们的命运与历史构成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在这种对立中,个体的声音或许会被历史的主体话语所遮盖,而文学把这种声音给“发现”出来。
个体与历史主体的关系构成了文学表达的主要切入点。在坚实的历史主体面前,写作的态度取决于作家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对历史的态度。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把个体在历史主体的碾压下的异变表现出来;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现的也是个体与现实的冲突。海明威像一个美国牛仔,把自我全方位地投入到这种征战当中,而他最后以不承认失败的失败而失败,虽然以死相抗,保持了人得高贵的尊严,但也可以看到老人努力下,人生荒谬与抗争的悖论;而加缪的写作正是对生活的荒诞感与无序感的寓言化的处理,把一个真实的人生真相告诉我们。
中国从四九年以来,政治功利性的话语被带进创作中,遮掩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的声音。文革期间把领袖崇拜与政治话语的语录化,个体处在随时被包剿与囚禁状态,暴力与强势的政治话语以及政治狂热的热情构成了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现状。那时个体的声音是被捆绑在历史主体的直至话语之中,这种谬误经历了很深的历史阵痛才得以修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改革文学,把带有强功利性的英雄暴发户的奋斗史写进文学,把文学降低为为暴发户树碑立传。而报告文学这种体裁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种文体,担当的正是这种带有强功利性媚俗角色,文学被贬低为一种为资本和时事服务的工具。而这种文化身份的降低是资本对文化的总体购买,文化总体降低为一种专事广告与造假的工具。
个体的声音在哪里?关于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个体的现状如何呢?现在的个体处在一种虚幻的假象当中,对物与理想倒塌后的荒诞,构成了当代人精神流浪的现状。这种流浪感不是个体对意义苦苦求索表现出的焦虑,而是对拜金主义的推崇与盲目无聊狂欢精神所迷惑。这种生活的无序与无聊感,增加了某种程度的喜剧效果。
萧联强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