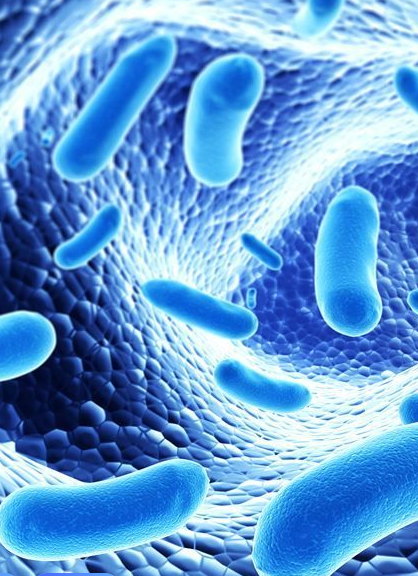诗人胡香和女儿
知道胡香,缘自诗人尚飞鹏2000年评述陕西诗人的长篇论文。写胡香的那部分,内容已经淡忘,但小标题“一个无法解读的胡香”,却记忆犹新。随后,有了博客,才有了真正阅读胡香的机会。作为1960年代生人,胡香上中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此后陆续有诗歌、散文、小说等见诸《诗刊》《中国文学》《延河》《美文》等刊物,入选《陕西女作家作品选》《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出版诗集《摇不响手上的小铜铃》。但如今,对于健忘的诗坛,甚至陕西的文学圈子,胡香的名字仍是陌生,知道她的人寥寥无几。
这么多年,胡香一直游离于诗歌圈子之外,就是在朋友们并不频繁的交流互动中,她也时而“在线”,时而“失联”。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她的生活和写作状况,更不用说内心深处的想法。胡香真的就像一个谜,“无法解读”的谜。其实,我们不用过多猜测,通过作品就能对她的生活或心理状态有所洞察。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披露,尤其是胡香这种从生命和灵魂深处发出的歌音。
阅读胡香,就是阅读命运。
当这个句子从脑海蓦然闪现,连自己都觉出几分错愕——命运深广莫测,胡香其人其诗何以等同命运本身?这话如若成立,我自己也需要一番深究,很可能触及“诗与生命同构”这样的话题及事实。胡香到底经历了哪些苦厄与痛楚,煎熬和挣扎,才让她不断地放低自己,甚至否弃自己,才写出“贴近额前的烧红的烙铁”,写出《地狱里的歌吟》?
但就在这时,另一位女诗人内心的声音,在我的耳旁萦回:“悲伤禁止询问!”
是的,阅读不是窥探,也非揭秘,而是满怀敬意的寻访,或许并不对等的对话与交流。如果谈到指认,那也是审慎和有所保留的。在浮华动荡的潮流底下,那沉静乃至沉寂的深处,真诗人存在着,甚至缄默着。长久的缄默让诗,真正的诗,从幽暗无名处蓦然显现。胡香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潮流之外的写作者,她坚持、存在状态,以及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和气质,给我带来很多启示。我相信,在现实世界,诗不仅以非诗性的因素传播,更以自身纯粹的方式而存在。就像胡香的诗,至今依然躺在博客寥寥几个页面,在虚拟的空间里独自言语——那长久未曾打理而几乎蒙尘,却闪闪发光的分行!
然而,灵魂深处的歌声,绝非炫人耳目的复调与花腔,它往往是自我的,寂寞的,甚至就埋在歌者哑默的舌根。胡香自己也说:“我在浓冬里写着无人阅读的诗歌/只是为了将诗献给诗本身/一种纯粹的感性的宗教/一种向生命和审美献礼的仪式”。
组诗《冬天》《梦境》《事物》等,是目前能够见到的胡香最早的作品,收入小辑《梦境谁能住》(2005-2007)。然而,这样一种“开端”,展现给我们的却是成熟诗人的状态:言说(语言)时而简隽时而放任,情感真挚而有力度,带着慧思的洞察赋予事物(诗歌)一种深度。比如,她写《崖畔菊》:“将这灿烂如同纯金的生命/变成探测深渊的手臂”,写《凤尾鱼》:“宁做凤尾/直至天堂失火/翅骨粉碎/用沉默止痛/潜入深水/变成永不说话的异类”,而在《醒来》中,她的表达如此决绝:“迎着剑尖 张开眼皮/向死里去索命”。小长诗《震动》,在惊悚的场景和血的现实中,写出一代人精神求索的历程;孤句“但却并不到此为止”的反复出现,加深了那种状态的幅度和强度。《一枚看不见救不起的羽毛它想说什么》,展示了细节的力量,以及细微之处语言和内心状态合一的力度:“然而,太细太细太细了。/这细如布满倒刺的钢丝锯条一样的丝弦。/我已握得太久。/手心里有了/不断切碎的火焰/反复断裂的冰碴/和蛇信子不断幽蓝的光芒。”这些“早期”诗作,无论在语言形态、情感基调或题材框架等方面,都成为胡香诗歌的“储备”或“原型”,并烙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
2008年的诗作,被诗人命名为《沦陷于细节或迷于绿》,精粹的作品多了起来,像《普赛克》《银狼王》《转身》《一如既往》《旷野无门》《时间的鞭痕》等。在这里,我想说说其他几首。《羽林郎》融合东西方文化元素,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涉及女性命运以及那古老的哀愁。而且,这种叙事性风格在胡香的所有表达中,也并不多见。《香》是一首容易被忽略的诗,只有细细品读,才能感受到词语运用的精妙,诗意的深厚和绵长。这首诗很可能始于自我比拟,但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生命之诗”。“神龛已空/它独自燃烧”,也与信仰有关,但这信仰之路已是被离弃的道路。《一只鹿被细节埋葬》也是凸显了细节,并由词语的联想和暗示推进叙述。这是一首带有悲剧意味的“命运之诗”,连诗人都禁不住这样发问:“天使在哪里呢/请你说话/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夏甲,迷于旷野的夏甲 天使安慰你》,取材于圣经故事,其魅力不限于抒情的朴素真挚及谣曲风格,还因较强的带入感而具有了某种戏剧性。
对于胡香来说,无论调动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抑或古希腊文化元素,最终都是为了进行生命意义上的表达。而且,这样一种诗歌运作方式,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厚度和广度,甚或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启明。
《生者与死者同在的大地》,是胡香2009年的创作,这样的命名已经为我们呈示了一个开阔多维的存在场域。这一年,胡香的写作进入喷发期,愈加精粹的作品不断涌现,像《我愿如方济格一样,问候我的命运》《美是困难的》《塞壬在歌唱》《我在清晨朗读忍辱波罗蜜》《我梦中的火狐尚未到来》等等。而且,在她众声奏鸣的诗歌音调中,一种低沉却有力的“音型”凸显出来:悲怆之音。诗人带着自己易碎而又柔韧的心,深入命运的荒寒、孤绝之境,感知、发现和体悟,感人至深地歌吟。她说:“我的废墟已经到来/我的死神也已上路”,她向万能的神发出祈祷:“请你救拔每一颗孱弱凄冷的心/把光明和希望给她/让她聆听这大地上万物生长的妙音/让她坚韧,度过每一条心怀叵测的暗沟与坎坷/让她平安地抵达死亡与永生之门/不再沿原路返回”。胡香无畏地凝视深渊,因为她已是深渊的一部分。但长久的沉溺并未导致沉沦,她向着心中的“蓝色高地”超拔和跃升,又从隐忍悲痛中淬炼出达观和智慧:“精神的流浪儿和他孤独无告的灵魂/既不冲突也不和解/他们门里门外两相为邻”。
如此沉痛却富有洞察力的表达,一直延续到2010年的《地狱里的歌吟》,甚至有加剧的倾向。这一年,胡香写了77首诗,是她最为高产和优质的一年。毫无疑问,这里的“地狱”是一种存在境遇,也即那种“深渊”。面对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却不必过于悲观,因为这“黑夜时间”,也必然是“救赎的时刻”。诗人看见:“道路与歧途一并展开”,于是祈求:“让我在一缕微光里/身处地狱而能仰望天堂”。那只有在绝望的灰烬中才能生发的热情出现了,那是感恩和礼赞的声音:“死亡与新生如此毗邻/永恒的歌赞属于两者”,“赞颂是神的事业/我只是在这早春的祷词里/响应着神的召唤”。这“地狱”般的处境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深刻的洞察出现在对“通灵的孩子”兰波的抒写中:“彩虹依旧会将每一个越境的孩子罚入地狱/那幸福与灾难/那永夜与极光 同时降临的时辰/人类的孩子/怎堪承受那巨大的被禁绝的秘密”。
于是我们得以倾听,那从低沉却有力的“悲怆之音”中生发的“神性音型”:在不堪和无望的境遇,向至高者发出的祈祷、渴慕、歌赞,以及对话和沟通的努力。这是对自我生命的净化和提升,也是对人生的悲剧性命运的消解或转化。
《时间之书》《沙之书》《灌木丛的风》《向风而歌》,分别是胡香在此后几年的作品集录,“悲怆”和“神性”的音型依然延续着。这些诗,在话语组织、言说方式和观照对象等方面或许有别,但诗歌主题仍可归结为:对生命的至深理解,对存在之谜的不断叩问和探索,以及信仰之路的艰难呈现。诗人自我审视,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外物,拥有“把石头也看碎了”的心力和眼力。在这直达本质的“观看”中,自我和事物已经交织混同,成为一种精神事物或语言的现实。诗人一边又发出悲切更具悲悯的声音:“放过她吧!不要再追问/存在的意义。/……看在/所有青草的份上,不要/记恨任何人,不要贬损任何事物”,一边“学习对不可知的事物保持沉默”;一粒琥珀在她看来:“好时光一过/你像从未开过口一样/保持着你无人能够进入的美/从死亡中永生/在永生里不能复活”,但面对王尔德(包括荷尔德林、布莱克、梵高、夏加尔、兰波、海子等同一精神血型的诗人、艺术家)及其命运,诗人带着深深的理解和认同:“艺术的灵魂找到一具悲怆的躯体”。这类追慕、致敬之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种自我的观照和表达。
胡香的诗,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那不仅是情感的抒发、生命的对话,更是一种精神洗礼。她没有过多地呈现诗歌的社会性主题,为公众及主流文化所认同的那种现实关联,对现实的摹写或反映,而是倾向于生命和灵魂的热切吁求,诗歌的精神性传达。胡香从生命内部、灵魂深处打开自己,无论哀歌与祈祷、感恩与礼赞,都“倾向于美”,倾向源始,努力说出万物隐藏的奥秘,并努力寻求与更高生命层阶沟通、对话的可能。这样,她的诗在芜杂繁乱的诗歌现场,就规避了哗众效应,却深入了生命和诗歌的根柢。
在胡香并不很长,也只有十多年的诗歌呈现中,竟出现了三年空档(2015、2016、2017)。这三年,诗人的写作因故停滞,抑或仅是作品未曾拿出展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2018年开始,她又开始发声,断断续续在博客上贴出新诗,还有随笔作品。正如她所说的:“与世隔绝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多年来不断的离群索居和自我边缘化的生活,让我深知人无法从自我剔除其社会属性。”这样的认知,与她诗歌表达中“身处地狱而能仰望天堂”的道理,如出一辙。或许我们只有在某种极端处境,在事物及其对立面的长久对决中,方能更加深入和客观地对待事物,包括生命、世界以及写作本身。
我们相信“从那幻象之城已经回来”的诗人,也由衷祝福“走过地狱并窥见真理”的诗人!
2020.5.31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