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体的遮蔽处理,大概始于柏拉图。
对于柏拉图,哈维·曼斯菲尔德提醒我们,要构筑出“理想国”的城邦,可能性在于无视人的身体。好像这身体—肉身,成了抵达“理想”的牵绊。
在成为牵绊之前,是怎样一幅场景呢?
“她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你的肚脐如圆杯”“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双乳好像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旧约》中提到的这些《雅歌》,已经贯通了人的身体与外界事物,并且传递了极为巧妙的共性。而在更早的《创世记》中,圣贤者指出,人对自身身体的发现,源于一次好奇的调皮的不听话——背叛了至高无上者的告诫。如此,这身体仿佛一条经久不衰的苦难之河的源泉。
“理想国”的居民肯定是厌恶(如果他们还有喜好与厌恶的话)这具身体(肉身)的。他们冥思苦想一切能抛却这具肉身(皮囊)的可能性。与“天国”同质异构的“净土”,召唤尚在六道轮转的人们摒离“执着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与“净土”同样若隐若现的“三十六天”,则是截然不同的境遇:肉身不灭。看来“身体”在这里获得了永恒的机遇。可行性之一是不间断地服用丹药。在科学盛行的今天看来,这一条件多少有些荒谬,且是对“身体”存续的致命摧毁——以损伤身体而获得身体的不朽,看上去极富辨证的逻辑。
“身体”无论如何都是要消殒的。究竟什么能留存下来?
无论东西,近代以来,对禁欲主义的批判日益盛行。我们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它很可爱,易破碎,稍不留神便会逝去。那个号称“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尼采,猛然变得娇羞了,关注身体,关注身体与思想的隐秘联系,仿佛打开了俗世的一扇天窗——身体是我的,我的身体为我所有。
于是,“我”的身体获得了“史”的意义(个人史),它有留存下来的必要?这与阿奎拉的疑问不谋而合——人的身体何以成为这个身体,人的灵魂何以成为这个灵魂。在劳伦斯看来,血管(身体的一部分)所感受的,经常是真实的。
既然谈及真实性,“身体”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性能弥足珍贵了,而且有了可供把玩的趣味。这一点,在青年诗人茱萸的文化随笔集《浆果与流转之诗》中多有指涉。
二、语言:体液与冷火
在茱萸的修辞学里,“浆果”是“身体”(肉身)的喻体:“我在这里将它比作人类复杂而曼妙的肉身,拥有柔韧苦涩的皮囊,内里却充满酸甜混杂的汁液。”我们知道,尚未成熟的浆果是食用之禁忌,拥有理想化意味的“汁液”,只有从瓜熟蒂落的结局里流淌出来,才合乎普遍的视效、味觉,以及质感。类比终极目标的“汁液”,如何成为一种对“浆果”的关怀?——“当多情的汉语遭遇人类软绵而轻盈的思虑,猝然的相遇便化为一柄语言之刃……”
“语言”之于身体,无疑成为了解读的工具。它进入身体,汁液理所当然扮演或润滑,或阻碍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汁液左右了“解体”进程。在与身体不断纠缠的活动中,“语言”拥有了湿漉漉、淋漓的气质。在茱萸看来,这种气质催生了汁液(体液)淌动的凹槽:“这种’解体’解放了橙的淋漓汁液,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果肉的晶莹。”
仿佛所有的行为都为一睹“晶莹”是为何而展开。毫无疑问,“语言”切实做到了这一步,在现代性枝繁叶茂的经典作品里,我们能尽览身体的碎裂、愈合,以及再碎裂、再愈合,极像一条河流。也只有河流才能提供如此敞开的视角。
如此,我愿意将与身体有关的叙事,称之为“水事”。——有“事”,即有戏剧的脚本。我想,这肯定应和了茱萸的“浆汁”一说。
“……这枚橙,开始被空前规模地制作成橙汁、果脯、药物、首饰、广告意象乃至产品LOGO,开始被高强度消费,进入符号增殖与意义重复的自我循环里”,“语言”应该是促进了这一“循环”的快速发生。
“语言”开始变得巧妙,意义延伸,指向范围更加辽阔。它能更迅猛地穿插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操持“嫁接与移植”的活计。因此而产生的忧虑,茱萸明显地道出了:“这枚橙……被加工、被规训,成为浮躁而遍施铅华的符号本身,这枚橙依然有饱胀的肉身与淋漓的汁液……”
也许“忧虑”一说并不准确,因为一切似乎都发生得十分自然,起承转合得不露痕迹。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团冷火,在橙树濒临枯朽的原野上,悄悄地滚动着,直到光耀屋舍。而作为身体的喻体——浆果,早已散落屋舍中。由浆果的碎裂而出现的那六瓣橙(《浆果与流转之诗》中的六篇文章)——耳目、毛发、唇齿舌、颈肩、胸乳、脚足,能触及到什么吗?譬如,对于“目”,茱萸写道:“……临渊照影,但是前提是必须躬身,这一极富有意味的姿态象征着谦卑与谢罪。”譬如,对于舌头,“这一件柔软的事物横贯在人类言说的关卡间”。再譬如,对于胸乳,“……文人们早已习惯了嗅觉与触觉上的享受,这’玩味’和’揉搓’,竟综合成了如此妖魅的一个词汇:软玉温香”。
反过来看,这身体滋养了“语言”的生长?我们似乎总在找寻最吻合感官感受的表达方式,出于对“理想国”的好奇。
三、诗歌:神圣的废部
如果“理想国”还有言语活动,那一定是诗歌了。也只有诗歌,能制衡圆满与梦幻(现实的“理想”)。也只有诗歌,能集结起所有隐秘的物什,上演一场关于“风物”的大戏——告诉人们,从哪里来。这一点,无疑扩大了“理想国”的空间概念,同时,为身体的再现(第无数次了)开始蓄力。
——按照叶芝的说法,我们和自我争辩,产生了诗歌。
——按照史蒂文斯的说法,诗歌就是内在的暴力抵抗外在的暴力。
“无视”“重估”算暴力吗?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现象世界的,“守缺”都有其行为的神圣性,意味着能从一切“圆满与梦幻”之中,重新发现“语言”的价值,即那柄将进入浆果的刃。要知道,在此刻,那柄刃是荒废的。它极可能是“理想国”居民屋舍的某一件挂饰。如果你正视它们,兴许能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在《帘箔:幽会的缠绵与阻隔》中,茱萸开始沉迷这些挂饰:“帘箔”不再是帘箔本身,而成为了遮蔽身体的有效方式;“幽会”这一从属于身体之欲望与激情的行为,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强化,叫人兴奋,如他所说:“帘箔充当了一个类似补语的角色,并非不可或缺,却能让整个句子更为完满和通透。”
这帘箔,这由小小的布匹、珠粒、坠件等串联起来的帘箔,实在接近诗歌的特质:日常,意义,距离,可拆解,碎片。
那孤立存在的布匹、珠粒、坠件,仿佛对应着不断从“语言”里局部独立的“耳目唇齿……”。我猜想,延续了传统精神的它们,在斑驳陆离的现代性里,俨然废墟,即废弃之物的集合地。我设想过这样的画面:一处空旷的场地,它们各自安详,流淌的河水串联起它们,让其变成了神圣高地。
在“意义”遭受摒弃的当下,这六瓣橙如同同时发射的子弹,即使命不中目标,作为废弃的弹壳,也是力量作用过的有效存证。
2013年8月,景德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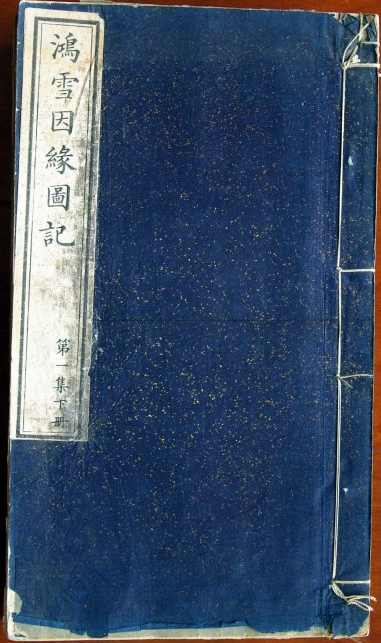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