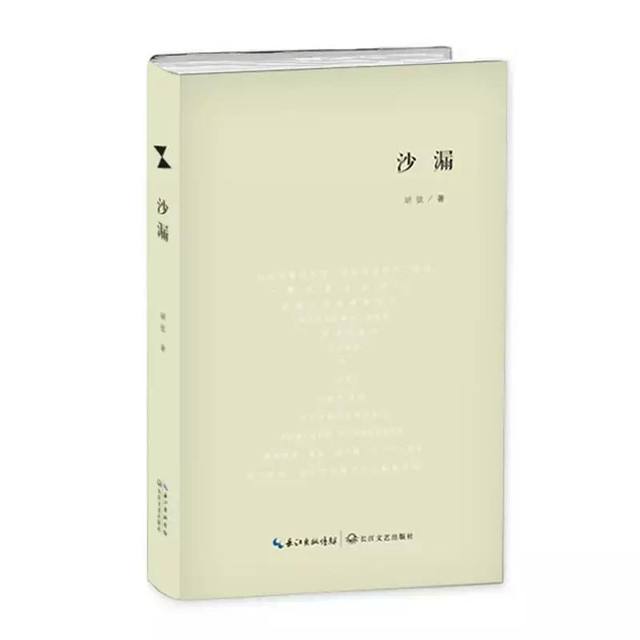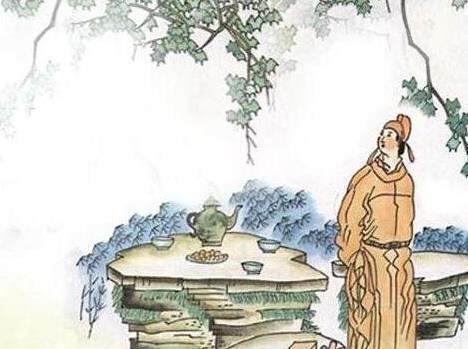同时,也难免让人感喟,一位诗人,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事物的命名,对语言的创变,在这个物质化时代的反响是多么轻微!其诗意言说的声音,要等多少年才能抵达公众内心,激起审美的涟漪?当然,关于写作,关于时代征候以及审美接受,一如生命存在、生活现场和自然宇宙中的诸多事物,都是诗人需要处理并正在处理的。
语言、语调及话语组织
语言是诗人的工具,用于处理自身与万物的关系,但它也会被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或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赋予本体论的高度。不管怎么说,语言都是诗人财富,是彰显主体精神或展现外物的凭借。胡弦的诗歌语言很有特色,语句短缩,质地轻盈,抑或有着万钧之力集于针尖的痛感。细究之下会发现:他的语言是去修辞化的,毫无矫饰之感;口语化的选择,增强了鲜活、灵动和亲切感;书面乃至文言的融会,则显出书卷气和文化内涵。就是这样,好的诗人从不懈怠对语言的追求,会从不同的话语资源中汲取,熔炼成自己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体系。
《金箔记》是一首寓意深广的诗,但其中的“金箔”意象,恰好可以用来比拟胡弦对语言的千锤百炼,以及这种语言的特质——轻盈、闪亮、富有延展性。从而,轻易抵达内心和事物的本质。他貌似简洁明澈的语句,却存在陡峭而险峻的内部,思之深邃和语义之丰散发智性之光。诗人在《献祭》一诗中写道:“使用最少的字,因为/句子随时需要逃生。”其所传递的,正是诗人了然于胸的语言智慧。胡弦的诗之所以始终保持语言的活力和新鲜度,表面看来,是对陈腐语汇和语言杂质的剔除、提纯,对俗常话语方式、言说方式的变构,实质上,是诗人感知事物、诗思运作方式的更新。而这体现的也正是诗人的创造力。
胡弦的诗歌语言绵密细致,充满哲思,但他的言说语调却是轻声细语式的,“南方气质”很浓,从不以咄咄的气势逼人。这显然是一种谦逊而睿智的言说方式。如果将一位诗人的精神气质和语言风格归因于地域文化的浸染,似乎并不全面,因为诗人如此道说:“无数次围城,河山飘摇,而炉中烟/总是一根孤直,不疾不徐。正是/这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教会了你对世界轻声细语”(《沉香》)。这似乎可以作为诗人心性和话音语调特征的另一种解释:在现实生存的隐忍和思悟中所进行的一种自主选择。更进一步,我们还可将他的“轻声细语”看作是一种智慧表达。因为诗人深知人在世界面前的渺小及人性的限度,于是,他接着说:“城市服从天象。岁月的真实/来自个体对庞大事物的/微小认识”(《天文台之夜》)。
胡弦诗歌的话语构成看似单纯,实则有多方的融会。前面也提到,他对口语、书面语以及文言古语的熔炼。具体到作品中,要看抒写对象和特定语境。比如组诗《拈花寺》,就有大量的古典语汇和情境入诗,透出江南的风情和古典之美。而在书写现代生活的诗篇中,剥离辞藻的日常化语汇便是主体。同时,他还会在诗中设置、化解历史文化典故,形成文本的互文关系。而一个最为醒目的标志,就是“嵌入式”语句的运用。常见的情形是,在一首诗整体的叙述节奏中,忽然被一个叙述主体不明的诗句或诗节(引号中的部分)中断了进程。当然,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这样做,无疑丰富了诗歌话语组织的构成方式,使得叙述视角多元化,为作品带来立体的结构。
物的想象和召唤
胡弦正是操持这样的语言和语调,朝向客观事物以及存在的深处探寻。
他的诗不以情感的饱满、真挚为特征,也不以强烈的抒情感染力取胜。相反,他尽可能地剥离诗歌的抒情性,因为他不是一个主观性的诗人,他的眼光是向外走的,取代感染力的是一种极为冷静克制的对事物的洞察力。如果我们稍稍梳理中外诗歌的流变历程,就会发现,为浪漫主义诗学所倚重的心绪、情感、个性及灵感,早被现代主义诗人所背离。因此,艾略特才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里尔克也说:“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结合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新诗来看,“叙事诗学”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于九十年代蔚然成风。诗歌的抒情被叙事所取代,诗歌指向的不再是主观情感,而是外物、人或事件。
当然,作为诗歌的抒写手段,抒情和叙事自古就存在。即就是当下,依然有不少抒情诗人,只是他们在情感抒发的过程中,多了一份审慎,间或融入更为深沉的思考。其实,胡弦的诗歌也存在抒情状态,只不过有意降低了音调和强度,显得细微而疏淡,像《小谣曲》《在春天》《伊犁河,记梦》等。总体上,胡弦采用的书写方式是叙述和呈现,当然也包含叙事性。这就像一个好诗人,绝对不会偏执于口语或书面语,抒情或叙事。他会采取一种综合的方式,进行贴切、有力的诗歌表达。
当诗歌的处理对象发生转向,可以说,正是自身感官经验的剥离,让物呈现,让纷繁杂乱的存在物展现自身的秩序。在写作中,胡弦排除满溢的情感,从自身抽离出来,实现了对物的静观和发现。《水龙头》《钉子》《秤》《一根线》《绳结》《裂纹》《空楼梯》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近乎中国古代的“咏物诗”,或里尔克的“物诗”观念,但这类作品要比传统咏物诗复杂、深邃得多。因为诗人在此是以一种哲学式的“我思”状态,进行观照和洞察,相比传统的审美静观,更深入事物的本质。于是,我们发现:“水龙头”像一个陌生物,突进我们的视域;“空楼梯”陷入对自己的研究中,在自省的知与未知中反复。而《夹在书中的一片树叶》一诗,既深入物的内部,也探及思维的纤细幽深处,激起的是知觉的旋涡和风暴。
物本身,是具有质感的存在,原初之物联接人的精神。在对物的凝视和谛听中,诗意、存在的秘密显露出来。这时,诗人就是命名者。“这种命名并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中。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胡弦诗歌中的很多物象都有自己的意识和判断,具有主体性——似乎不是诗人在那里言说,而是事物自己呈现自身。这当然与诗人主体性的撤离有关,但也绝非拟人手法的运用那么简单。
或许,对于情感、精神、灵魂的过度关注和褒扬,妨碍了人们对社会、现实、自然等等事物的认识,现代艺术转而追求对于物的发现,即令为常识和经验所遮蔽的事物重新向我们敞开怀抱。这种艺术上的物质主义倾向,并非贬低人的精神和意识,因为“物的深度惟有在人的深处才有彰显的可能”。纯粹的“水龙头”,就是这样出其不意地挺进我们视野的,带来新的审美体验和生存经验。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