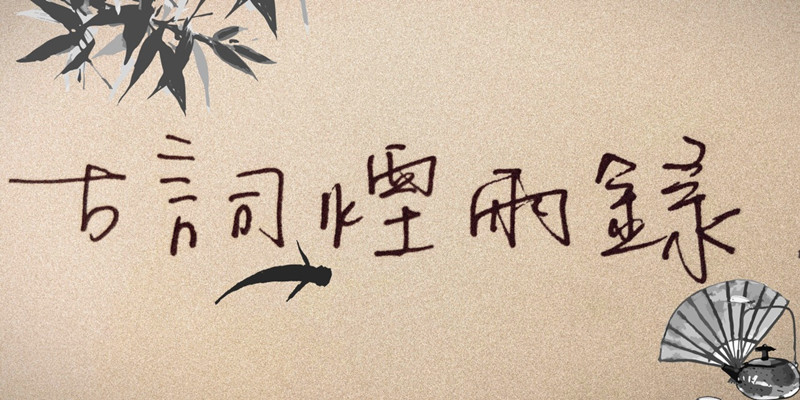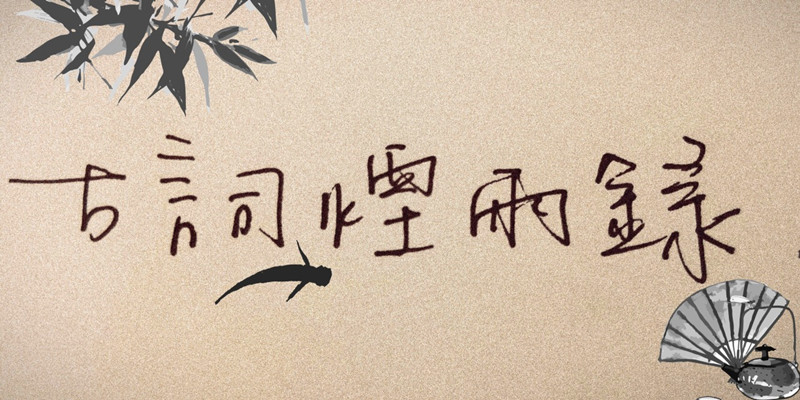因为这不过是一句寻常的描摹、转述,是日常语言而不是诗歌,仅仅以七言律句的格式说出来而已。而魏夫人的《菩萨蛮》词中说“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便成为了诗句(词句)。唐人白居易,也曾将“四十多年过去了”的事实,用月亮“东西四五百回圆”的方式表述出来,让事实充满了警动人心的力量。
所谓诗境、词境,即人所不能离开的、自身与天地万物共同构建的广袤情境。词人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之中,才能在笔下创建以这广袤为蓝本的审美境地。若是以“悬空者”的状态转述已经被提炼、概括的纯粹事实,凭借抽象而精确的数量词作为表述工具,则诗歌便永无出现的机缘。
所以,诗词能喻哲理,但本质是反哲学的。哲学的思维方式便是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的对立面去反观反思。日本哲学家木田元先生在《反哲学入门》一书中说:真正的“哲学”是欧美人所特有、而不是全人类共有的思考方式,它要求人的理智站在远离世界的位置反观世界、反思人生,恰似用手提着自己的身体离开地面。但自己如何在一个外部的立场上、反观自己不能脱离的所在,成为了困扰西方哲人几百年的哲学难题。
东方世界所特有的诗化、人文化的思考气质,恰恰不具有这种“超自然原理”,而是要投入纷繁的现象之中,以直观的方式彻悟人与世界宇宙的息息相关。这样的人文气息,以及我们反复探讨的诗境词意,就是王国维说的“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西方哲学-科学精神恰恰是要避免看到的世界“着我之色彩”。
东方世界的古典人文精神,来源于万物有灵的观念。日月星辰、高山大河、蛇虫狐兔、大树老藤、祖先逝者,皆有精魂。人们生存的世界因而神魂飘拂,充满了种种意志、情态、愿景,人不得不与之接谈、应酬。就像《庄子》所说:“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①
诗词中满漾着人间情意的自然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似于远古巫术或宗教模糊化之后的视觉残留。诗境与鬼境之间、士大夫的诗情画意与寻常百姓拜神拜鬼的行为之间,都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
当西方的哲学-科学精神像鲁迅笔下的疯子那样打灭了残破神庙中的长明灯,山之阿也将从此不再若有人兮。
菩萨蛮
[宋]魏夫人
溪山掩映斜阳里。
楼台影动鸳鸯起。
隔岸两三家。
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
早晚溪边去。
三见柳绵飞。
离人犹未归。
(选自《唐宋名家词选》第177页)
上阳白发人(节选)
[唐]白居易
……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
(选自《唐诗名篇故事》第441页)
①《庄子》,中华书局2007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