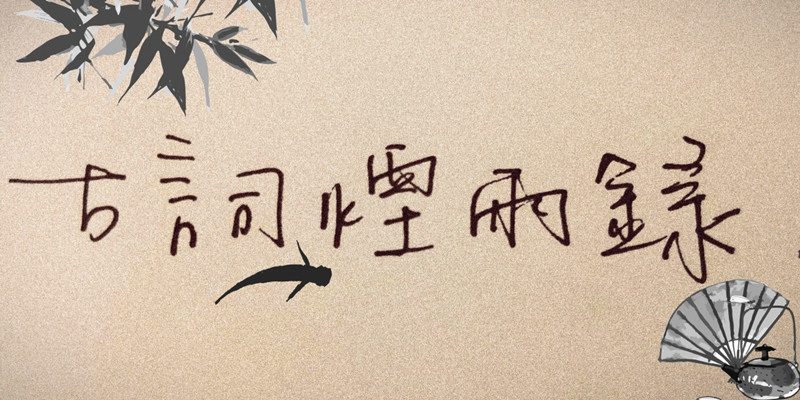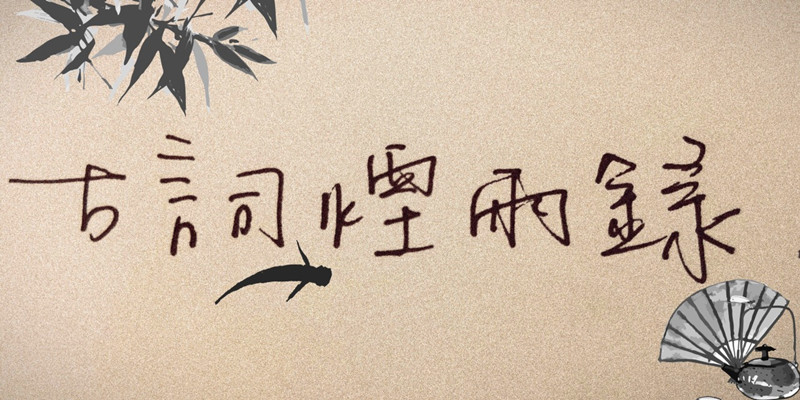词的“非功利性”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原稿下面还有“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将诗词视为艺术品,而不是工具。
他期望诗词能够超离现世、超离功利,通过直觉与感发直接达到不染纤尘的艺术境界。
殊未知,中国古世从未有过如此诗文。仕如杜甫,隐如陶潜,视野无不聚焦于现世时空。
唯有五代北宋的词,才真正脱离了功利性、实用性,在娱乐的、不严肃的本义中抵达了纯审美、纯诗意的境地。
另一方面,王国维视为“词家所禁”的寿词,其实是词之常态。晏殊的集中便有众多诸如“急管繁弦、共庆人间瑞”“满酌玉杯萦舞袂。南春祝寿千千岁”之类的词作。《全宋词》中这样的词更占有极大的篇幅。常规意义上的“词”,一直可以以中性的姿态,承载现实人际关系和社会性庆典的浊重喧哗。能够抵达纯审美境地的词,反而是少部分特出之作。
王国维之所以在原稿中删去“怀古、咏史”字样,或许是碍于东坡《赤壁怀古》之高绝。然而在观念方面,苏子以诗文的叙事、感发等方式填词,恰好与王国维对词的纯审美要求站在对立的位置之上。
词与人文精神
实用性、道德性,是中国古典时代人们的重要价值取向。
实用性,即现世重于彼岸。
道德性,即伦理即是真理。
实用性价值,容易导致人们拒斥根底性的发问与思辨。
道德性价值,则在中世纪时成为让人们动辄得咎的精神重负。
有意思的是,当人类从古世进入近代,这两种价值观念分别展现出了更多的负面因素:当人们怀着传统赋予的实用心态进入现代社会,很容易唯利是图。而古典的伦理精神,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当代社会中人们轻视规则、人情泛滥的负面因素。
然而,中国古典时代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那些伟岸的人格、不屈的灵魂,却也是从实用性、道德性这两种价值取向中精炼而成的。
士大夫们,必须先在以实用性和道德性为主的精英文化中浸润至深、并具有极高修养,又需要超越实用而达到“关怀”、超越道德伦理而臻于“挚爱”。
词的发生地是歌筵之畔。在纯娱乐的环境之下,那些具备高级精神修养的人们,得以暂时脱离观念的羁缚,将既真挚而又经历过锻冶的人性和盘端出。
所以,花前酒边的词人们,既少见低级趣味的粗俗,也少见故作的狂态。他们呈现出的是充斥着享乐欲望的、真面目的人性,却也是经过文明锻冶的高级人性。风范、情怀、修养、识见,一切恰到好处。这就是为何韦庄词艳丽夺目,却总被视为有楚骚之意。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亦是如此。
在词的世界里,现世是被诗化后的场域,世俗标准的功利被弱化,只有人与景深共同造就的审美境界;伦理中的名教色彩也已消隐,只呈现出真挚的情感。
秉持着深厚的精英文化修养的词人们,就这样为中国古典文明调和出了浓郁的人文色彩。
发端于诗经楚辞、并在唐诗宋词中绚烂绽放的审美精神和人文精神,闪烁着中国古典文明最为灿烂动人的光芒。
冯震翔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